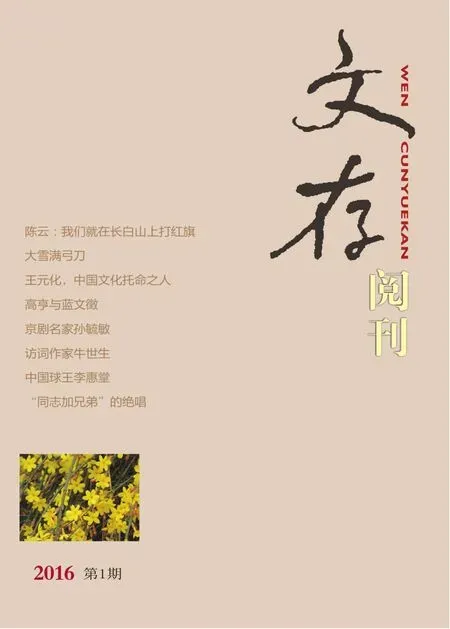在時光的倒影之中外一篇
□任林舉
?
在時光的倒影之中外一篇
□任林舉
窗外的山桃花開過,然后又落去;過站的候鳥來了,轉眼又飛走……
望著在風中空空搖擺的樹枝,突然想起母親,想起母親那些寂寞的表情和期盼的目光。在母親的生命里,也許我就是那常來常走、一閃而過的花或鳥兒吧?
盤點自己這半生,能夠陪伴母親共同度過的時光真是太少了,相對人生的全部進程,充其量也只能占到種子之于糧食的比例。小時候,母親幾乎每天向我灌輸著“好男兒志在四方”的觀念,并把全部心思都用于督促我的“學習”,以期有一天可以讓我藉此離開那片土地、那個村莊,自然,也會離開她。就連我有時“心血來潮”幫她做一點零活兒,她都面露慍色,責備我胸無大志,像個女人一樣俯身俗務。于是,我只好硬起心腸,“忘我”讀書。忘我,也忘記了母親,不再去想她勞作時的辛苦與艱難。為了不負母親的期望,我瘋狂地奔跑在求知、“升學”的路上,早早地實現了對她、對故鄉的“離棄”,遠走高飛。
最初那些年,母親表現得十分“剛強”,她常以她的出色的節制和冷靜向我傳遞一種樸素的信念,讓我堅信,我們能夠擁有的團聚和快樂如我們的財富一樣,是不能揮霍的,只有“細水”才能“長流”。由于家境貧寒,承擔不起路費和額外的消耗,母親就鼓勵我不要想家,不用總惦記回家。所以,除了春節,幾乎所有節假日我哪兒也不去,只是躲在集體宿舍里給母親寫信,在時間和空間的屏障之外,向她描述我學習或工作上的“順利”以及生活和際遇上的“平安”。幾頁信紙、一張郵票就行使了“見字如面”的使命。如此這般,似乎就真的“免”了彼此間的“牽掛”。母親說,只要平安,就比什么都好。每當我們離別,她總是從我身后丟下一句很“硬”的話:“走吧,我不惦記你。”我知道那句話的真意,便順勢把那句“堅硬”的話當作抵擋風雨的外衣,緊緊地裹在身上,咬緊牙關,為她創造出種種“不惦記”或不用惦記的理由。
不知從哪一年起,母親變得不再“剛強”。如果有一段時間,我因為“沒頭沒腦”地忙碌,沒有抽出時間給她打個電話,她就會坐立不安,在客廳里一圈兒接一圈兒地轉,邊轉邊對妹妹說,又像是在喃喃自語:“你大哥沒來電話吧?”直到妹妹看透她的心思,將我的電話撥通,她才會從那種無所適從的狀態中轉過神來,重歸安然。而當我出現在她面前時,她的目光也再不像以往那樣淡定,從上下打量開始,一直到最后的密密纏繞,不離左右。我知道,這目光是許多年、許多孤單寂寞的夜晚或白晝、許多堆積在心里的情感,經過她以心以命地細細搓捻,捻成的兩條無形的繩索。如今,她要用它們將自己和她的兒子緊緊系在一起。不僅是目光,她的腳步也會常常不由自主地隨著我的移動而移動,我到了哪里,她就跟到哪里,那情形就如一個三歲的孩子跟定了大人一樣,怯怯地,無聲地,卻異常執著。
母親老了,老得孩童般溫柔、孩童般脆弱。
去年,傳統的“小年”剛過,我還沒來得及考慮回家的事情,母親就急著讓妹妹給我打來電話,特意叮囑我回家時千萬別給她帶錢帶物。我理解她的言外之意——“我什么都不稀罕,只要你人回來就行。”
放下電話好一會兒,我才從生硬、麻木的工作狀態中回轉過來。雖然這些年事業、生活、情感等領域里的諸多錯位,讓我不得不經常從一種狀態轉換到另一種狀態,但這種不斷的轉換和“穿梭”,并沒有把我磨練得更加潤滑、靈敏,反而因為過于頻繁的“操作”和“磨損”,讓我的意識和思維里生出了斑斑“銹跡”,越來越難以在各種狀態間轉換自如。當我終于放下眼前的雜事和雜念,凝聚心神想一想母親的境遇和愿望,替母親盤點一下她生命里的存儲和盈余,內心里突然生出無限的感傷,想起為人父母的不易與可憐。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人生中的某些事情,怎么看都像一場執迷不悟的暗戀。每當我想起卞之琳的那首詩,就會想到天下父母對于子女的那份一往而深、一去難返的愛與情感,自然而然也想到母親。在我的認知當中,母親的可憐更甚于天下其他父母,不僅僅因為她的敏感、細膩,還因為她的命,苦如黃蓮或比黃蓮更苦。她這一生啊,三歲失去了父親;四歲失去了母親;八歲失去了親人的照料與家庭;十三歲失去了最疼愛自己的哥哥;四十五歲失去了丈夫……到了最后,還能剩下些什么呢?她一生沒有工作和所謂的事業,她全部的事業就是養育五個子女。到了晚年,因為幾次遷居,連證明自己身份的戶口底檔也弄丟了,竟然成了一個沒有“身份”的人。如今,她在這個世上惟一的身份就是五個子女的母親,她在這個世上活著或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盼望著一年一次或很少幾次見她自己的子女一面,而她的子女大部分時間都被其他的事情追著,被其他的人追著,心思、情感以及關注的目光俱在“別處”并沒有凝注于她。
近些年,雖然我差不多每個節假日都會放棄游玩和出行的機會,趕回去看望母親,但我還是覺得自己的“身份”有些可疑。像一個忘恩負義的之人,本應該讓自己的母親晚年不再忍受思念之苦,卻將少得可憐的關懷和探望當作引以為傲的“孝心”和慰藉;也像一個自私自利的小人,本來是為了獲取自己心靈和情感的安慰,填補自己心中的缺憾,卻儼然長了一雙翅膀,忽來忽走地閃現于母親面前,扮演著雪中送炭和撫平思念的愛之天使。
在家里,在母親身邊,我能夠做的只是盡可能多地陪陪她。與她單獨相處,斷斷續續地說一些話,看著她慢條斯里地擺弄自己那些小物件兒:毛巾、手帕、圍巾、床品等等,一樣樣地數,一樣樣地疊,一樣樣地擺,方方正正,齊齊整整,有條不紊,像是以一種珍惜的情緒梳理著往昔歲月,投入、忘情、不厭其煩。那些物品,都是我這些年陸續給她帶去以供日用“不起眼”的小東西,如今看上去依然簇新如初。看著看著,就有淚水悄悄涌入我的雙眼,看著看著,我仿佛就穿越了時光隧道,抵達了歲月的另一端。呈現在我眼前的,已經不再是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分明是一個埋頭擺弄自己心愛的糖紙、沉醉于“過家家”的小女孩兒。
北方的春天來得遲,節氣都已經到了清明,天空還有雪飄落,但這時的雪已經“站不住”了,落下來就會融化。母親固執地認為這場雪會危及我們的行車安全,不等我們返程,就一遍遍叮囑:“路上雪大,可要多加小心呵!”跟她解釋了幾遍,仍不管用,待我們臨出門時,聽到的還是她那句充滿擔憂的“嘮叨”。以往告別,只要我們回頭,總是能夠看到母親依戀的身影和目光,但這一次卻有些出人意料,轉身就不見了她的身影。大妹妹敏感,發現了我目光里的詢問,便告訴我,母親回自己房間了。我突然醒悟,母親是基督徒啊,她此刻定然依規“走進內室,面對你的神,說出自己心中的愿望。”
就這樣,我再一次從母親身邊飛馳而去,只把母親丟在回憶之中或者說那長長的時光的倒影之中,孤獨地坐在自己房間里,巴望著下一次與兒子的重逢。
大朵大朵的雪花從天空飄落下來,落到車窗上,隨即融化,像雨滴,像淚水在玻璃上流淌。在一片模糊的視野之中,母親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一點點清晰起來……也許,終會有那么一天,母親要離開我們,我想,那些與母親共度的時光,應該會如種子一樣,在我心里發芽、生長,鋪滿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