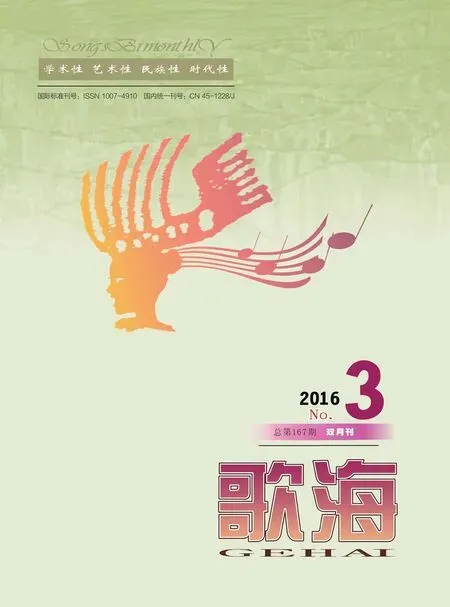古史辨派與朱謙之在“詩樂”上的態度
·留 生
古史辨派與朱謙之在“詩樂”上的態度
·留生
古史辨派又稱“疑古學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出現的以“疑古辨偽”為特征的學術流派,其創始者及主要代表是顧頡剛、胡適和錢玄同。朱謙之作為近代音樂史學家,在音樂文學史、哲學、宗教學、東方學等方面貢獻卓著,他與古史辨派在關于《詩經》中“詩樂”的學術態度上具有見解一致的地方。
古史辨派;朱謙之;《詩經》;“詩樂”;態度
一
古史辨派,又稱“疑古學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出現的一個以“疑古辨偽”為特征的學術流派,①一般認為,這個學派是從1923年顧頡剛發表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開始形成的,因為在這篇文章里,顧頡剛第一次揭起“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論斷。其創始者及主要代表是顧頡剛、胡適和錢玄同。前者顧氏發明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說,后者錢氏自稱為“疑古玄同”,以“新知”亮劍于學術界。不可否認,古史辨派的誕生與胡適提倡“整理國故”的方法與實踐有關,也不可小覷胡適的“歷史的演進法”與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說”之間的傳承關系。放眼看去,這股疑古浪潮并非“空穴來風”,可謂古已有之,如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為精辟!以后,宋、晚明、清初均有疑古之風存,如宋代的劉知幾,晚明的胡應麟,清代的姚際恒、崔述等。若說西方,則近代以來有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杜威的“實驗主義”等思想。總之,就民國時期誕生的古史辨派而言,他們在當時的環境里注重吸收西方近代社會學、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典籍,意圖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實現“創造性的轉換”,②林毓生語,參看《什幺是“創造性轉化”?》一文,載于林毓生著:《熱烈與冷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7頁。在學術界確實產生了莫可估量的生命力,而筆者關注的僅僅是其中對“詩樂關系”的論述。
朱謙之(1899年—1972年),字情牽,福建省福州市人。因其學術趣味與研究領域廣泛,有“百科全書式”學者的美譽。終其一生,在音樂文學史、哲學、宗教學、東方學等方面貢獻卓著,均有大量著述傳世。③據不完全統計,他一生共留下專著42部,譯著2部、論文100余篇。參見黃心川:《朱謙之文集·第一卷》序文。就其音樂學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音樂的文學小史》《凌廷堪燕樂考原跋》《中國音樂文學史》《希臘與中國音樂之交流》等。朱謙之與古史辨派在對《詩經》中“詩樂”的學術態度上,有很多見解一致的地方。
二
早在1923年,古史辨派掌門人顧頡剛先生就撰文在《小說月報》上向二千年來的詩學傳統發難進攻。④指《〈詩經〉的厄運與幸運》,1931年收入北平樸社出版的《古史辨》第三冊時,更名為《〈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以下出自這篇論文的字段均引自《顧頡剛民俗學論集》,錢小柏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251頁。他以疑古學者的鋒芒批評義理派的詩學把《詩經》的真相“全給弄糊涂了”,⑤《顧頡剛民俗學論集》,錢小柏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3頁。這就“譬如一座高碑,矗立在野里,日子久了,蔓草和葛藤盤滿了。在蔓草和葛藤的感覺里,只知道它是一件可以附著蔓延的東西,決不知道是一座碑”。所以他說自己要“做一番斬除的工作,把戰國以來對于《詩經》的亂說都肅清”,也希望能夠“洗刷出《詩經》的真相”。他在說明自己做這篇文章的動機時說:“最早是感受漢儒《詩》學的刺戟,覺得這種的附會委實要不得,后來看到宋儒清儒的《詩》學,覺得里邊也有危險”,再之“給求真的欲望所逼迫”而不得不妙手秀文章了。①《顧頡剛民俗學論集》,錢小柏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頁。《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一文,不難看出古史辨派對詩樂關系的討論,實際上與對《詩經》中歌謠的整理有關。需要注意的是,顧頡剛等人所說的歌謠,“已經不是先秦兩漢所謂‘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而是把歌謠引申為民間的歌唱”,②趙敏俐、吳相洲、劉懷榮等著:《中國古代歌詩研究——從〈詩經〉到元曲的藝術生產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頁。也就是民歌。
胡適先生作為古史辨派的“引路人”“參與者”與最終“分道揚鑣者”,③杜蒸民:《胡適與古史辨派》,載《安徽史學》1989年第1期。也曾發表過多篇論說《詩經》的文章,惟有一篇1925年的演講錄《談談〈詩經〉》略及《詩經》與歌謠的關系,且劈頭就將《詩經》作為經書的價值否定掉,只承認“《詩經》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④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三冊,上海書店影印版,民國叢書第四編第66號,第577頁。據實而言,胡適在《詩經》與“用樂”的關系問題上,并沒有什么創見,至于他所謂的“《詩經》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一說籠統而不科學,因為《詩經》中有少量的作品是沒有歌詞的器樂曲。但是,他認為“(詩經)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⑤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三冊,上海書店影印版,民國叢書第四編第66號,第577頁。1925年11月18日始草,12月16日脫稿,原刊于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10、11、12期上,1925年12月16日至30日發表。確屬新知卓見。
倒是胡適的學生顧頡剛關于《詩經》的幾篇討論文章,對于詩樂關系的考查最有價值。按其發表的時間順序,依次為《〈詩經〉的厄運與幸運》《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和《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
顧之論見,價值何在?先看《〈詩經〉的厄運與幸運》。⑥該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傳說中的詩人與詩本事》,指出周代的音樂很普及,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均有歌唱的喜好,故而《詩經》就是“入樂的詩的一部總集”,詩與樂是分不開的。
第二部分《周代人的用詩》則著重討論了周代人對于“詩”的態度及“詩”的運用場合。顧頡剛指出“《國風》中的大部分是采自平民的歌謠,……在大小《雅》里,采的民謠是少數的(如《我行其野》《谷風》等),而為了應用去做的占多數(如《鹿鳴》《文王》等)。《頌》里便沒有民謠了”。在顧頡剛看來,春秋時期,《詩經》的流播十分廣泛,“當初做詩時雖分階級,而后來用詩的便無階級”。同時,《詩經》也是為著種種的應用,如典禮、諷諫、賦詩、言語等而產生的,其中既有民間采集再加工整理而成,也有直接由樂工作出來的。所以,在戰國之前,人們“對于這些入樂的詩都是唱在口頭,聽在耳里”。⑦《顧頡剛民俗學論集》,錢小柏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頁。
第三部分《孔子對于詩樂的態度》,他認為孔子處在“樂詩”的存亡之交,即當時音樂界出現了三個趨向。⑧《顧頡剛民俗學論集》,錢小柏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頁。第一是僭越,即超越用樂的等級來享用音樂。第二是新聲的流行。“新聲是不合于詩,不合于禮”,音樂上十分自由,“沒有節制,聲調可以伸縮隨意,不立一定的規矩的”,在使用上可以專當音樂來聽,不必依附著別的應用。對于新聲是否即為《論語》中的鄭聲,顧頡剛也認為“未能解決”,但是他又說“總之,新聲與鄭聲都不是為了歌奏三百篇而作的音樂,是可以斷言的”。顧頡剛肯定了新聲的藝術價值,并委婉地批評了孔子惡鄭聲所體現出來的中庸主義的倫理觀,他認為“新聲的起是音樂界的進步,因為雅樂是不能獨立的,只做得歌曲的幫助,而新聲就可脫離了歌舞而獨立了”。第三是雅樂的敗壞。他說“雅樂到了孔子時,決不能維持它的原來的地位了”。
第四部分《戰國時的詩樂》,認為戰國時存有一種比之鄭衛之音更甚的俗樂,即“桑間濮上之音”,文獻記載這是比“亂世之音”更甚的“亡國之音”。顧頡剛認為春秋與戰國時期,在用樂過程中所使用的樂器也存有較大的差異,戰國時期偏于享樂的絲竹樂器的使用更為頻繁。樂器的不同,也反映出音樂與文學的關系,即春秋時的用樂是做“歌詩”的輔佐,與現在的歌曲伴奏類似,而戰國之“用樂”趨向于脫離“歌詩”,向著純器樂曲的方向演化。換句話說,西周以來“賦詩”的傳統逢戰國亂世而“隱微”,重“器樂”而不重“歌樂”之風漸趨盛行。雖不能說《詩經》的本相——樂詩已絕跡,但自戰國以來詩與音樂的關系“疏離”確是事實,所以顧頡剛說“《詩》的基本意義和歷史是春秋時人所不講的,到這時因為脫離了實用,漸漸的講起來了”①《顧頡剛民俗學論集》,錢小柏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頁、251頁、252-253頁、266頁、282頁。。
第五部分《孟子說詩》,批評孟子解詩“以意逆志”對詩學的害處,無關于詩樂關系,故在此置之不論。
就后三個部分,顧頡剛總結道:
“從西周到春秋中葉,詩與樂是合一的,樂與禮是合一的。春秋末葉,新聲起了。新聲是獨立性的音樂,可以不必附歌詞,也脫離了禮節的束縛。因為這種音樂很能悅耳所以在社會上占極大的勢力,不久就把雅樂打倒。戰國時,音樂上盡管推陳出新;雅樂成為古樂,更加衰微得不成樣子。一二儒者極力擁護古樂詩,卻只會講古詩的意義,不會講古樂的聲律。因為古詩離開了實用,大家對它有一點歷史的態度。但不幸大家沒有歷史的知識可以幫著研究,所以結果只造成了許多附會。”②《顧頡剛民俗學論集》,錢小柏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頁、251頁、252-253頁、266頁、282頁。
從中不難看出,其“詩樂始合后分”的觀點承襲了王國維在《漢以后所傳周樂考》中的“詩樂分途說”。
再看《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全文涉及兩個重要的概念,一者是“徒歌”,一者是“樂歌”。他所謂“徒歌”,就是民間百姓口頭傳唱的尚未入樂的歌謠,而“樂歌”則是經過了樂工的整理改編,具有重章復沓結構特征的入樂的曲調。顧頡剛關于“徒歌”與“樂歌”的區分標準,與他在家鄉搜集歌謠的經驗直接相關,他說:“我前數年搜集蘇州歌謠,從歌謠中得到一個原則,即是徒歌中章段回環復沓的極少,和樂歌是不同的。徒歌中的回環復沓,只限于練習說話的‘兒歌',依問作答的‘對山歌'。此外,惟有兩類也是回環復沓的,一是把樂歌清唱的徒歌,一是模仿樂歌而作的徒歌。”③《顧頡剛民俗學論集》,錢小柏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頁、251頁、252-253頁、266頁、282頁。
三
在上述文章里,顧頡剛還從創作動機的角度,討論了“徒歌”與“樂歌”的形成,認為:“徒歌是民眾為了發泄內心的情緒而作的;他并不為聽眾計,所以沒有一定的形式。他如因情緒的不得已而再三詠嘆以至有復沓的章句時,也沒有極整齊的格調。樂歌是樂工為了職業而編制的,他看樂譜的規律比內心的情緒更重要;他為聽者計,所以需要整齊的歌詞而奏復沓的樂調。他的復沓并不是他的內心情緒必要他再三詠嘆,乃是出于奏樂時的不得已。”④《顧頡剛民俗學論集》,錢小柏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頁、251頁、252-253頁、266頁、282頁。
在他看來,“《詩經》中一大部分是為奏樂而創作的樂歌,一小部分是由徒歌變成的樂歌。當改變時,樂工為它編制若干復沓之章”。通過“春秋時的徒歌”“《詩經》的本身”“漢代以來的樂府”及“從古代流傳下來的無名氏的詩篇”這四個方面,顧頡剛進一步推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他說:
“春秋時的徒歌是不分章段的,詞句的復沓也是不整齊的;《詩經》不然,所以《詩經》是樂歌。凡是樂歌,因為樂調的復奏,容易把歌詞鋪張到多方面;《詩經》亦然,所以《詩經》是樂歌。兩漢六朝的樂歌很多從徒歌變來的,那時的樂歌集又是分地著錄,承接著《國風》,所以《詩經》是樂歌。徒歌是向來不受人注意的,流傳下來的無名氏詩歌亦皆為樂歌;春秋時的徒歌不會特使人注意而結集入《詩經》,所以《詩經》是樂歌。”⑤《顧頡剛民俗學論集》,錢小柏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頁、251頁、252-253頁、266頁、282頁。
可堪注意的是,顧頡剛在文中以為“賦詩”就是“樂詩”,這與梁啟超在《釋“四詩”名義》中所認同的“賦詩即是不歌而誦”針鋒相對,而朱謙之也承續了顧頡剛的觀點,如他在文中寫到:
“按賦詩即樂歌,雖班固說過‘不歌而誦謂之賦’(《藝文志·序》),但那是漢人妄生分別的曲解,其實現在學者如顧頡剛先生已經告訴我們:‘歌與誦原是互文’;(如從動詞方面看,襄十四年傳說:‘公使歌之,遂誦之’;襄二十八年傳說:‘使工為之誦’;襄二十九年傳說:‘使工為之歌’;可見是同義的。再從名詞方面看,《小雅·節南山》說:‘家父作誦’;《四月》說:‘君子作歌’;《大雅·崧高》和《烝民》說:‘吉甫作誦’;《桑柔》說:‘既作爾歌’;可見也是同義的。‘誦’與‘頌’通,頌即周頌魯頌之頌,也即歌頌之頌。)可見賦詩即是樂歌了。”⑥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頁。
而實際上,以上整段話都是顧頡剛的觀點。至于“賦詩”是否就是“樂詩”,既重要,又難解。那么,既然朱謙之承認《詩經》所錄都是樂詩,卻又將之分列為“歌詩”“賦詩”,其間的差異他并未說明。顯然,朱謙之對顧頡剛的研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寫到:
“近吾友顧頡剛先生發表一篇《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他是從春秋時的徒歌上,《詩經》的本身上,漢代以來的樂府和古代流傳下來的無名氏的詩篇上,從這各種事實來證明《詩經》是樂歌。雖然,顧先生不是有意作音樂文學運動的人,但他這種根本主張,也可算得比許多文學史家有精義多了。”①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頁、82頁、79-80頁、65頁。
四
就“新聲”與“鄭聲”的話題,也可以將顧頡剛的文章與朱謙之的文章作一對比,對理解詩樂關系也有幫助。顧頡剛從《國語》中的話,推論出春秋末葉出現的新聲的音樂特征,諸如“變簡單為復雜,變質直為細致”,②錢小柏編:《顧頡剛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頁。并對新聲的藝術價值給予肯定。但是,究竟《國語·晉語》里的“新聲”是否即《論語》里的“鄭聲”,或“鄭聲”還是另外一種樂調,顧頡剛也表示“未能解決”。
后來朱謙之關于“鄭聲”與“鄭樂”的分辨大致也就是從這里得到了啟發,如朱謙之說“‘鄭聲'是專當音樂聽的,是不合于文學的,反之,‘鄭樂'——現在《詩經》里的《鄭風》——是詩歌音樂合一的”③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頁、82頁、79-80頁、65頁。。問題是,即如朱謙之所說,則《小雅》中的六篇有目無辭的笙詩又怎么解釋呢?所以,筆者認為朱謙之沒有注意到“鄭聲”與“新聲”是否有別,而是直接將顧頡剛對“新聲”的評價代之以對“鄭聲”的評價。他甚至將音樂與政治結合起來論述,說“鄭聲是沒有文學的音樂,所以他的聲調,只是使人聽了神魂顛倒,一點沒有什幺好處,并且這種音樂,不但不算‘新聲',并且分明是‘亡國之音',分明是音樂上的復辟運動”④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頁、82頁、79-80頁、65頁。。也是因其一貫提倡合樂的“音樂文學”,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論調相反,顧頡剛的分析更為合理,也不排除鄭聲是一種旖旎萎靡的曲調的可能,所以孔子從禮的出發,對“鄭聲”深惡痛絕,而“鄭聲”與“新聲”也有可能是不同的。
此外,王國維的一些觀點對朱謙之也產生了影響,如朱謙之在文中所說:“我們現在要替詩樂作一個考證,當然免不了要拿這些冠冕堂皇的‘詩禮'來研究一番,研究的材料,最好的是阮元的《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說》和王國維的《樂詩考略》了。”⑤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頁、82頁、79-80頁、65頁。朱謙之在《論詩樂》一文中,按照禮樂的等級觀念,將“升歌之詩”分為“士大夫用《小雅》、諸侯燕士大夫也用《小雅》、兩君相見用《大雅》或用《頌》、天子用《頌》”,⑥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頁、82頁、79-80頁、65頁。并述說“臺上升歌”與“臺下間歌”之分別,這些都是源于王國維的觀點。
再比如《論詩樂》的第二部分《詩樂考》,通過先秦古文獻詳考詩與樂的關系,在清人阮元《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說》所謂“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⑦揅《經室集》(全兩冊)(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上海: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78-82頁。與王國維《樂詩考略》中所謂的“金奏之詩”“升歌之詩”“笙之詩”“管之詩”“舞之詩”分類的基礎上,又做了一番梳理,并從當時的音樂與詩的活動中總結出“歌詩、賦詩、奏詩、笙詩、管詩、籥詩”等六種情況,但是筆者認為這種分法欠妥當,如歌詩與賦詩的區別在哪里?籥籥也是管樂器,那么管詩與詩的區別又為何,朱謙之并未說明。當然,他比較早的關注到《詩經》中的樂器問題,將之細分為三類共二十九種,其一是主要樂器,如鞉、鼓、椌、楬、塤、篪等,其二是用來伴奏的,如鐘、磬、竽、瑟等,其三是用于舞蹈中的干、戚、旄、狄等。其實,王國維的文章也提到過樂器的使用問題,如“凡金奏之樂用鐘鼓,天子、諸侯全用之,大夫、士鼓而已。歌用瑟及搏拊,笙與管皆如其名,舞則《大武》用干戚,《大夏》用羽籥”。⑧《觀堂集林》(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頁。
朱謙之在《論詩樂》第六部分“論風雅頌”中,論及《雅》時,主要用到了兩個成果,其一就是王國維的《漢以后所傳周樂考》,以此得出“可見所謂二十六篇的《雅》,早已零亂不堪”。⑨朱謙之:《音樂的文學小史》,上海:泰東圖書局,1925年版,第105-106頁。論及《頌》時,朱謙之多處借鑒王國維的說法,但是他并不同意王國維所謂的“以名頌而皆視為舞詩,未免執一之見”,①《觀堂集林》(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頁。因此說“其實頌字的意義,雖也有音樂上的特點,而自以解作舞詩為最妥,王氏的話,未免阿其所好了”。②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頁、57頁、56頁。
五
朱謙之結合傳統的解經文獻,條分縷析、歸納總結,并且鉆研了一些新的論題的同時,也注意古史辨派的學術成果。他明確的提出了“《詩經》之音樂的研究法”,即“直接從音樂方面去觀察”。③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頁、57頁、56頁。但問題是《詩經》的音樂已經遺失,如何從音樂方面去觀察?因而,筆者認為“《詩經》之音樂的研究”,并不可能成為一種獨立的角度或方法,它只是一種可以與文本相結合的維度或者參看系數,并進而成為進入《詩經》所處歷史情景的一個“媒介”或者一個“面向”。面對《詩經》的文本,更為可行的似乎是從文學、聲韻學、考據學的角度來理解當時的音樂文化,尤其是文學與音樂的關系,而追尋《詩經》的音樂形態似乎需要在一個“想象的空間”里完成。朱謙之的才華在于,正是從單部的音樂文學,也是“最好最古的音樂文學”④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頁、57頁、56頁。——《詩經》開始,逐步構建起“音樂文學史”的宏大結構,進而樹立了“音樂文學的進化史觀”⑤比如朱謙之所謂的“所以,文學史和音樂史是同時合一并進的,如一個時代的音樂進化了,便文學也跟著進化,另發展一種新文學,而前代的舊文學就不能普遍,只好供好古家所賞玩,便成為貴族文學了”,參看《音樂的文學小史》,第76頁或《中國音樂文學史》,第49頁。再比如他說“不但如此,文學的起源就是樂器的起源,文學進化的大勢,也是跟著樂器的進化而進化的”。這都是朱謙之富于獨創性的觀念。。
留生,中央音樂學院2013級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方向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