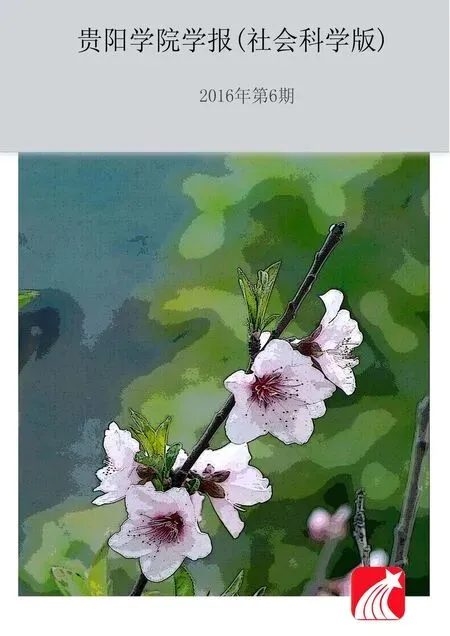略論“包容型”刑法文化的特征與意義
陳 鴻
(廣東司法警官職業(yè)學(xué)院,廣東 廣州 510520)
略論“包容型”刑法文化的特征與意義
陳 鴻
(廣東司法警官職業(yè)學(xué)院,廣東 廣州 510520)
“包容型”刑法文化是一種涵容善良仁愛的群體化刑法精神模式,也是一種特殊的教化公民、預(yù)防犯罪的過程。謙抑性、人道性、和合性是包容型刑法文化的基本內(nèi)涵及特征。弘揚“包容型”刑法文化,有利于我國公民更深入認識刑法的精神實質(zhì),有利于我國社會穩(wěn)定、民族興旺與國家強盛,有利于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的實現(xiàn)。
包容;刑法文化;謙抑性;人道性;和合性
刑法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在刑法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是國家相關(guān)法律設(shè)施、刑法規(guī)范等外化法律實體的內(nèi)在精神部分,具體地表現(xiàn)為一個國家的犯罪觀與刑罰觀。不同的刑法文化孕育著不同的犯罪觀、刑罰觀。犯罪觀、刑罰觀影響甚至決定犯罪預(yù)防與控制的不同方式,從而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刑事法制與刑事政策。綜觀當前刑法文化領(lǐng)域,國外的刑法文化大致可以分為人權(quán)型刑法文化、經(jīng)濟型刑法文化、專政型刑法文化;在我國,傳統(tǒng)的刑法文化主要有工具主義刑法文化、重刑主義刑法文化、泛道德主義刑法文化,也存在“天人合一”的自然主義刑法文化。但無論是中國傳統(tǒng)刑法文化還是西方社會的刑法文化,其所彰顯的不外乎人類共同的東西——人性以及不同國度與民族中特色的東西——習俗。在當今國際關(guān)系日趨復(fù)雜的環(huán)境下,在人們對傳統(tǒng)封建的重刑型刑法文化與現(xiàn)代西方雙重標準的人權(quán)型刑法文化都開始質(zhì)疑的情況下,筆者以為,“包容型”刑法文化是當今社會刑法文化發(fā)展的基本方向,也是我國刑法文化的時代注腳。
一、“包容型”刑法文化的特征
筆者所稱“包容型”刑法文化,是指注重謙抑性、人道性、和合性的刑法之群體性精神模式,以及基于人權(quán)、人性的基本價值預(yù)設(shè),以多元化、均衡化、人權(quán)價值最大化的原則教化公民、預(yù)防犯罪的過程。
(一)“包容型”刑法文化是一種涵容善良仁愛的群體化刑法精神模式
作為刑法實體的內(nèi)在精神部分,首先,“包容型”刑法文化是一種特殊的群體化精神模式,亦即特殊的犯罪觀、刑罰觀及其方法論之體系。這種體系應(yīng)當涵容善良仁愛,具有鮮明的謙抑性、人道性、和合性的內(nèi)涵特征。
1. 刑法謙抑觀—“對盡量少的人定罪處刑”
謙抑,亦即謙讓、退卻之意。所謂刑法的謙抑觀(The principal of compress and modesty),按照通說,即指刑罰的必要性、非濫用性的基本觀點。日本主觀主義大師宮本英修博士在其專著《刑法綱要》中最早提出了刑法的“謙抑性”一詞;在我國,甘雨沛教授和何鵬教授則最早提出了“收縮或壓縮”刑法的刑法謙抑精神說。其后,專家學(xué)者對于謙抑性的論述漸趨系統(tǒng)化。我國當代著名刑法學(xué)者陳興良教授對刑法的謙抑性從立法角度作了系統(tǒng)論述。他認為,刑法的謙抑性,即刑法的經(jīng)濟性或者節(jié)儉性,是指“立法者應(yīng)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其他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的預(yù)防和控制犯罪。”[1]日本著名刑法學(xué)者平野龍一則從司法的角度闡釋了刑法的謙抑性,他明確指出:刑事制裁的成本要高于其他任何制裁方式的成本,因此,“即使刑法侵害或威脅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須直接動用刑法。可能的話,采取其他社會統(tǒng)制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說,只有在其他社會統(tǒng)制手段不充分時,或者其他社會統(tǒng)制手段(私刑)過于強烈、有代之以刑罰的必要時,才可以動用刑法。這叫刑罰的補充性或者謙抑性。”[2]
“包容型”刑法文化的謙抑觀,主要表現(xiàn)為對刑罰對象范圍的包容(寬容)——“對盡量少的人定罪處刑”,亦即讓盡量多的人被包容在正常社會成員之內(nèi),被排除在刑罰對象范圍之外。其一,從刑法與他法的關(guān)系看,刑法是一個國家其他所有法律的保障法,是(非戰(zhàn)爭時期)維系與規(guī)范社會基本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線。也就是說,只有在對于那些社會秩序—法秩序侵犯行為人缺乏更好的遏制辦法時,才不得不搬出刑罰這尊大神。刑罰用得太濫,也就不神了。其二,從犯罪心理學(xué)角度看,犯罪行為是行為人在其“病態(tài)心理”驅(qū)動下實施的一種“病態(tài)”行為。對于“病人”,最好的辦法不是將這個“病人”一棒子打死,而是設(shè)法找到其病因,然后因病施治。亦即應(yīng)給予法秩序侵害行為人一個“治病”機會——改過自新的機會,一個盡量好的“治病”環(huán)境—非監(jiān)禁的環(huán)境。其三,從刑罰功能本身看,刑罰阻止犯罪、預(yù)防犯罪功能有限。刑罰本身就是一種國家之惡,刑罰具有明顯的正反兩面性。正如德國刑法學(xué)家耶林所言:“刑罰如兩刃之劍,用之不得其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3]用得適度得當,刑罰是阻止犯罪、預(yù)防犯罪的正能量;用得不當,刑罰是弊大于利的有害社會負能量。不容否認,如何正確把握刑罰的度,是現(xiàn)實社會中的難題。中外歷史證明,刑罰的不當,即刑罰的過厲過濫或者過緩過少(更多的是前者),往往給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造成明顯的消極影響。
“對盡量少的人定罪處刑”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對盡量少的人定罪”。對于犯罪證據(jù)不足,尤其是犯罪關(guān)鍵證據(jù)缺乏者,堅持“疑罪從無”;對于符合刑法形式犯罪構(gòu)成,但是主觀惡性較少、“情節(jié)顯著輕微”者,不以(或不宜)犯罪論處。其二,“對盡量少的人適用刑罰”。亦即對于被判決有罪者,刑罰是重要選項但非必要選項。對于輕微犯罪者以及后果不是十分嚴重的過失犯罪者,只要悔改態(tài)度好、不具備再次犯罪危險或者犯罪能力,獲得受害方諒解的,應(yīng)以非刑罰方法處置。誠然,此種“對盡量少的人定罪”、“對盡量少的人刑罰”之刑法謙抑觀,亦為刑法之善的表現(xiàn)。
2.刑罰的人道觀—“對犯罪人適用盡量輕緩之刑”
人道(humanity),顧名思義,即關(guān)愛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權(quán)利與價值的道德。人道觀,或稱之為人道主義(Humansnistas),亦即注重人的本性、人的權(quán)利、人的價值之觀點。蘇聯(lián)哲學(xué)家布耶娃認為,“人道主義意味著‘人是最高價值這一原則’不容懷疑”。 1974年第15版的英國《新大英百科全書》寫道:人道主義是一種把人和人的價值置于首位的概念。把人和人的價值放在首位意味著“生存主義的第一原則”[4]。
“包容型”刑法文化的刑罰人道觀,是指在刑事法律之制定與適用過程中,注重如下三大體現(xiàn):體現(xiàn)對人的生命權(quán)、健康權(quán)等最基本權(quán)利的尊重,將其放在首位;體現(xiàn)人的可塑求變、趨利避害屬性即人性之基本規(guī)律,弘揚人性的積極面并抑制人性的消極面;體現(xiàn)人的追求成功之價值屬性,弱化刑罰的懲戒功能并強化刑罰的改造功能。概言之,刑罰人道觀表現(xiàn)為對犯罪人處罰程度的包容—“對犯罪人適用盡量輕緩之罰”。所謂輕緩,一是厲度的輕緩,盡量不判死刑、堅決避免酷刑;二是速度的輕緩,盡量避免超短自由刑,適度延長重罪的自由刑;三是環(huán)境的輕緩,適度擴大緩刑、管制以及監(jiān)外執(zhí)行。此謂刑罰之仁。
(1)原則上反對死刑
死刑是對人的最重要、最基本權(quán)利的踐踏,是對公正與社會契約的違背。其一,死刑并不能產(chǎn)生最佳威嚇效果。從對人的心理威懾效果看,刑罰的延續(xù)性遠過于刑罰的嚴厲性。其二,死刑使得錯誤的審判完全失去糾正的機會。自從刑法誕生以來,從來就沒有哪個國家與地區(qū)能與錯誤審判絕緣。另一方面,“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而索樂,辱而求榮”[5]。一個人因為過錯或者罪惡而受到一定懲罰時,其本身往往具有進取、求榮的內(nèi)在動力,但是一個死刑卻一次性剝奪了其全部機會。從這個角度看,死刑無論誤判與否,都在相對程度上阻礙了社會正義的實現(xiàn)。因此,“當死刑不是必需時,它是非正義的”[6]。其三,死刑會毒化人們的心靈。死刑會引起人們對犯罪人的同情,會強化人們尤其是犯罪方“冤冤相報”的仇恨心理。
(2)堅決禁止酷刑
酷刑,既造成人的身心極大痛苦,也是對人的健康權(quán)的嚴重侵犯、對人格的極端侮辱。因此,刑罰的人道觀旗幟鮮明反對酷刑。其一,反對刑訊逼供。正如貝卡利亞所言,這種方法能保證強壯的罪犯(能夠經(jīng)受酷刑而不招)獲得釋放,使軟弱的無辜者(經(jīng)受不起酷刑而屈打成招)被定罪處罰。因此,刑訊逼供除了對人身心的傷害,就是冤假錯案的溫床。其二,反對嚴酷刑罰。一方面,酷刑之刑罰并不能更好地控制與預(yù)防犯罪。“嚴刑峻法不僅不能有效遏制犯罪,而且還會造成這樣一種局面:罪犯所面臨的惡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規(guī)避刑罰。為了擺脫對一次罪行的刑罰,人們會犯下更多的罪行”[7]。另一方面,反對酷刑已經(jīng)成為世界性潮流。1984年召開的聯(lián)合國反酷刑大會明確聲明:“沒有什么例外情況可以使酷刑成為一種正義的行為,無論是戰(zhàn)爭狀態(tài),還是戰(zhàn)爭威脅;無論是內(nèi)部的政治動蕩,還是任何公共的緊急事件。”而且,大會制定的《聯(lián)合國反酷刑公約》于1984年10月開始實施,于1988年11月3日在我國生效。
(3)適度擴大緩刑、管制等環(huán)境輕緩刑
我國刑法第67明確規(guī)定對于被判處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如果確有悔罪表現(xiàn),且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適用緩刑。對于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短期自由刑適度擴大緩刑、管制刑以及特殊情形下的監(jiān)外執(zhí)行,不僅可以節(jié)省國家的經(jīng)濟開支與司法資源,更重要的在于可以讓緩刑犯避免監(jiān)所的“交叉感染”,可以繼續(xù)與親人在一起,這些均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國內(nèi)外有關(guān)資料研究表明,被執(zhí)行緩刑等環(huán)境輕緩之刑者,其再犯率普遍較低,具有較好的社會效應(yīng)。
(4)盡量避免超短自由刑,逐步增加長期刑
筆者以為,超短自由刑不利于罪犯的改造。主要依據(jù)有二:其一,超短刑期并不人道。人道人道,人性之道。刑罰的人道,不但注重人的尊嚴與價值,還在于合乎人的本性。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之基本表現(xiàn)。超短的自由刑并不能讓犯罪人感覺服刑是明顯的害,并不感覺服刑是太大的代價,因此其規(guī)避犯罪之意識同樣不強烈,不利于改造。其二,超短刑期堵塞了犯罪人改造的時空與過程。在當今的各類犯罪中,絕大多數(shù)屬于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在犯罪人的“病態(tài)心理”或者極端思想引導(dǎo)下出現(xiàn)的極端行為。而人的病態(tài)心理或者極端錯誤思想的轉(zhuǎn)變是一個漸變過程,需要時間的磨合。因此,十天半月、一月兩月等超短刑期對犯罪人的改造的效果是令人懷疑的。國家在杜絕死刑、酷刑的同時,應(yīng)嚴格限制超短自由刑、增設(shè)限制減刑的長期刑以及終身監(jiān)禁刑、從嚴把握重罪的減刑、假釋的程度與速度。2015年11月開始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在貪污罪、受賄罪的處罰中增設(shè)了終身監(jiān)禁刑,顯然是我國刑罰改革的一個良好開端。
3.刑法的和合觀—“對所有犯罪人處施盡量促生罪刑”
和者,相應(yīng)、相配之意;合者,結(jié)合、相生之謂。所謂刑法的“和合觀”,亦即堅持和合協(xié)同、有序?qū)ΨQ、整體和諧、融合出新的罪刑觀。 “和合辯證思維是中華文化之根”[8],也是當代中國法律文化精神的體現(xiàn)。概括說來,刑法的和合觀主要表現(xiàn)為對定罪處刑施刑科學(xué)性的包容——“對所有犯罪人處施盡量促生罪刑”。所謂“促生罪刑”,就是“罪刑適宜,由刑促生”,亦即通過一個“弘揚公正、合乎情理、注重過程”的罪刑配置、實施體系,促使犯罪人中的盡量多數(shù)真心服法,誠心服刑,致力改造成社會新人,獲取新生。此為刑法之良,亦涵刑法之愛。具體包括如下主要內(nèi)容:
(1)和合立法觀
立法的和合,主要在于罪名的完善以及罪與刑的合理對應(yīng)。其一,罪名應(yīng)當全面完整覆蓋現(xiàn)有各種危害行為。或者說,任何一種嚴重社會危害行為都有一個罪名與之搭配對應(yīng),從而做到“法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其二,輕重罪名與不同刑種、刑度的合理對應(yīng)。應(yīng)當針對不同的罪名、不同危害結(jié)果、不同主觀惡意程度做到調(diào)配合理度、實用度的最大化,從而做到“罪刑對價,輕重有別,嚴而不厲,簡而不繁”。其三,注重過程的體現(xiàn)。勿需置疑,罪犯的改造是一個長期過程;刑法的完善發(fā)展也是一個長期過程。因此,死刑的廢除、自由刑期的延長,不能一步到位,不能大躍進,應(yīng)當根據(jù)國情循序漸進。應(yīng)該說,我國刑法從1979年第一版的100多個罪名到1997年第二版的400余個罪名,從第八個刑法修正案后的450余個罪名到第九個刑法修正案后的460余個罪名,以及兜底性罪名的出現(xiàn)等,表明我國在罪名的系統(tǒng)完善上,具有明顯的持續(xù)性的進步。另外,隨著刑罰的不斷修正,保留死刑的罪名從1979年的68個減少到第八個刑法修正案后的55個,再到第九個刑法修正案后的46個以及巨額財產(chǎn)來歷不明罪、行賄罪等個別罪名量刑的適度加重,表明我國罪刑調(diào)配的合理性得到了增強。但是,與美國、德國等發(fā)達法治國家相比,我國的刑事立法在罪名的無縫對接、處罰的簡約科學(xué)等方面還有較大的和合空間。
(2)和合司法觀
在包容型刑罰觀看來,司法的和合,重在“有據(jù)、有節(jié)、有情的融合”。其一,就法院來說,堅持“科學(xué)判決”。刑事案件的判決應(yīng)嚴格貫徹“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原則,證據(jù)不足,應(yīng)堅持“疑罪從無”;在犯罪事實清楚無誤的前提下,除非屬于絕對法定刑,量刑盡量不頂格判處,一個行為不管同時符合多少個罪名,均杜絕加重處罰、數(shù)罪并罰;對于危害較輕、善后工作盡心盡意,已經(jīng)獲得受害方諒解的情形,法院可以在雙方取得一致的條件下,主持實施刑事和解;相反,對于罪行惡意很深、悔意不足、民憤甚大之人,即便其善鉆法律之空子,也不能輕易讓其逍遙于法網(wǎng)之外。法院的最終定罪量刑應(yīng)當讓犯罪人、受害人認為在理合理,口服心服。其二,就公安、監(jiān)所來說,堅持“人性執(zhí)刑”。首先,應(yīng)當嚴格依據(jù)法院的判決執(zhí)行刑罰,讓犯罪人感受到服刑是自己所犯罪行的應(yīng)有代價,這是必須明確的基本前提。必須避免“一味寬緩優(yōu)待、甚至變相享受”的刑罰執(zhí)行方式。痛苦與代價是犯罪人思想震動、轉(zhuǎn)變的重要條件,只有必要的痛苦與代價,才能有效促使犯罪人“避犯罪之害,趨新生之利”;其次,刑罰執(zhí)行部門必須避免簡單的“冷、厲、壓”方式,注重改善軟硬設(shè)施,營造一個人性化的執(zhí)法環(huán)境,充分利用刑法關(guān)于減刑、監(jiān)外執(zhí)行、假釋等成文規(guī)定以及相關(guān)刑事政策;再次,充分利用社會關(guān)愛力量。“社會化是實現(xiàn)罪犯改造人性化的重要路徑”[9],自始至終要充分調(diào)動犯罪人的親朋好友以及社會諸方的關(guān)愛力量。通過上述人性化執(zhí)刑舉措,讓犯罪人在服刑中充滿動力,看到希望。
(二)“包容型”刑法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教化公民、預(yù)防犯罪的過程
1.文化的本質(zhì)就是教化人的過程
文化可以從三個方面予以理解。其一,從實體層面看,文化是指人類創(chuàng)造的一切有形產(chǎn)品的總和。其二,從理論的層面看,文化是指一定社會的意識觀念形態(tài),是一定社會的環(huán)境因素在人的觀念上的反映,是一種由物及人的人化過程及其狀態(tài),主要包括風俗習慣、學(xué)術(shù)思想、宗教信仰、文學(xué)藝術(shù)以及一切典章制度等。其三,從功能的意義上看,文化有如《周易》所云:“觀乎天文以觀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以“文化”來教化天下[10],在這里,文化就是一種管理手段,亦即通過既定的精神理念、價值觀念來規(guī)范人、調(diào)控人、改變?nèi)耍嗉唇袒?化人)的過程。
2.“包容型”刑法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教化公民、預(yù)防犯罪的過程
刑罰,作為一種特殊典章制度,其判決與執(zhí)行過程是一種特殊的“化人”過程。在我國長達數(shù)千年的封建社會,刑法的實質(zhì)就是儒家化的“倫理刑法”,“表面上為明刑弼教,骨子里則以禮入法”[11],刑法之罰,其主要目的在于教化百姓遵守封建禮教秩序,服從封建統(tǒng)治。在當前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刑罰制度本身則具有多種積極功能,其中教育改造功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包容型”刑法文化氛圍憑其謙抑性、人道性、和合性的特點優(yōu)勢,有利于導(dǎo)引公民遵紀守法,有利于增強犯罪人服刑改造的內(nèi)在動力,更好更快地將罪犯教育改造成社會新人(教化人)。
二、“包容型”刑法文化的意義
(一)“包容型”刑法文化有利于人們更深入認識刑法的精神實質(zhì)
刑法現(xiàn)象是一種十分復(fù)雜的社會意識現(xiàn)象與過程,要認清其精神實質(zhì),有賴多層次多角度的考察。從結(jié)構(gòu)層面看,刑法可以分為顯性層次與隱性層次。通常人們直觀的刑法立法機構(gòu)、司法部門以及現(xiàn)成的刑法條文及其解釋,只不過是刑法的外化、物化部分—顯性層次,人們對它們的認識最多也就是“知其然”的淺層面,由此產(chǎn)生的諸如各種立法問題、司法問題或困惑并不能得到很好解決。有專家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外化物化的刑法就好像木偶,而刑法文化才是木偶表演后面的提線與操作者。也就是說,刑法文化是刑法的隱性部分,只有通過它才能了解刑法內(nèi)在運作機制與規(guī)律,才能把握刑法認識與實踐的精神實質(zhì)與核心靈魂,進而讓人們“知其所以然”。建立在中外刑法文化比較與我國國情基礎(chǔ)上“包容型”刑法文化,自然有助于人們認識刑法的精神實質(zhì)及其運行規(guī)律。
(二)“包容型”刑法文化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與民族興旺、國家強盛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zhuǎn)型期、改革攻堅期、矛盾復(fù)雜期、風險積累期。期間,隨著經(jīng)濟的社會化、人口的城市化以及交流的信息化、自由化,諸如單位、戶籍等傳統(tǒng)社會控制手段逐步弱化甚至失靈,而新的社會治理與管控模式尚未完全建立;另一方面,公民收入呈現(xiàn)兩極分化態(tài)勢,國外敵對勢力十分猖獗。在這種環(huán)境下,一個小小問題,處置不善,往往演化成一個破壞性巨大的群體性事件或者“獨狼”現(xiàn)象,[12]從而導(dǎo)致各類犯罪現(xiàn)象高發(fā)。如何善處當今高發(fā)的各類犯罪?無疑,在非戰(zhàn)爭時期,刑法是處理這些問題的最重要手段。然而,無數(shù)事實表明,一味的酷刑、死刑,或許能夠短期治標,但絕對不能治本。即便是我國1983年開始布署的定期“嚴打”(從重從快嚴厲打擊重大犯罪)運動,其穩(wěn)定社會的邊際效益快速下降,甚至出現(xiàn)弊大于利的狀況。依據(jù)1983年~2001年《中國法律年鑒》統(tǒng)計,1982年至1986年,全國公安刑事立案從748476起降到547115起;但是1987年突升至827594起,以后一直在高位徘徊,2001年高達4457579起。因而,重刑、酷刑、濫刑等等,都不是解決高發(fā)犯罪問題的最好辦法。盡最大可能保護絕大多數(shù),堅決處置窮兇極惡的一小撮,盡最大努力分化、改造犯罪者中的最大部分,這才是解決高發(fā)犯罪問題的有效舉措。而這,正是“包容型”刑法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包容型”刑法文化通過對刑罰的謙抑、人道、和合的闡釋,讓公民充分認識到基本刑罰的必要性、代價性,從而努力避免犯罪,尤其努力避免犯重罪;也讓犯罪人認識到刑罰的必要性、有限性以及執(zhí)刑過程的人道性,從而增進對服刑的理解,使其在服刑中看到希望,進而專心于勞動改造,早日成為重新適應(yīng)社會、有益于社會的新人,降低再犯率。因此,“包容型”刑法文化對維護、促進社會的穩(wěn)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國歷史證明,包容型刑法及其執(zhí)法理念有利于民族興旺、國家強盛。一方面,我國歷史上兩個大一統(tǒng)的短命王朝,其短命大都與暴政、酷刑相關(guān)。一是秦朝。從秦始皇首建大一統(tǒng)到秦二世亡國,總計不過15年時間。期間,“繁刑嚴誅,吏治刻深”,“以刑殺為威”[13](秦朝的此種做法還成為漢初統(tǒng)治者認定為秦二世亡國的教訓(xùn)[14])。二是隋朝。從隋文帝楊堅強勢建國,到隋煬帝楊廣被殺亡國,也僅有37年時間。雖然隋煬帝改革失去地主貴族集團支持,是其亡國的重要因素,但是隋煬帝重役、酷刑、濫殺等無所不用其極的執(zhí)政方式讓其徹底失去民心,是其滅亡的根本性原因。比如在平定楊玄感時竟認為:“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后”[15]。另一方面,我國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四大盛世王朝。雖然“盛世”的形成,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但翻開我國的法律思想史不難發(fā)現(xiàn),我國的每一個盛世,都與謙抑、人道的刑法思想與執(zhí)法理念有著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漢代“文景之治”期間,漢文帝先后廢除了殘忍的因言論而治罪的“誹謗妖言法”、因一人犯罪而株連九族的“相坐法”,漢景帝廢除了夏商、秦朝以來的酷刑用具,引領(lǐng)了執(zhí)刑人道化的改革;唐朝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期間,從唐太宗到唐玄宗,都信奉“以仁為本,以刑為末”的刑罰理念;至于清朝的“康乾盛世”及其延續(xù),諸多學(xué)者以為,康熙及其以后皇帝倡導(dǎo)的具有前瞻性、開創(chuàng)性的“罪疑惟輕”的刑罰思想以及“以德化民,以刑弼教”[16]的刑法理念功不可沒。
(三)“包容型”刑法文化有利于建設(sh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的實現(xiàn)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sh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社會主義法治是人民民主的法治。人民依法當家作主,人民民主是法治的目的和核心內(nèi)容,這里就有一個關(guān)鍵性的問題——公民的民主法治素養(yǎng)問題。公民沒有良好的民主素質(zhì)與法律素養(yǎng),法治國家只是一紙畫餅,一幕海市蜃樓。公民良好的民主法治素養(yǎng)包括樹立良好的法律理念、法律思維習慣以及良好的法律運用操作能力。首先,公民必須樹立良好的法律理念、法律習慣,這是基本前提與關(guān)鍵所在。人是理解的動物、機會主義的動物,只有懂得法律的重要,人才會去學(xué)法、用法。而法律文化通過法律內(nèi)在精神本質(zhì)、基本功能的探究,可以讓公民真正懂得法律(良法)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進而逐步樹立起法律意識、法律理念、法律習慣。其次,公民必須具備良好的法律運用操作能力。法律文化通過不同法律的比較,通過法律的宣傳普及,營造一個法律的氛圍。這個氛圍,有利于促進公民自覺、不自覺接觸法律、學(xué)習法律、熟悉法律、運用法律。刑法,作為國家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作為其他所有法律的保障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包容型”刑法文化有利于加深公民對國家現(xiàn)行刑法的理解,有利于加深對國家刑事立法、司法改革的理解,其對培養(yǎng)公民法治素養(yǎng)的積極作用不可或缺。
[1]陳興良.刑法的哲學(xué)[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7:6.
[2](日)大谷實.刑事政策學(xu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6.
[3]陳興良.刑法的價值構(gòu)造[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8:10.
[4](法)薩特.存在主義就是一種人道主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30.
[5]商鞅.商君書.算地第六.古詩文網(wǎng)[EB/OL].(2013-11-19) [2106-11-01]http://www.gushiwen.org/guwen/shangjun.aspx.
[6]林海.貝卡利亞.向酷刑與死刑宣戰(zhàn)的意大利貴族[J].法律與生活,2015(13):51.
[7]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59.
[8]左亞文.和合思想的當代闡釋[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17-218.
[9]李雪峰,范輝清.人性化—罪犯改造理論的基石[EB/OL].(2014-10-26) [2106-11-01]http://blog.163.com/xuefeng,2014.
[10]刑法基礎(chǔ)理論探索[M].趙秉志,主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64.
[11]任喜榮.倫理刑法及其終結(jié)[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1.
[12]陳鴻.當前我國暴恐犯罪的新特點及其應(yīng)對[J].廣州大學(xué)學(xué)報,2016(8)34.
[13]楊永泉.兩漢以學(xué)社會批判愢潮管窺[J].南京社會科學(xué),2008(6):52.
[14]張武舉.刑法的倫理基礎(chǔ)[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45.
[15]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82[EB/OL].(2013-07-27) [2106-11-01]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1zztj/179.htm.
[16]陳鴻.略論刑法特性與社會和諧功能[J].政法學(xué)刊,2007(12):39.
[責任編輯 何志玉]
On the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of “Tolerance” of Criminal Culture
CHEN Hong
(Guangdong Justice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510520, Guangdong, China )
The “tolerance” of criminal culture is a group spirit mode of criminal law which is featured with kindness and benevolence. It is also a special process of enlightening citizen and preventing crime. Modesty, humanity and harmony are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lerance” of criminal culture. To promote the “tolerance” of criminal culture will be propitious for the citizen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criminal law, for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f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goal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ruled by law.
tolerance; criminal culture; modesty; humanity; harmony
2016-10-10
陳 鴻(1968-),男,湖南邵陽人,廣東司法警官職業(yè)學(xué)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學(xué)與法律文化。
D914
A
1673-6133(2016)06-00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