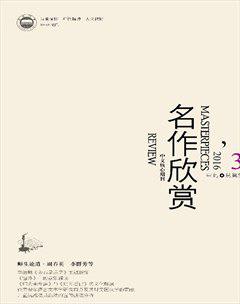論勞費爾語言文字學研究特點及其對美國漢學的貢獻
摘 要:德裔美籍漢學家伯托爾德·勞費爾以其卓絕的語言學研究著稱,他的研究頗具特色,如:語言學對他而言既是研究工具,又是研究目的和旨趣所在;與文獻學研究結合進行;重細節和實證,不重理論建構;與歷史學相結合;跨學科的研究特點;大文明觀的研究視角等。他在語言學方面的成就,為美國學者的研究奠定了扎實的語言文獻基礎,其跨學科研究方法亦對美國漢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伯托爾德·勞費爾 語言文字學 研究特點 貢獻
德裔美籍學者伯托爾德·勞費爾(Berthold Laufer,1874—1934)可謂20世紀初期美國最杰出的漢學家之一,為美國漢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縱觀勞費爾一生,他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貢獻給了學術:在歐洲,他先后就學于柏林大學、萊比錫大學,并于1897年獲得了萊比錫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在此期間他花費了大量時間來學習必要的語言學知識,掌握了波斯語、梵文、巴利語、馬來語、漢語、日語、滿語、蒙古語、達羅毗荼諸語、藏語等多種語言,為日后的語言文字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美國,他先后組織和參與了杰蘇普北太平洋考察隊(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席福考察隊(Jacob H. Schiff Expedition)、布來克斯通考察隊(Blackstone Expedition)等科學考察,為美國帶回了大量漢、藏文典籍和珍稀古董。這些經歷使他在美國逐漸站穩了腳跟,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做短暫停留后,他應邀赴芝加哥費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出任人類學部主任,美國便成為他學術研究的主要陣地。{1}
美國是一個后起資本主義國家,其漢學研究起步相對較晚,遠遠落后于歐洲。20世紀初期,美國雖已有六七十年的侵華歷史,但他們所能舉出的漢學家卻仍然寥寥無幾。最早研究中國學問的美國人是傳教士衛三畏(S. Wells William,1812—1884),其研究成果集中于1848年所出的《中國總論》(Middle Kingdom)一書。繼他之后尚有柔克義(W.W.Rockhill)、費諾羅薩(E.F.Fenollosa)等,“至于人才之豐澀,造詣之淺深,以視歐洲先進諸國,固不可同日而語”{2}。當時美國正在加緊爭奪遠東霸權,為了與當地人打交道時更加得心應手,它的一些學術機構和學者出于功利主義目的,一面開始研究這些地區的歷史文化,一面從歐洲(主要是德國)引進漢學家以發展美國的漢學,勞費爾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進入美國學術界的。雖然受過良好歐洲傳統漢學訓練的勞費爾根本不可能很好地適應乃至認同美國學術界的功利主義氛圍,在美國的漢學研究領域里他也時常是孤立的,但他仍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大量學術研究,甚至有過一天工作16個小時的記錄。他杰出的研究成果填補了美國學術界的諸多空白,極大推動了美國漢學的發展。
一、勞費爾語言文字學研究特點
勞費爾一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出版論著逾兩百種{3},著作內容包羅萬象,地域上覆蓋了中國、印度、東西伯利亞、日本、薩哈林島、菲律賓群島以及太平洋群島等廣大地區,研究興趣則集中在當地文化的古老形態上。之所以有這種傾向,一是因為勞費爾在早期研究活動中將大量熱情傾注于考古,遠東地區人們的古代生活更能吸引他的注意;二是得益于所受的歐洲教育,與美國學者出于現世需要熱衷于研究亞洲當代政治經濟形勢不同,歐洲研究遠東地區的杰出學者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獻身于這一地區的古老歷史與文化。作為美國東方學研究的杰出代表,勞費爾被譽為“在大西洋彼岸,就知識的淵博和對主要資源的掌握而言,唯一堪比沙宛與伯希和的學者”{4}。而他卓絕的語言學研究既是其學術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進行其他研究的必備工具,為他本人和其他美國學者的研究奠定了扎實的語言文獻基礎,因此總結勞費爾的語言學研究特點及其貢獻是有必要的。縱觀勞費爾的學術研究,筆者認為其語言學研究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語言學對勞費爾而言既是工具,也是研究目的和旨趣所在。在他的著作中,有專門研究阿爾泰語系所有格問題的,有探討印度支那語系中a-前綴的,有探索月氏語相關問題,等等。同時,深厚的漢語造詣以及對其他東亞語言的掌握,使得勞費爾在研究中國的名物、風俗、語言、動植物、社會組織、地理、宗教、文學以及藝術等各方面時都能夠得心應手。勞費爾所具有的這種語言學的知識和才能,在同行學者中鮮有能與之匹敵者。
第二,勞費爾的語言學研究是與文獻學研究結合進行的。勞費爾在從語言學、音韻學層面對各種古代語言文字進行研究的同時,廣泛閱讀了數量龐大的相關歷史文獻,并在學術生涯的早期,出于練習和實踐的目的發表過一些翻譯作品。對于這些古代文獻,他并非不加任何批判地拿來,無論是西方語言記錄的材料還是東方語言記錄的材料,他都會以批判和審慎的態度閱讀和使用。勞費爾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追求自然科學研究一般的精確性,他認為后人對前朝的記載一方面因為時間的久遠難免存在訛誤,另一方面加入了記載者的主觀意志,需要謹慎對待。
第三,勞費爾的語言學研究重細節和實證,不重理論建構。他一生在自己研究的各個領域都很少有構建理論輪廓的作品,這也是他作為“微觀漢學”代表人物的原因。以他的吐火羅語的研究為例,他研究的諸如吐火羅語中ri一詞的由來、漢語中“阿魏”名稱的源流以及tuman的意義與溯源,{5}都是具體而微的問題,相應地,他對整個吐火羅語的語言學體系沒有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和概括。
第四,語言學與歷史學相結合。以勞費爾對藏文起源問題的研究為例,除了提出語言學和文獻學的論據外,他還從歷史學的角度進行考察,指出吐蕃與和闐開始交往的時間與藏文形成的時間相悖,從而否定藏文起源“和闐說”,進一步證實了藏文源自印度的觀點。{6}
第五,跨學科的特點。這得益于勞費爾早期在歐洲所受的跨學科性質的學術訓練,即歐洲傳統的“通才式”教育。古代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對象雖然具體而集中,但卻遠非一個學科所能解決,需要研究者有淵博的知識背景和多學科理論與方法的綜合應用。除了結合歷史學和文獻學,勞費爾還從地理、醫學、宗教、文學等多個方面考察研究古代語言文字,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在他的名著《中國伊朗編》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第六,勞費爾古代語言文字研究中的大文明觀研究視角。語言學的研究范圍是具體而抽象的,但勞費爾的眼光卻是寬廣的,他總是從各種語言文字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大文明觀視角,將研究對象置身于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予以觀照,進行綜合的考證和對比研究,以求得盡可能準確的結論。
二、勞費爾語言文字學研究對美國漢學的貢獻
要探討勞費爾的語言文字學研究對美國漢學的貢獻,首先有必要考察一下美國漢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發展狀況。美國早期的漢學研究主要有兩個特征:第一,最早的美國漢學研究以傳教士為主體,比如裨治文、衛三畏等。這些學者本身具有的先決條件是他們在中國居住多年,精通漢語,搜集并閱讀了大量漢文書籍、文獻,甚至可以用漢語著書立說。雖然他們的研究水平高、程度深、范圍廣,但因未曾受到正規的學術訓練,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終究人數太少,難成氣候。第二,不同于歐洲漢學的古典之風,美國漢學注重中國和亞洲的近現代歷史研究,這與美國侵略中國的現世利益是緊密相連的。{7}重視近代史就導致美國學者大多不了解中國和亞洲的古代文明,至于對這些地區古代語言文字的研究,就更無從談起了,以至于大多美國學者無法閱讀中國和中亞地區出土的用古代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記載的文獻,其漢學研究頗受局限。雖然美國人并不想完全仿效歐洲漢學——他們認為應當將漢學與現實的社會研究結合起來,但勞費爾所擁有的資料功夫、語言功夫、考證功夫以及跨學科的寬廣研究視野和科學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滋養了美國漢學{8},其中又以語言學研究的貢獻最大。
第一,勞費爾在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和造詣,為美國學者乃至其他國家的學者都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不僅使得中國的古典文獻和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能夠為眾多學者所見,而且對一些生僻語言的翻譯和研究,如藏文、西夏文、蒙古文等,更是極大開闊了美國學者的視野,使得以這些語言記載的文獻能夠為大家所知曉。美國漢學發展的一個瓶頸就是掌握中文、藏文、蒙文等東方語言的人太少,勞費爾利用他的東方語言專長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奠基工作,如他曾翻譯了《一位藏族王后的小說》{9}《苯教的贖罪詩》{10}《密勒日巴》藏文本{11}等一系列藏文文獻,美國的藏學研究能后來居上,勞費爾的貢獻是不能忽略的。同時也從語言學的角度對這些語言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發表了諸如《藏文中的外來詞》{12}《關于女真族的語言》{13}《關于阿爾泰語言第二格的形成》{14}《西夏文字——印中語言學研究》《“薩滿”一詞的起源》{15}《藏族人語言科學研究——寶篋經》{16}《“哇”“嘖”考——關于藏語的發音》{17}《藏文姓名的漢文轉寫》{18}《印度支那語言中的前綴A-》{19}等一系列論著。
第二,勞費爾在語言文字學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對美國漢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學領域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多樣性決定了單一的學科無法擔此重任,而勞費爾為美國漢學樹立了跨學科研究的典范。”“二戰”結束以后由費正清開創的、以研究中國史和中國現實政治經濟問題為主的所謂“中國學”,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繼承了勞費爾這種跨學科研究的方法。
從某種意義來講,勞費爾的語言文字學研究對美國漢學的貢獻是一種綜合體。對于大多數西方學者而言,由于語言的障礙,封鎖在這些語言中的巨大財富無法挖掘,而勞費爾則打開了這寶藏的封印,從中獲取了大量信息,并將這些信息補綴、縫合,從而向世人昭示出各種文化之間的相互聯系以及相互影響。1930年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的常務秘書長莫提摩爾·格里夫斯(Mortimer Graves)在寫給美國科學院關于“發展美國的中國研究的需求和計劃”的報告中稱,“例如,一部中國碑文集巨著、中國地理辭典、中國考古學術語辭典、西藏甘珠兒和丹珠兒與中國三藏經的批判性比較、漢——藏和中國語言比較研究大全、關于中國與其他東方世界的文化聯系研究、植物栽培和動物馴化史研究以及中國人和他們祖先早期文化的重構研究,這些工作的大部分靈感來自最偉大的美國漢學家勞費爾博士。”{20}這或許可以視為美國學術界對勞費爾的至高褒獎吧!
{1} 陳繼宏:《漢學家伯托爾德·勞費爾》,《新學術》2009年第1期,第114—116頁。
{2} 賀昌群:《悼洛佛爾氏》,原載《圖書季刊》1934年卷2第1期,后收入《賀昌群文集》第3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549—555頁。
{3} 陳繼宏:《勞費爾與中亞古代語言文字研究》之《附錄·勞費爾論著目錄》,蘭州大學2006級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第42—70頁。
{4}{8}{20} 轉引自龔詠梅:《勞費和他的漢學研究對美國中國學的貢獻》,《海外中國學評論》2007年5月第2輯。
{5} Berthold Laufer, ‘Three Tokharian Bagatelles: A Chinese Loan-Word in Tokharian A, A Tokharian Loan-Word in Chinese, Tuman, Toung Pao, 1915, pp. 272-281.
{6} Berthold Laufer, ‘Origin of Tibetan Writ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38, 1918.
{7} 仇華飛:《論美國早期漢學研究》,《史學月刊》2000年第1期。
{9} Berthold Laufer, ‘Der Roman einer tibetischen K?nigin. Tibetischer Text und übersetzung.8 figures and book-ornaments after Tibetan designs drawn by Albert Grünwedel.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11. pp. x, 264.
{10} Berthold Laufer, ‘Ein Sühngedicht der Bonpo.Aus einer Handschrift der oxforder Bodleiana,Denkschrifte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phil.-hist.Classe,Vol.XLVI,pp.1-60.Abhandlung.
{11} Berthold Laufer, ‘Milaraspa, Tibetische Texte in auswahl übertragen. Folkwang-Verlag,Hagen, 1922.
{12} Loan-Word in Tibetan. By Berthold Laufer.[J] Toung Pao, 1916.
{13} Berthold Laufer, ‘Zur Sprache der Jutchen, Cologne Gazette,Nr.325,9.4,Jan.1896.
{14} Berthold Laufer, ‘Zur Entstehung des Genitivs in den altaischen Sprachen, Revue Orientale (Keleti Szemle), Budapest, 1901, Vol. II, no. 2, pp. 133-138.
{15} Berthold Laufer, ‘Origin of the word Sham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17, pp. 361-371
{16} Berthold Laufer, ‘Studien zur Sprachwissenschaft der Tibeter, Sitzungsberichte des philosphilol und der history. Classe der k.bayer.Akad.d.Wissenschaften,München,1898,part.III,pp.519-594.
{17} Berthold Laufer, ‘über das Va-Zur, Ein Beitrag zur Phonetik der tibetischen Sprache, Wiener Zeitschrijt fii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Wien, 1898-1899, Vol. XII, pp. 289-307; Vol. XIII, pp. 95-109, 199-226.
{18} Berthold Laufer, ‘Chinese transcriptions of Tibetan names, T'oung Pao, 1915, pp. 420-424.
{19} Berthold Laufer, ‘The Prefix A- in the Indo-Chinese languages, Journal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 1915, pp. 75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