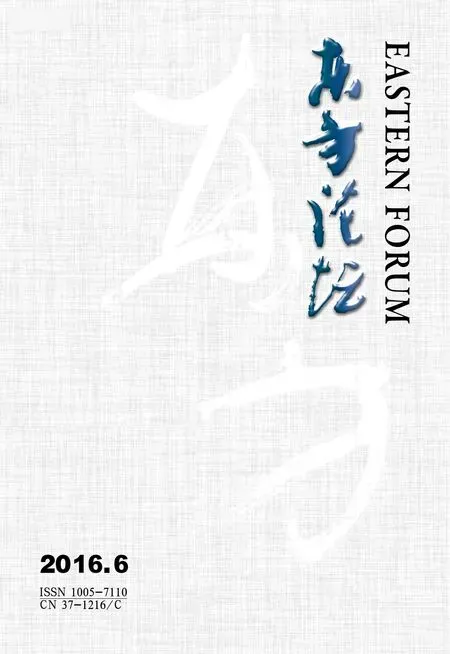略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分期問題
韓 晗
(深圳大學 文化產業研究院,廣東 深圳 518000)
略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分期問題
韓 晗
(深圳大學 文化產業研究院,廣東 深圳 518000)
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分為三個階段(六個時期)。第一個階段也是第一個時期,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至1900年義和團運動,此為萌芽期;第二個階段為第二個時期和第三個時期,從1901年至1917年新文化運動,此為發育期,期間中國現代文化產業諸多門類逐漸完善;第三個階段為第四個時期至第六個時期,從1917年至1949年,此為成熟期,在這一階段中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發展完備。
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晚清;歷史分期
學界公認,文化產業是一個與資本主義有關的概念,封建社會、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并無文化產業,前者只能說存在著具備文化產業特征的文化形態,但不具備產業化的生產、消費方式與社會化的規模;而后者只有文化事業,而無文化產業(譬如前蘇聯與今天的朝鮮)。西方學界對于文化產業、文化工業相關問題的反思與研究,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對于資本主義問題研究升華之后的結果,屬于資本主義文化、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①“文化工業”由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與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人所提出,用以批判現代西方文化的工業化生產,認為文化成為了迎合消費者的商品,喪失了其人文主義的啟蒙意義,后世一般以“文化工業”指稱工業化生產的文化體系。因此,文化產業是資本主義時代所蘊育出的文化形態。
中國現代文化產業起源于晚清,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幾乎同時。從鴉片戰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百多年里,中國的文化產業從無到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是中國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為繼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推動、繁榮中國現代文化起到了積極的歷史作用。因此,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與學術意義。
我們必須要厘清一個史實,有學者認為,晚清至1949年之前,中國并非是資本主義時期,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1](P2)從表面上看,兩者之間明顯是有沖突的。但本文所言之“資本主義”是指的經濟特征,而“半殖民半封建”則是政治特征,兩者屬于不同概念范疇。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特征萌芽于晚明的蘇州,真正出現于晚清的口岸、租界地區。化產業本身是附著在資本主義經濟上的一種文化方式與產業形態,故而中國文化產業亦最早出現在晚清的口岸、租界地區,這是歷史、經濟雙重原因所決定的。
近年來,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研究開始為海內外學界所共同重視,學界同行也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受制于全球史觀及其研究方式的影響,就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分期這一問題一直缺乏應有的關注,而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特殊性決定了其歷史分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今后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研究方向。藉此,筆者愿不揣淺陋,就自己對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分期問題的粗陋孔見,拋磚引玉,請學界諸方家不吝賜教。
一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大致分為如下三個階段(六個時期),第一個階段稱之為“萌芽期”,即第一個時期,時間跨度為是從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第二個階段則稱之為“發育期”,即第二個時期與第三個時期,時間跨度為1900年義和團運動至1917年的新文化運動;第三個階段則稱之為“成熟期”,即第四個時期、第五個時期與第六個時期,時間跨度為新文化運動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萌芽期”即第一個時期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預備期,我們知道,這一歷史時期是十九世紀最后六十年,也是清王朝從閉關鎖國走向內外交困的一個時期。其間經歷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所謂的“同治中興”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又稱第一次中日戰爭)與八國聯軍戰爭。因此,我們既要看到當時中國處于風雨飄搖、山河破碎的生死關頭,也應該看到它也處于“被迫”的現代化進程當中。一方面,清王朝不得不應全球化的大勢,通過一系列強加在頭上的不平等條約,開放口岸、設立租界,一方面,清王朝亦要“師夷長技以自強”,通過“洋務運動”等一系列現代化手段來提升自己的綜合國力,進而在與西方列強談判時,可以多一點討價還價的籌碼,而民族工業、外來資本工業與官辦工業也由是應運而生。在這樣特殊的歷史語境下,中國有了自己的早期現代工業與資本主義市場。
與之相伴隨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出現。在晚清之前,中國也有一些可以稱之為“文化產業”的文化現象,譬如唐代的歌舞教坊、宋代的勾欄瓦肆與明清的江南出版業等等。但是要衡量一種文化現象是否屬于文化產業,首要標準就是要看是否屬于“產業”。什么是產業?產業的英語是“industry”,這個詞也可以翻譯為“工業”,即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生產。首先“文化產業”必須是規模性的,其次它存在于都市文化、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消費、分配等流通諸環節的基礎之上,否則就根本不能算是文化產業。
因此第一個時期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萌芽期。談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則不得不談中國現代文化,它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主體。十九世紀下半葉,時值諸口岸通商開埠、租界林立,一批以傳教士、工程師、士兵、外交官、記者、探險家、商人與學者為主體的外國僑民大量涌入中國,在中國許多地方形成“華洋雜居”之狀況。僑民來華,自然也將新的外國文化形態及其表現方式帶入中國。
這當中既有他們生活必不可少的《圣經》及各類與基督教有關的文化生活,也有他們平日里所喜歡的歌劇、賽馬,以及在歐美早已習以為常的報刊、雜志。他們既需要在文化上自我滿足,也希望可以用他們的文化來影響周圍的中國人,這是當時大多數殖民者的普遍想法——不管是歐西諸國在中國租界,還是法國人在交趾支那(即今日越南、老撾與柬埔寨等地)、英國人在英屬印度皆如此,而且當時中國人本身對于源自歐西的舶來文化也懷有一種“異邦想象”的喜愛。這一切使得中國現代文化的主體、客體既有外國僑民,也有受西方教育、影響并“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2](P16)
在這重語境下,中國現代文化產業應運而生。早在1815年,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在香港中國辦了最早的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33年,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Gutzlaff)在廣州創辦另一份報紙《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60年,上海出現一個由旅滬英美僑民創辦的 A.D.C劇團(又稱大英劇社、愛美劇社,Amateur Drama club of Shanghai);1874年,改良派先驅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并自任主筆,宣傳變法維新;1894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支持建筑師裴令漢(William Bellingham)創辦《京津泰晤士報》(亦稱《天津時報》);1897年,嚴復等人創辦的《國聞報》在北京創刊。
從形態上看,在第一個時期,中國現代文化產業主要以兩種形態存在,一是報紙,二是戲劇。但有兩點不得不提,上述只是“新文化”產業,而傳統文化產業,也在新的生產關系下綻放出了新的光彩,那就是全國各大城市(特別是上海、廣州地區)日漸成熟的戲曲市場與書畫市場。
書畫、戲曲原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兩大文化市場亦非新鮮物種,白居易的《琵琶行》便是講的歌女上船賣藝,《清明上河圖》里的勾欄瓦肆則將其市場化,而書畫“潤格”早在晉代就有,王羲之為一位道士抄了《道德經》,道士將自己養的一群鵝“舉群相贈”,這便是書畫交易之雛形。及至唐代,詩人王勃字、詩皆冠蓋文壇,求字者甚多,王勃未及而立,便“金帛盈及”。而另一位書法家皇甫湜曾向求字的宰相裴度開出“一個字三匹絹”的“高潤格”,這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的書法交易最高紀錄。宋明以降,戲曲、書畫的早期市場都是存在的。
但必須說明的是,這依舊不能算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仍是一種自由、不規范的封建市場。形成市場固然是產業的前提,但是這個市場必須是健全、規范并明確法權關系的,正如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所說,“羅馬法是簡單商品生產即資本主義前的商品生產的完善的法律,但它也包含著資本主義時期的大多數法權關系。”[3](P20)唐宋以來的戲曲、書畫市場明顯不具備這個基本因素。因此,中國戲曲、書畫現代市場則發軔于晚清,這是“西學東漸”的結果,在這樣的市場下,才可能孕育出中國現代文化產業。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書畫市場、戲曲市場隨著“西學東漸”的浪潮而逐漸現代化,其交易亦開始逐步走向規范,這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之雛形。譬如同治六年(1867年)在廣州成立的戲曲市場中介組織“吉慶公所”與上海出現的“京班戲園”、1878年在上海出現的書畫中介交易機構“箋扇莊”等等,這與十八世紀在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出現的藝術品中介機構、拍賣行與劇院經紀人(Theatre broker)有著功能上的相似之處,不難看出,這顯然是“西學東漸”的影響下應運而生的產物。
一言以蔽之,第一個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處于萌芽期,只有零星的一些文化產業現象出現,尚不夠成氣候。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無論是報紙、戲曲還是書畫市場,它都已經展現出了現代文化產業的特征,這是和傳統的文化市場很不一樣的文化產業形態,這一時期理應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起始性的萌芽期。
二
第二個階段則是“發育期”,即二十世紀前十七年(1901-1917)。這一時期之于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意義非常。首先是電影、話劇等新興藝術形態的出現,這是形式上的創新,帶動了中國現代文化產業體制的發育;其次是時代的變遷,在這短短十七年里面,帝制宣告終結,新文化運動興起,封建專制法統與道統相繼走向崩潰。這對于中國現代文化產業而言,無疑是促進其發育的重要土壤。在發育期中,第二個時期與第三個時期可謂先承后續,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發展意義上有著共通之處。
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第二個時期是從義和團運動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這是清王朝的最后11年。此階段雖然時間不長,但卻意義非凡。在這一時期里,三個重要的現代文化形態依次在中國出現,一是1904年出現的唱片,二是1905年出現的電影,三是1907年出現的現代話劇(萌芽時稱文明新戲)。這三個新生事物,構成了日后中國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當然也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談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有兩個因素不能忽略,一個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個前面已經提到,這里不再贅述。還有一個就是西方現代科技,它對于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形成至關重要,但時常被人忽視。前面我們講到的報紙,它和之前中國的“活字印刷”就很不一樣,因為它是現代機器印刷出來的,不是人手工雕版、排版的。現代機器的能源不是人力,而是電力,這是西方工業革命的產物。人力雕版印刷的印刷品,數量有限,難以成為“產業”,但電力就不同了,這大大解放了生產力,可以在短期內印刷大量的報紙、書籍,為傳播新聞、昌明新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術保障。報紙如是,唱片、電影與話劇則更不用說,這是西方現代科技所帶來的福利。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依賴于錄音技術的唱片播放載體留聲機一經發明便由西方僑民帶入中國廣州、上海等地,因為其功能奇特,當時頗受中國達官顯貴們的青睞。但當時只是以銷售留聲機為主,未有唱片制作。及至1904年,京劇表演藝術家孫菊仙試制了《鐵蓮花》《捉放曹》等唱片,1908年,東方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是為中國唱片業之起始。畢竟唱片的生產、灌制以及留聲機的生產、維護必須要依賴于現代技術,中國唱片。業在這一時期獲得了發展,同時中國的唱片技術也有了從無到有的進步。
與唱片一樣,電影在中國的出現也與傳統戲曲關系緊密。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在琉璃廠土地祠為京劇大師譚鑫培拍攝了京劇《定軍山》片段,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黑白無聲電影。在此之后,中國電影業獲得了迅速發展,成為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而電影業的發展,又與攝影、錄音技術密不可分。
和電影、唱片不同,中國最早的話劇是留日學生“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演出的《茶花女》與《黑奴吁天錄》,但要說最早的現代戲劇,則應屬1899年上海圣約翰書院的中國學生編演的新戲《官場丑史》。但后者演出之后,并未形成應有的反響,既未加演,也未推而廣之。前者在演出之后,主創團隊田漢、歐陽予倩等人卻認為此應是中國戲劇一大創新。于是,回國之后,他們繼續進行文明新戲的創作、演出活動,成為了中國話劇的奠基人。
話劇與傳統戲曲不同,它因為是寫實而非寫意的藝術,因此更多受西方歌劇影響,需要借助舞臺燈光、音響技術與升降設備等等。所以,話劇、電影與唱片都是與新技術息息相關的新興文化技術。此外,印刷技術的繁盛也帶動了畫報業的興旺,如北京的《啟蒙畫報》(1902)與《開通畫報》(1906)、廣州的《時事畫報》(1905)、上海的《東方雜志》(1904)、《世界日報》(1908)和《圖畫日報》(1909)等等都在這一階段相繼創刊。新技術對文化的影響,在20世紀前11年里體現得淋漓盡致。[4]
必須值得說明的一點還在于,就在這一階段,一千多年的科舉取士被取消。讀書人的“中舉”之夢被迫斷碎。他們不得不改弦更張,為求生存從江浙一帶“轉戰滬上”,成為了“自輕自賤”的“補白文人”,靠賣文而求生。當中以周桂笙、李伯元、包天笑為代表的近代小說家由是崛起,成為了晚清通俗文學、大眾文藝與都市文化的重要主體,是當時報刊、畫報、話劇、電影等新興文化產業最重要的生力軍。
因此,我們勢必要站在更高的歷史高度來反思這一問題。這11年是清王朝最后的11年,一方面,戊戌變法已經宣告失敗;另一方面,光緒帝下詔廢除科舉考試,宣統年間宣布“預備立憲”。但在朝野上下,大家對于清王朝的改革態度以及是否能夠成功并不抱太大期望。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同年革命黨人吳樾刺殺五大臣事敗;1907年,女權運動先驅秋瑾被清廷殺害于紹興;1910年,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失敗。與此同時,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在1907-1909年兩年間發動了8次起義,雖均以失敗而告終,但卻在國內掀起一陣狂飆突進的推翻帝制的革命浪潮。1911年,“保路運動”爆發,藉此武昌城一聲槍響,兩千年的帝制在中國終結了。
國運如此,文運豈能僭越?中國古代早有“文以載道”之風。在經歷了“西學東漸”半個多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化形態借助新技術、新觀念橫空出世,它顯然就不可能是遺世而獨立之物,在特殊年代,文化當然要有所作為。因此,話劇、電影與唱片的出現,顯然與大革命之前這暴風驟雨將至的歷史大時局密不可分。事實上也證明了,在此階段出現的新興文化形式,盡管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成為了革命家改造社會、喚醒民眾的工具。從這個角度來講,第二階段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特征重在一個“新”字——新形態、新技術、新觀念與新的時代需求——即對于革命的追求。
第三個時期則是從辛亥革命至新文化運動爆發的1917年,雖然只是6年時間,但這短短6年卻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上相當重要的6年。一是中國電影業的登場。1913年,美國人經營的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了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中國第一部有故事情節的短片《難夫難妻》,這標志著中國電影產業的出現;二是出版業的興盛。與辛亥革命爆發的同年,中華書局成立,國內出版界形成“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爭雄”的局面,意味著中國的出版市場開始進入競爭時代;三是藝術品市場的發展。大量清廷遺老、寓公顯貴的出現,使京滬兩地書畫、文物交易相當火爆,大大超過了以往。[5]
歸根結底, 這是由于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封建時代,也瓦解了傳統倫理所致。長期以來,受孔孟禮教影響的中國人奉行“重農抑商”的觀念,而辛亥革命之后,資本主義觀念進入中國,不但科舉早已廢除,且官方自上而下推行“實業救國”之政策,使得商業行為不再被全社會所輕視。傳統的文人墨客唯有賣字鬻文以求生存。晚清遺老、書法家李桂清如是哀嘆自己迫不得已做“職業書法家”的境遇:
(我)不得已,仍鬻書作業,然不能追時好以取世資,又不欲賤賈以趨利,世有真愛瑞清書者,將不愛其金,清如其值以償。[6](P53)
在舊王朝已倒,新文化未立的6年間,中國現代文化處于黎明前的探索期,但現代文化產業卻蓬勃發展,為日后現代文化傳播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這得益于文化產業的主體——新式知識分子的出現,他們可能是落第書生,也可能是留洋學生,還可能是被西化的晚清遺老、洋行買辦,也可能是新政府里的職員等等。他們既是現代文化產業的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他們共同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支持者與推動者。
在這6年間,租界未廢,民國已立,借著“實業救國”的浪潮,中國的都市文化迅速崛起,這為現代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正逢其時的溫床。在1910年代的上海,500多所新式中小學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與此同時,陸續建立了由華僑投資的四大百貨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與大新公司。而且就在1910年代,傳統的茶樓、戲園開始讓位于擁有鏡框式舞臺、新式燈光技術、編號座位與展演新劇目、新影片的現代戲院、電影院。“游樂場”這個新生事物也隨之出現,并在1910年代在滬上大行其道——如經潤三在1912年創辦的“樓外樓”、1915年創辦的“新世界”與1917年落成的“大世界”等等,皆為當時新興文化產業形式之代表。[7](P78)此外,工藝美術大師鄭曼陀在1914年成立自己的工作室,首創“擦筆水彩畫法”為商家繪制月份牌;另一位美術家周柏生在1917年開始為“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設計廣告牌、月份牌,此為中國現代廣告業之濫觴。[8]
上述種種皆深刻地反映了新文化未興,現代文化產業先行,這一切皆拜都市文明所賜。6年時間雖短,但現代文化產業卻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歷史地看,這6年的時間為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定下了一個基調:以都市文化為基礎。這與歐洲、美國現代文化產業的興起是一致的,只有市民社會的勃興,才能為文化產業帶來廣闊的市場,無論中西,皆不例外。
三
第三個階段則為“成熟期”。所謂“成熟期”,就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體制逐漸完備的時期(1918-1949)。在此期間,中國現代文化產業諸多門類體系發育齊全,并且開始有了文化產業類的法律法規,部分門類的市場化程度亦較為深厚,并且參與到了二十世紀文化全球化的大勢當中。縱觀“成熟期”的三十二年,是現代中國戰亂頻仍的亂世,但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迅速發展的時代。此階段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先后經歷了第四、第五、第六這三個時期。可以這樣說,雖然歷經戰火淬煉,但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卻一直在艱辛中努力開拓,在挫折中揚帆起航,在每個不同的階段均取得了值得驕傲的成就,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化史、經濟史、城市史乃至社會史的重要內涵。
第四個時期則是從新文化運動至全面抗日戰爭爆發(1937年),在這20年里,中國的現代文化產業獲得了巨大發展,形成蔚為壯觀的“摩登文化”。在這一時期,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初步形成了自身的格局:以圖書、報刊出版業為主體,以民營電臺、電影業為兩翼,唱片娛樂業、戲劇戲曲業、工藝美術業與藝術品市場齊頭并進的壯觀局面。
現在不少學者認為,這一時期乃是中國現代文化的“黃金時期”,因為我們所熟知的現代文學作家、電影導演乃至建筑師的經典作品,都是這一時期完成的。但實際上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亂世。在短短20年時間里,全國各地先后爆發了北伐戰爭、中原大戰、兩廣戰爭、兩次蔣桂戰爭、第一次國共內戰、“一二·八”事變、濟南慘案與“九·一八”事變,戰火從東三省燒到兩廣,從上海蔓延到川藏,幾乎覆蓋了整個中國,當中還不算家常便飯的匪患、天災、瘟疫等等。如果說這段時間里還有不錯的文化成果誕生,這只能說明中國的文藝家、文化人確實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在逆境中不但求生存,而且還得到了發展,這自是“國家不幸詩家幸”的最好寫照。
因此,我們要理解這一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既要對當時的文化史有所了解,也要把握大的歷史背景。正如前文所述,這一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局面的確“壯觀”,乃是因為文化產業各體系均有較大發展,這在之前是沒有過的。譬如1935年成為了中國出版史上的“雜志年”,雜志發行量與品種堪稱翹楚;1922年,張石川的明星電影公司成立,1925年,邵醉翁(邵氏兄弟之兄長)的天一影片公司成立,1928年,大光明電影院開業,1932年,盧石的聯合電影公司成立,1934年,張善琨的聯華電影公司成立——幾乎與此同時,好萊塢八大公司在上海、北京分別設有分號,并大規模占領中國市場;在出版界,1920-30年代形成了世界書局、開明書店、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四足鼎立”之勢,而以《玲瓏》《萬象》為代表的滬上文化、時尚類雜志則爭奇斗艷,現代文化產業一派繁榮之景象。
如此亂世,這般文章,初看確實匪夷所思,但細想卻非毫無理由。一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此20年內,除了日寇入侵的戰爭之外,其余戰爭軍閥、黨派奪取地盤的內戰為主,多半集中在鄉村而非城市,因此鄉村雖生靈涂炭,但城市仍歌舞升平,文化產業的發展未受到太多影響;二是從經濟的角度看,內戰特別是軍閥混戰不但催生出以江浙財閥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群體,而且可以提高重工業、紡織工業、面粉與制藥行業的效益,使得產業工人的收入也有較大幅度提升,這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規律所決定的。美國總統杰弗遜(Jeffson)曾有“一場戰爭制造一批富人”的論斷,中國也有“發國難財”一說。史實證明,在這20年里,中國的民族工業確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1920年,國內民族工業資本產值不過2.51億元,到了1936年,竟然達到了16.32億元,每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2.41%,這個增長率是相當驚人的。
工人階級隊伍的日益壯大,實際上為現代文化產業提供了重要的主體與客體。筆者曾就印刷工人與左翼文藝運動的互動關系為例,解析了產業工人之于現代文藝的重要意義。①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詳見拙文《論現代印刷業與1930年代的左翼文藝》(載于《北京印刷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實際上,產業工人的構成是復雜的,除了體力的底層工人之外,也包括技術工人、工程師、設計師與工廠管理者等“準中產階層”。他們在上海、南京、北京、漢口、重慶與廣州等口岸城市廣泛存在,可謂是一個巨大的消費群體。他們生活在城市中,有一定的現代科學知識與市民觀念,這是現代文化產業得以迅速發展的重要基礎。
但是,隨之而來的抗日戰爭則徹底將中國現代文化產業拉至谷底。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發展的第五個時期——抗戰八年(1937-1945)期間,中國一大半國土淪至敵手。軍閥混戰意在問鼎中原,因此多是搶奪鄉村地盤,但日寇入侵卻是為其本國工業殖民化需要,因而專挑城市下手。武漢、南京、上海、北京、廣州、福州等大都市在鐵蹄下紛紛淪陷,即使剩下的重慶、桂林、成都與昆明等被稱之為“大后方”的城市,曾經以消費文化為主的文化產業也幾乎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宣傳抗日救國的“文化事業”。縱然在上海“孤島”時期有一些古裝戲、傳統戲曲的演出,也是借古諷今、宣揚抗戰之作。而汪偽文人們所鼓吹的“和平主義文藝”則幾乎毫無市場,受到了淪陷區群眾的大力抵制。幾年前興旺的雜志出版業,在抗戰時期卻無比慘淡:
最近我們常聽人談起,上海的出版界幾乎可說是停頓。文藝單行本不出,學術研究專著更是絕無。掌握這出版界門面的還是只有若干種雜志……近年學術研究空氣完全等于零的時期。[9]
但在這一時期,仍有兩個重要的文化產業的人物不得不提,一是以張愛玲為代表的都市作家,這是抗戰時期中國出版業難得出現的亮點;二是以費穆為代表的電影人,他們在抗戰時期為中國電影業所做出的歷史性嘗試,對于中國電影業產生了深遠且復雜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重心當然是上海。作為一個特殊的城市,上海文化人在抗戰時期的活動以及他們的政治傾向一直是學術界所關注的問題。上海最大的特點在于“華洋分治”,它的租界區曾在戰時長期未被日軍占領,直至1941年12月上海徹底淪陷,1943年汪偽南京政府宣布“接管”租界地區。因此,上海的租界地區在1937-1941年間曾涌入大量資本家、外商與各種難民,當中不乏有產者。藉此,上海租界地區在抗戰時曾一度呈現出了“畸形的繁榮”,百貨商場、酒店、舞廳、跑馬場生意好過戰前,“今朝有酒今朝醉”“時尚摩登”的娛樂消費主義成為了當時滬上文化產業的主旋律,“張愛玲現象”“費穆現象”便是在這樣的語境下出現的。
但從大局上看,抗戰時期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總體上仍是凋敝、蕭條的狀態。上海局部的泡沫式繁榮并不具備普遍性。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其核心是中國現代文化,其核心是晚清以來的批判現實主義與“五四”啟蒙思想。但抗戰時上海的“摩登文化”,雖然形成了“看上去很美”的高產值,但除了少數呼吁抗戰的古裝戲、古裝電影之外,真正有意義、可留諸后世的作品并不多。
因此,抗戰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可以用“一家泡沫,百家凋零”來形容。上海租界地區文化產業的泡沫化,至今仍是學界、文學創作界熱衷關注的一個話題。但作為對中國近代文化產業史的研究,既應關注上海地區抗戰時這種不正常、泡沫式的“興”,更應放眼全國,去研究北京、漢口、廣州等地因戰爭而導致的文化產業之“衰”,只有這樣,才能對當時中國的文化產業有一個準確、客觀的把握與了解。
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第六個時期,就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1946-1949)。在這一時期,中國現代文化可謂是枯木逢春,從日寇嚴酷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中走出,開始尋求“五四”精神中人道主義的價值,而文化產業亦是如此。電影業告別了光怪陸離、搔首弄姿的“都市摩登”,一批現實主義、反映人性之溫暖的“文人電影”開始出現,如黃佐臨的《假風虛凰》(1947)和《夜店》(1948)、桑弧的《太太萬歲》(1947)和《哀樂中年》(1948)以及費穆的《小城之春》(1948)等等,皆為當時代表之作。與此同時,中國的出版業亦走向了復蘇,上海地區在該期間創辦文學刊物198種,年均54種,與“孤島”時期(年均60種)、“雜志年”前后(1928-1936,年均59種)差異并不大。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地緣格局處于“分裂”狀態,一是國統區的文化產業,一是解放區的文化產業。前者不言自明,而后者是否屬于“文化產業”,一直是學界爭論的話題。因為中國共產黨一向注重文化宣傳,并認為其是政治、革命的重要工具。從這個角度來看,解放區的文化活動雖然繁盛,但一無民營資本進入,二不以盈利為首要目的,嚴格地說不能算作是文化產業,而被大陸主流史家稱之為“新民主主義文化宣傳事業”。但事實上,解放區出版、電影、戲劇活動并不遜色于國統區,其雜志、書籍的出版當然也有盈利。延安、東北與華北等解放區書店、出版社何止百千,而且還成立了“新華書店”托拉斯發行機構。其出版業是顯而易見的高額利潤,只是解放區的整個文化產業的投資方、獲利方都是中國共產黨而已。這種近似于“官辦文化產業”的文化行為,應屬于廣義上的文化產業,因此它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應探討、研究的對象,而且應與國統區的文化產業進行對比研究。
綜上所述,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前后一共三個階段,六個時期,歷時109年,橫跨晚清、民國時期。這三個階段,六個時期中的各自不同的歷史事件、社會思潮共同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發展的跌宕起伏與波瀾壯闊。平心而論,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與中國現代文化史一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意義非凡,對于后世影響尤其影響深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承接中西之學、昌明科學民主的歷史意義,因而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
[1]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
[2] 熊月之.上海的外國人:1842-194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 復旦大學法律系國家與法的理論、歷史教研組.馬克思、恩格斯論國家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
[4] 韓晗.摩登圖像:論傳媒技術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進程[J].現代傳播,2014,(8).
[5] 韓晗.想象的空間: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基于科學思潮的視角[J].東方論壇,2014,(6).
[6] 陳振濂.中國現代書法史[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
[7] 張真.銀幕艷史:都市文化與上海電影(1896-1937)[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
[8] 韓晗.日常生活、都市文明與現代科學的傳播——以1900年代的中國現代大眾文化為中心[J].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J].2015,(6).
[9] 漱六.七年來的上海雜志事業(上)[J].文友, 1944,3(2).
責任編輯:馮濟平
Analysis of the Period Divis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SUNNY H. HAN
( Institut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00, China )
This research divides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into three periods ( including 6 stages ) in ligh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fi rst period, also the fi rst stage, is the late 60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named the embryo period. The second period, which includes the second stage and the third stage, is the fi rst 17 year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named the puberty perio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ategories of the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were perfected gradually. The fourth stage to the sixth stage is from 1917 to 1949, also is the third period named the mature period, when the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ed fully.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late Qing Dynasty; period division
G129
A
1005-7110(2016)06-0064-07
2016-09-16
韓晗(1985-),男,北京人,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后,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研究員。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早期抗日文藝期刊研究(1931-1938)”(15FZW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