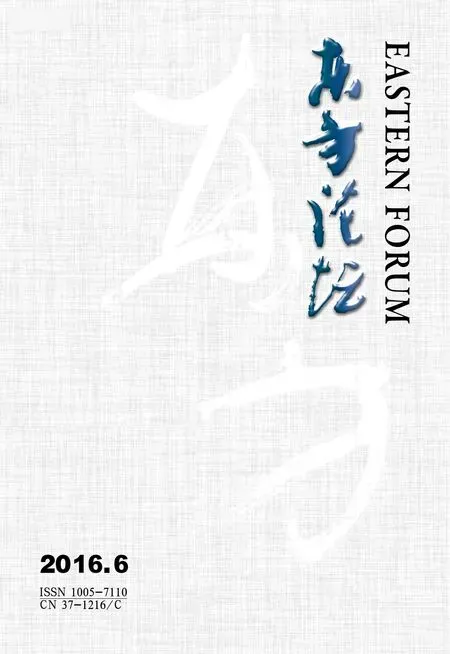為何傳統?何為傳統?
——當前語境下重審傳統文化的必要性及其概念辨析
閆 曉 昀
(青島大學 文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為何傳統?何為傳統?
——當前語境下重審傳統文化的必要性及其概念辨析
閆 曉 昀
(青島大學 文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在當前全球化文化語境下,重新理解民族傳統文化的契機已經成熟。無論從現代文化主體的深層心理結構、“五四”以來“盲目西化”的不盡人意還是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來看,重審傳統文化都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義。然而,回溯傳統并不意味抱守殘缺,而是在現代視野中重新理解“傳統”的內涵,使優化和升華后的“現代民族傳統文化”能為現代民族文學建設和文化復興提供保障與指導。
民族;文化認同;傳統文化;傳統;現代
自二十世紀初期西方文化與價值觀念隨軍事入侵滲透至中國起,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自足狀態也隨之終結,基于傳統農業文明構建的中國文化以此為原點,走上了延續一個多世紀的西化之路。概括而言,西方文化主導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三個主要時段,即反帝反封建時期(包含“五四”和與之相應的民主革命時期)、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及當前的全球化時期。每一次思想風暴,均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我們也無法否認西方價值理念對于中國文明進程的推動。然而,如同“四夷”的存在曾經激起家國民族對于邊界和本土思想文化的保護意識一般,當前的“全球化”語境對于民族文化個性的消磨同樣激發了類似的焦慮,必須承認的是,西方價值觀的強勢滲透已經使民族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文化失根的可能性促使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迫切地需要實現民族文化身份認同,從而保持中國文化的個性特征與個體價值,“文化身份”確認因此成為溝通文化與文學并實現上述訴求的迫切需求,對文學領域而言,這也是實現本國優秀文學作品在世界文學舞臺上得以芬芳綻放的基礎保障。“文化身份”最初是一個來自于西方文學批評的概念,從整體文化生態來看,文化身份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迫切話題,即使一直在強力輸出價值觀的西方國家,也同樣為其模糊勢態而焦慮。中國的文化與文學也要防止民族傳統及其文化精粹淹沒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事實上這個問題也已經逐漸走入關注視野。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中青年作家即曾表達過重審民族文化傳統的愿望并積極實踐,指出文化決定人類和文學,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而當下,無論在官方意識形態宣傳對民族文化質素的強調中,還是在學界對于傳統的重新解讀里,都暗含著以優質傳統文化“復興中華文明”的潛臺詞,以期尋找中華文明得以生存、延續與發揚的文化優根,發掘其所內含的積極力量和優秀組成,并以之為依托促進民族文化與精神品格的再生。我們顯然已經意識到,由民族文化認同所表征的“個性”與“優根性”,已經代替先前對于“共性”的盲求和對于“劣根性”的批判,成為本民族文學在世界文學舞臺上爭得一席之地并獲得掌聲的根本方法,在當前家國民族同心追逐“中國夢”的宏大訴求中,重新估定民族文化的價值與地位,亦是“夢圓”的必經之途,畢竟,中國之“夢”萌發并生長于“中國”這一核心理念之中。
可見,無論從外部語境還是內部訴求來看,重審民族傳統文化均勢在必行。除去當前“文化形勢”這一“導火線”之外,此一“勢在必行”還有其獨特的原因與價值,本文即以此為據,力求詳盡闡釋當前文化語境下重審傳統文化的必要性及方法,并試圖探求理解“傳統”的方法。
一
從現代文化主體的深層心理結構來看,重審傳統文化有其“根深蒂固”的必要性與必然性。現代進程中的文化實踐似乎已經證實,越是在文化身份模糊的融合時代,對文化之根的尋求越為自發與迫切。本文開篇處曾提到現代化過程中的三次西方文化浪潮,每一次中西文化激烈對撞的時刻,中國知識分子均在文化焦慮下產生了“尋根”熱望——“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一次浪潮)雖以對傳統的抗拒打開了現代思維,然而仍有一脈堅持向民族傳統致敬,并試圖從中尋找重建民族品格的方法。雖然如何更有效地實現中華文明進化,是激烈的思想革命還是溫和的自我升華仍是未解的題目,但此一脈對于民族文化身份的恪守,在當前無疑具有不遜于現代思想革命的價值。這種對于民族文化傳統的反思式回歸從未停止,及至政治解凍后的“尋根文學”時期(第二次浪潮),對文化之根的尋求已成為作家更為自覺的行為,其影響也遠不限于對政治文學的反抗,而在當前全球化語境下(第三次浪潮),對傳統的回歸已經不單純是文學領域的一個側面,更是上升為社會整體的顯性訴求,以確保民族文化以獨立自主的身份與形象繁榮于世界舞臺。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每當思想與文化走向更為開放的新境遇,我們總會回轉身形,向傳統中尋找支持,且思想環境越自由越開放,對傳統的回望越頻繁,異質文化越強勢,對傳統的眷戀越熱切。這至少可以說明兩方面問題:其一,依戀傳統是人類的精神本能,即使最為嚴苛的思想控制,也難以真正消解傳統之戀;其二,對“國別文化”而言,一種可稱作“民族文化主義”的觀念深存在國民文化心理的深層,正是它保證了傳統不死。因此,在現代文化主體觀念中,傳統文化常常以一個復雜的雙重形象存在:在意識的表層,它是罪魁禍首、食人惡魔與人性劊子手,必須以徹底的“反傳統主義”來祛除,然而在意識的深層,它卻是值得依戀甚至令人同情的。所以,雖在現代之初,身負危機意識的現代知識者們曾試圖以“全盤西化”的理想來解決中國社會的痼疾,然而,因這一文化上的偏激態度從本質來看未能遵循文化主體的深層心理,而在具體實踐中頻遇曲折反復,主體們也從未真正終止對傳統的回望。假如跳出時空限制,站在當下角度來看,也許這才是現代主體真正的內在訴求。在傳統文化結構急遽解體的二十世紀初期,盡管這一訴求被遮蔽,但也并未在異質文化壓倒性優勢的威脅下消失。曾提出“全盤西化”主張的胡適,甚至在晚年成為一個文化的“民族主義者”,主張重審我們民族“古老的文化”,這些也許可視作對該論點最為直接的例子。傳統文化作為集體無意識存在于國民思想和其文化產品中,幾千年來已深入民族精神血脈深處,成為創作主體的精神內殿,自覺地引導著主體在遭遇文化侵襲的時刻捍衛著它的尊嚴與地位。如果我們在傳統中收獲了文化優越性與歸屬感,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指責重審傳統是“保守”甚至“倒退”的,更何況傳統的根脈如此之龐大深厚,跨過如此久遠堅固的民族文化傳統接納異質文化,無異于構建空中樓閣。揚棄地繼承傳統文化,發揚其優秀之處,應當是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可缺席的環節,在當前政治、經濟、文化合作更為自由開放的背景下,其意義更是不容忽視,倘若無視其意義,也無疑等同于從根源上否定了民族文化的存在價值,荒蕪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使現代主體陷于文化上的流離失所之苦痛。
二
“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后,文化先鋒們運用西方文化價值觀以及與之相適配的理性和懷疑精神去“重新估定一切價值”[1](P126),正是這種價值重估導致了思想的革命。新興的現代知識分子嘗試重建中國社會的文化體系,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念在這場“除舊布新”的文化運動中遭遇全線潰敗,從中心退向邊緣。不可否認傳統文化的確存有阻礙文明進步的糟粕,然而,對傳統文化的反抗自發生伊始即陷于過度激烈的極端境界。帶著“全盤西化”的理想,批判者們對傳統文化大多采取一概否定的方式,以致糟粕與精華一并舍棄,甚至走向了非理性的極端,從意識形態高度打擊傳統文化價值觀,有意回避平實公允的討論。傳統文化的“劣根性”被無限放大,而其優質因素則被縮微成無關緊要的潛流。然而,“盲目西化”并未帶來預想的結果,這也為今天重審傳統文化的工作提供了反思的起點與外部機緣。過度批判消解了對話的可能,導致了“新文化”必定優于“舊文化”,且必將戰勝“舊文化”的簡單邏輯,在西方文化的強勢滲透下,傳統文化可謂完敗,似乎其思想產物僅為“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封建禮教以及“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1](P268)。這一言論是否公允暫且不論,在此值得強調的是,即使這些看似必須“連根拔起”的中國所“獨有的寶貝”,實際上并未被“全盤西化”的理想肅清,魯迅筆下麻木的民眾仍在當代改名換姓地存活,迷信與愚昧仍在當下的鄉土中國中保持著殘存的生命力,而國民性批判的話題在文學書寫中從未中斷。西方文化的救贖,顯然并未取得預想的成功。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在帶來先進思想與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無法忽視的負面干預。“現代”使鄉土中國產生了“前”“后”之分,盡管不能否認其對于社會文明進步的促進作用,但傳統文化中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精華是否已在“現代”的過程中蒙塵?自然、社會與人是否已在“工具理性”的裹挾下異化?這些“后現代”的鄉土中國正在經歷的種種問題似乎提醒著我們,西方理念奠基下的現代文明同“我鄉我土”至少存在不兼容成分。中國并未經歷西方歷史演進的過程,在文化源頭上差異甚大,假若我們僅僅為一些理念所吸引而不能真正理解其內涵,便會自然而然地陷于“意義創造”的藩籬,將想象的意義投射到口號之上,依據偏頗的理解來解釋名詞并以此為據解決問題,這種解釋常常與這些名詞所代表的思想沒有多大關系,而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也幾乎無可避免地會產生形式主義的謬誤,使西方文明的精華難以為我所用[2](P21)。非思想性甚至盲目暴動的文化迷信向來是創造的障礙,何況從對自由、民主、科學等現代品格的原始追求來看,以徹底打倒中國傳統的思路來迎接現代也并不合理,自由與民主的獲得從來不是依靠一種思想對異己的鎮壓而實現。要使西方文化為我所用,必須使之得以消化,“漢化”為與中國實際相適配的思想范式,而實現其“漢化”,則需在“自我”的觀照下接受“他者”,將西方理念內化于重建中的民族文化體系,盲目吸收有害無益,而“全盤西化”觀念的形成正是未能把握這一根本原則的結果,由之而來的諸多不良后果,也是此認知錯誤的產物。“全盤西化”的倡導者們將傳統中國的各個組成要素視為“同質”之物,而這種“質”在其看來理所當然是陳腐的、落后的甚至反動的,應當盡數舍棄的,因此,在其觀念中,政經體制的落后即等同于文化體系的落后。事實上,經由漫長的歷史沉淀而生成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系是一個復雜的混合體,這與“化合”式的西方文明秩序有所不同,其中內含著多種不同的成分與不同的發展傾向,這些成分與傾向有其獨立的品格與生存空間,其中不乏先進思想與優秀文化。因此,全盤顛覆式的反傳統思想運動看似示好“現代文明”,其本質卻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當這一激進的反傳統運動與潛存于民族記憶深層的“文化民族主義”沖突時,便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股內涵復雜的思想張力,其結果正如有學者所言,造成了“中國思想史與政治史上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2](P175),而查補這些文化偏頗所造成的“漏洞”還需從“前現代”中尋找“補丁”。畢竟,在如此漫長的歷史中逐漸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體系,其對現代中國依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糾偏力,面對現代文化的偏激之處,傳統文化勢必將以其相異的價值取向進行強力修正,以防止中國現代文化陷入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曾經出現的認知誤區。總之,在借西方文化來反抗傳統、實現現代的方略中,無論從西方文化自身還是從中國文化土壤的特異性來看均有障礙,而當我們發現顛覆傳統并未取得預期效果的時候,也是反思應當開始的時刻——我們對西方現代文明的理解和借鑒是否是準確到位、得其精要的?我們是否真誠地將其作為思想與文化的指南針,而非僅僅借其來充當支持與辯解反傳統運動的工具?我們所遺棄的傳統是否毫無價值?而我們所熱衷的西方文化,是否無所不能……我們也應當在這一反思過程中總結究竟怎樣的“現代”是我們需要的現代,怎樣才能在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文化語境中使中國實現現代,而重審傳統,正是這一反思工作應當邁出的第一步。
三
曾有學者指出,“思想史上可能有突然的飛躍,但是那常常是來自精英和天才的思想,一般的知識和思想卻不會有突然的變異,它只是在緩緩地綿延……傳統的殘存是如此強烈的粘固劑,而歷史的象征是如此堅固的石塊磚頭,要在一時就掀翻它是不那么容易的”[3](P78)。這一言論在如今看來無疑是正確的。傳統文化體系的各個組成并沒有(也不可能)隨著傳統文化結構在現代的崩塌而消失殆盡,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支撐民族觀念世界數千年的基本文化結構解體后,穩固可靠的文化新權威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得以重建。因此盡管抱有美好的愿望,但文明的進化沒有捷徑,我們日漸察覺到,中國文化的前行之路從根本而言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溫和過程,而試圖割裂文化傳承而制造天翻地覆的突變只能造成思想范式的失序,中國現代歷史上并不缺少與之相關的沉重事實,因此有學者才會無不感慨的結論道,“歷史的發展需要循序漸進,才能真正得到好處,少有壞處。中國近現代歷史則是一部激進主義獲得極大的成功卻又變成極大的災難的記錄”[2](P561)——我們從未否認現代思想啟蒙運動為中國歷史帶來的巨大意義,然而以決裂的方式追求現代的到來,忽視了文化規律的制約,終將是緣木求魚之道,畢竟,任何一種思想都不可能是空穴來風,外來的異質思想必須與本民族思想有某種契合點,才有可能被接受、融合,正如有論者所言,“傳統架構解體以后并不蘊涵著每一個傳統思想與價值便同時都失去了理智上的價值。一些傳統的思想與價值雖然因原有文化架構之解體而成了游離分子,這些游離分子有的失去了內在活力,但有的卻與西方傳入的思想與價值產生新的整合可能。”[2](P259)此類論斷,為在當前語境下重新審視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以及如何反思傳統并重新考量其內涵提供了良好的認知基礎,也明確標識出內蘊在文化發展進程中顛撲不滅的漸進規律。這種規律不僅體現在宏觀層面,對具體的現代文化主體而言也是難以跨越的戒律。即使在“五四”時代,那些最為堅定的反傳統主義者也缺乏摧毀并重建中國文化體系的內在力量,社會秩序與文化秩序雖已被深深地撼動,但仍未完全解體,在這一“夾生”的語境中,他們仍然視某些傳統的價值與信念為當然,而改變這種“當然”,需要漫長而痛苦的文化磨合。在文化發展規律的制約與引導下,傳統文化在現代文壇(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壇)上從未徹底退場,“東方文化的思維和審美優勢”[4]始終蔓延在文學版圖中。當前在復興民族文化的整體訴求及追逐“中國夢”的文化大語境中,有關傳統文化的討論不僅在學術界異常活躍,而且無論在官方還是民眾話語中,傳統文化的優秀質素也得到了廣泛的認識與敬仰,一些“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曾遭受冷遇的文化保守主義作品也重獲青睞和推崇,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重新獲得了公允的理性思索與評判,其在文學創作和文化宣傳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總體而言,傳統文化的地位以及與文學的關系同二十世紀初期相比是大不相同的,且越近當下,對傳統文化的攻擊越少,親和越多。傳統文化潛行姿態的改變印證了文化發展規律的正確性,由此所折射的文化態度及文化環境的變化是耐人尋味的,而我們之所以不厭其詳地論述種種主觀意識、客觀現象及普遍規律,即是為這種“耐人尋味”尋找結果——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促進下,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時機已逐漸成熟。
四
重審民族傳統文化,并在“取精用弘”中實現其現代復興,是現代反思引發的必然文化取向,也是本土文化心理渴求的結果和文化重建的內在要求。把中國傳統的文化加以創造性地轉化,使之成為我們現代民主自由國家在文化與道德上的基礎,是在確保民族文化身份的同時使現代文明更具合理性及合法性的首要條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審傳統并不意味著抱守傳統文化殘缺,也非盲目癡迷于文化優根性的魅力,否則這將與“全盤西化”在偏激程度和負面影響上并無二致。實際上,這種“全盤傳統化”的重審方式也不存在生成條件,畢竟,審視的主體已是經受現代思想洗禮的現代知識分子而非傳統士大夫,且其審視的客體為現代背景下的中國文化。主客體的“現代化”使審視者們能夠自覺地以更為開闊高遠的視野來反思傳統,令重審工作在起初便帶有了濃郁的現代特性。因此,現代文學發生以來,即使如沈從文等明確地致敬傳統的作家也絕不是以反現代為目的,而是從人的精神層面關懷著現代性,呼喚著一種健全的民族生活方式,以安置一個個漂泊無定的現代靈魂,進而實現現代民族文化人格的再造,自落筆伊始即表現出極為現代的特性。在這種糾葛甚至矛盾的表現中,傳統與現代構成了一組頗有意味的關系,交錯互融,難以割裂,使作為專有名詞的“傳統”與“現代”也變得面目模糊,其約定俗成的含義,似乎也并非如其表象一般邊緣清晰。
因此,在現代語境中重審傳統文化,有必要對相關概念做出更明確的闡釋。就“現代”而言,筆者認為,“現代”與其說是一個歷史時段,不如說是一種歷史發展趨勢,它絕不等同于“西方文明”甚至約定俗成的“現代文明”——現代文明終究有成有壞,其“成”功效顯著,其“壞”也制造出頗多隱患。因此,“現代”更應當被視作一個形容詞來理解,用以描述一種有利于思想認知、文化品格及社會秩序合理性提升的趨勢,畢竟,我們無法說先秦時代有關人生終極真理的討論是“傳統”的,也不能不承認《紅樓夢》中對封建文化不合理性的暴露與之前或同時代文學相比是“現代”的。這似乎也提示我們應當重新理解“傳統”一詞,這對當前重審傳統文化的工作而言至關重要。從本質上來說,“傳統”是一個開放的概念,盡管它極易被理解為封閉、復古、保守的代名詞,但實際上,“傳統”本身蘊含著無盡的變數。以文學為例來言,即使在文化結構極為穩定的古代社會,文學的“傳統性”(與“現代性”相對)也并非凝固于一種靜止狀態,而是經常借助異族文學特色來豐富和補充其民族特色,只不過這種調節缺乏主體自覺意識,未能改變民族文學的質的規定性。進入現代社會后,外來文化的強勢沖擊使民族文學與社會體制一樣,均在質的層面上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文學的“傳統性”也在其動態機制的牽引下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它既承續了傳統文學的民族性精華,又接納了民族社會形態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新變,以現代文化為依據為自我注入了新因素,進化成為新層次上的傳統性。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歷史境遇的不斷變遷使民族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呈現出時代性的變化,文學的傳統性也不斷刷新,但這種具有時代性的“刷新”往往是在對立統一的辨證演變中對固有的“文學集體無意識”的認同、發展和超越,縱使新變,其變之根基仍在“傳統”的大版圖之內。因此,我們所理解的“傳統”絕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概念,它始終處于被制作和被創造的開放過程,永遠指向無窮的可能性,同自閉和倒退絕不等同。正如當代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所闡釋的那樣,傳統是過去與現在在不斷的遭遇、沖突、融合中產生的種種可能,它是流動的而非凝滯的,是變化的而非確定的,是一個屬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概念。這一闡釋從根本上消解了現代與傳統之間不可逾越的障礙,為傳統與現代的不可分割提供了來自哲學層面的論據,也為我們重新理解與闡釋“傳統”提供了思索契機。在“現代”觀照下對“傳統”一詞的內涵與外延做出必要說明,有利于我們明確在當前語境下重審傳統文化的動力與目的,亦將為重審傳統文化的工作提供方法論的指導。事實上,如果意識到傳統并不意味著陳腐倒退,而現代也并不等同于文明先進,那么便可發現傳統與現代并不相悖,古老的傳統中亦有推進文明前行的現代因子,而現代也不等同于反傳統,而是傳統的自我篩選、轉化、優化與升華。以現代為背景和目的來回望傳統,收獲的將并非單一、對立的某一方,而是一個內涵豐富的“現代民族傳統文化”,而這一暗示著融合與共生的偏正短語,或許是為何中華民族經歷了西方文化的殖民與同化的洗禮之后,其文學仍能作為特異性國別文學參與世界文學譜系繪制的最簡明準確的答案。畢竟,文學的現代化并非以消除文學的傳統特異性為前提與目的,它對待各民族文學的態度既非同化也非合并,其本質意義在于為各民族文學的生成與發展提供更充實的營養和更豐富的參照系。因此,在具體方法上,重審傳統,不是簡單地重返過去,它應當以追逐“現代民族傳統文化”為指向,施展從內到外的融合行為,既非采取“以夷制夷”的辦法來拒斥“異質文明”,也非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洋務運動”來維護傳統的政治制度與文化精神,更非“全盤西化”的謬論,而是力求審慎地對待傳統與現代,既祛除傳統文化糟粕,吸納現代文化精華,也在謀求現代化的同時,將中國文化的特質與優根性組成在現代化轉變的過程中保留下來,并發掘其之于“現代”的意義。簡言之,當以現代人的眼光,帶著今天的問題,在對傳統進行現代解釋的基礎上,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推進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思想資源和人文智慧,從自身中尋找實現“文明進步”的可能性,同時,也為外來思想尋找相應的契合點,考量中國應當怎樣在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打開現代性之維。這既是用現代視野對傳統進行去偽存真的過程,也是用傳統力量糾偏現代弊端的過程。因此,我們在現代語境下回溯傳統,重審具有根性意義的傳統文化并取精用弘,并非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內蘊了負載傳統和反觀現代的雙重目的,是現代中國呼喚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文化體系、新的價值學說和新的意義世界所要做的重要工作,是尋找使“現代”在古老中國抽枝結果的方法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是在文化全球化語境中保持民族文化人格、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必然之舉。
在現代思維的觀照下重審傳統文化,將會逐漸在審視的過程中構建起一個現代民族文化體系的模型。它將建立在對傳統中國文化及現代西方文化真正的了解上,而非僅憑對兩者(尤其是現代文化)的教條式理解來構設中國文化,它應當是中國的、現代的,既具古典氣韻,又有現代新風。這一整合生成的全新文化體系無疑擁有巨大的意義空間,能夠貼切反映著中華民族的現代民族品格和深層文化心理,確立民族文化身份,強化民族文化深度,保障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對話性,糾偏西方文化席卷下文化與文學的異化,呼喚與引導著優雅、和諧、審美的民族新文學的誕生,并能促進理論建設的“現代中國化”進程,建立可準確、貼切地理解本國文學魅力的批評體系。它是民族文化認同的起點,是理解并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步驟,也是現代中國文學展示自身魅力、走向世界的前提。這將是當前語境下重審傳統文化所結出的芳香果實,同時亦是我們迫切期待重審傳統文化的原因與動力。
[1] 胡適.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M].上海:三聯書店,1998.
[3]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4] 韓少功.尋找東方文化的思維和審美優勢[J].文學月報,1986,(6).
責任編輯:馮濟平
The Necessity and Concept of Reviewing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Current Context
YAN Xiao-yu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 The time for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 culture is already mature under the current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Judging from the deep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modern culture subject, the failure of the blind Westernization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r from the universal law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reconside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both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However, backtracking tradition does not mean clinging to incompleteness. Wit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from a modern perspective, the optimal and sublimed "modern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e" can provide guarantee and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of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rejuvenation.
identity of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 modern times
G12
A
1005-7110(2016)06-0071-06
2016-04-26
山東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點研究項目“新國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及其價值辨析研究”(15BZBJ08);山東省藝術科學重點課題“傳統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專項課題(Z2014044)
閆曉昀(1982-),女,山東臨沂人,文學博士,青島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