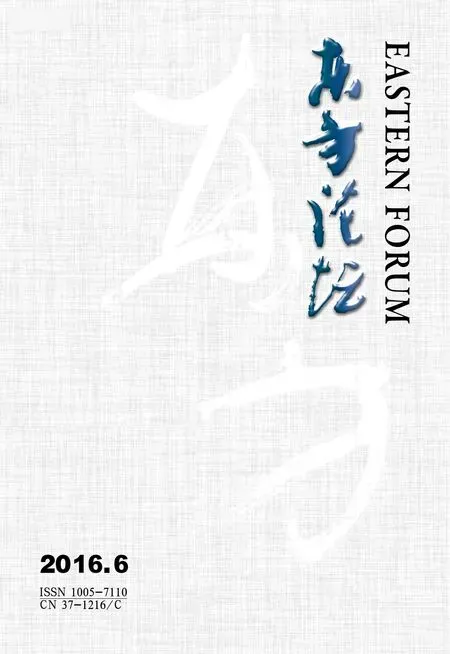中國文化探源與發展研究的新途徑
——評《海陸一體化維度上的東方秘境——不其文化研究》
程 玉 海
中國文化探源與發展研究的新途徑
——評《海陸一體化維度上的東方秘境——不其文化研究》
程 玉 海
在20世紀中國歷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中,關于東夷部族的聚居、生活與演變,文明與文化的研究,不僅當屬其中,而且其田野考古,史料發掘和整理,理論研究和探索的成果,填補了一系列歷史空白,沖擊和改變著一些傳統的觀點和認識。同時,也將我國歷史文化和區域文化研究,推向了新高峰,并且同文化自覺、探尋精神家園的各項目標密切相聯。鞏升起先生的《海陸一體化維度上的東方秘境——不其文化研究》[1](以下簡稱本書)一書,既屬于上述文化探源和發展研究的范疇,又為這一領域研究的深化,為青島地區史前文明和文化起源、歷史文化發展等方面,探索了一條創新之路,取得了優秀的成果和寶貴的經驗。
一
就近代意義上的青島市而言,其開埠建市,也僅有百余年的時間。但就現青島地區的歷史文化而言,其悠久性和豐富多彩,并不亞于我國其它歷史文化名城或地區。北阡遺址、三里河遺址、城子遺址等,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正如本書所言:青島地區歷史文明的曙光,至少不會晚于距今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時期,到距今4600年前后的龍山文化時期,由“城子遺址”等反映的“古城子人”,即遠古意義上的東夷“不其人”,已達到了“新的繁榮的高峰期”。因此,早在公元前692年齊國滅萊子國之前的漫長歷史時期,這里始終是東夷人的故土,正是東夷人點燃了青島地區歷史文明的火焰。這既是本書充分論證,并有著可靠依據的重要結論,也是對東部沿海地區東夷部族和文明研究的重大成果與貢獻。本書的意義首先表現在這里。
在20世紀前的兩千多年間,我國關于東夷部族和文明的研究極為薄弱,其主要原因是儒家“尊夏卑夷”思想影響的結果,并由此造成了“萬世一系皆出于黃帝”,把“發祥地完全不同的氏族都強隸屬于黃帝名下”的觀點和做法。[2](P6-9)因此,在春秋后長達2000余年的時間里,它成為我國歷史典籍中占統治地位的正統觀點。關于東夷人的研究被邊緣化,甚至成為“歷史空白”。直到20世紀,由于北辛,大汶口、龍山、岳石文化的相繼發現,這種狀況方得以扭轉,東夷部族及其文化的意義,逐漸得到承認。
本書堅持和深化了上述觀點,并充分考證認為:“不其”兩字本身就是東夷文化的產物。“不”字來自東夷原始骨刻文中的“文字符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其”字也指向東夷部族的名稱和圖騰。正如本書所說:“自新石器晚期開始,‘其’字作為專有名稱而存在于歷史記憶之中”,它“首先是東方一個古老部族的名稱”[1](P70)。
在夏、商東夷人的萊夷族群中,存在著一個被稱為“其”的部族,它是“由若干胞族組合的總體”,是萊夷中“最強大的一個部族”,“它所居住的區域相當遼闊”[2](P45)。本書認為:“不其人”,應為萊夷“其族”的一部分。并指出:“上古時代在東方曾有其族和其國的歷史存在,其立族和立國之地就在山東半島”[1](P86),“爾后在中原王朝不斷東擴的背景下,其族和其國的領地不斷壓縮并向東遷徙,從而到了今不其地”[1](P86)。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其”是一個具有特定歷史含義的歷史地理和文化概念,“這是一個古老的東夷部族”,“一個古文化體系”,其“內在于東夷文化大體系中”。[1](P60-88)
本書不僅確定了“不其”與東夷“其族”和文化的關系,還厘清了它的歷史延續和承繼,那就是“不其”由圖騰、族名,而被直接承繼為地名和山名,即“不其地”和“不其山”。此后又出現了“不其縣”“不其城”“不其侯爵”“不其侯國”等六重承繼。這一文化現象極為獨特,它本身已經證明,“不其”直接源自東夷文化,不僅是“直系”,而且沒有間斷。這種文化現象在國內極為罕見,同時,它也從另一方向提供了東夷文化作為中國文化源頭之一的證據。
一個嚴肅科學結論的確立,往往僅需幾句話就能表述清楚,但求證與探索過程的艱辛和痛苦,卻并不為人所知。確立“不其文化”源于東夷文化同樣如此,由于時代久遠,除了“不其山”仍屹立在嶗山西北麓,幾乎沒有多少可供直接使用的現成資料。這也是過去無人觸動這一課題的原因之一。由此,本書所以把“不其文化”喻為不亞于“迷津或阿特蘭蒂斯沉沒”般的迷題[1](P9),也就可以理解了。
作者鞏升起先生很早就認識了這一課題的意義,多年持續不斷的對它進行探索和研究。史海蕩舟,艱辛探索,方撥開迷霧,披沙見金,從而把散落于東夷骨刻文、陶文、甲骨文和金文,大量典籍中的只鱗片爪般的點點資料,發掘整理出來,并在本書中加以全面考證和論述,終解開了不其謎題,為青島地區歷史文化研究,乃至中國文化探源作出了貢獻。
當然“不其文化”源頭的確立,對全面、準確地認識青島地區和城陽的歷史文化極為重要, 它作為與“瑯琊文化”“即墨文化”等基本相同的古文化淵源,共同支撐起了青島地區歷史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平臺,展現了以“不其”為標志的“不其人”“不其部族”“不其文化”,以及包括“古城子人”在內的青島地區古先民,在這塊廣闊的東夷故土上聚居、漁獵、航海、生活,以及創造文明和文化的過程,從而揭開了青島地區古歷史文明的神秘面紗。當然,青島地區和城陽,在全國、齊魯和山東歷史文化中的地位,也就在其中了。
二
“海陸一體化”和“東方中的東方”,是本書提出的兩大命題,也是本書的重要思想和觀點,它與“不其文化”東夷起源說,共同構成了這一文化形態的基本特征。它說明“不其文化”的意義,還深深植根于海洋文明與文化之中,無論是不其地東夷故人的航海活動,還是我國古代發生在這里的海戰,春秋至北魏年間與這里相關的大航海,以及古代北方海上絲綢之路等,都充分證明了它的產生與發展,同我國海洋文化緊密相聯,它屬于古代中國海洋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進一步說,它也證明了青島地區歷史文明和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屬性。
新石器時期,也就是龍山文化時期,古人類在從事生產活動的同時已經有了交換,因此就有了交通和古道,而且“路程也許相當懸遠”[4](P695)。我國歷史學界和考古界,依據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遺址點分布圖認為:在新石器時期,我國西部已形成了從中原沿黃河和渭水的古道。同時,我國東部也存在著由“古濟水直到東海之濱的古水道”,并且還是“一條主要的交通道路”,“由東海之濱可以西至渭水源頭”[4](P398)。
莫言創作以其獨特的風格在新時期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無論在內容方面還是形式方面,莫言小說創作都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和創新。一直以來,不少學者認為莫言作品具有狂歡化的敘事特點。從狂歡化理論的形成及其特質來看,莫言小說的狂歡化敘事并不是對狂歡化理論的簡單模仿,而是體現了高密東北鄉民間社會和民間文化的獨特魅力。與歐洲狂歡文化的淵源不同,莫言小說的狂歡化敘事沒有狂歡節慶儀式的喜慶氣氛和廣場效應,而更多地表現了民間底層社會的人生苦難和悲情訴說。
就水運和海運而言,“5000-7000年前已有舟楫的發明”,即原始“桴與舟”,“桴即竹筏,或木筏”,“舟就是獨木舟”,這就是古語中的“刳木為舟,剡木為輯”[4](P398)。
由上可見,至少到龍山文化時期,濱海沿岸居民,已經有了“桴舟”和航海活動。由于東方濱海的原始居民為東夷人,所以,本書認為“早在龍山文化時期,東夷民族已創辟大航海史詩而傳播文明于太平洋兩岸”。
不其地的“古城子人”,作為東夷部族的一部分,無疑應屬于具有航海活動的古人類。“古城子遺址”發現的“蚌鋸”等原始工具,說明他們已具備建造“桴舟”的條件和能力。當時,古膠州灣的海岸線,可直接到達今城子遺址附近。擁有如此理想的海灣航海條件和能力的“古城子人”,為了生存與發展,也必然會有航海活動。為此,本書認為,“古城子人”不僅開始了航海活動,而且在膠州灣東北岸不其地海域,還會“存在著古港”,“至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關于東夷人、“古城子人”航海和古港的更直接證據,雖然還有待于未來的考古發現,但本書提出的觀點,已具備了一定的事實依據,仍應為可靠的結論。
商、周時期,這里的航海活動不僅已很頻繁,而且開始了遠洋航行,周初的箕子東渡,就已到達朝鮮。有一種觀點認為,箕子由膠州灣出航進入遠洋。如果這一事實成立,那么它對“不其文化”海洋屬性的意義不可估量。本書也非常慎重的記述了這一點。
早在春秋戰國之際,我國南北海上航線已經通暢,如《左轉·哀公七年》中的“吳之舟師自海入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中的范蠡“浮海出齊”等。當時,吳、齊等沿海諸侯國,各自的海上戰船已達到數百艘,吳、齊兩國還在瑯琊海域打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海戰。這就證明,到春秋戰國時期,我國海船已適應遠程航海,已積累了海運和航海經驗。史料記載:此時我國商船已能由福建一帶,到達今越南和印尼,這應為最早的海上絲綢之路。
秦漢時期,我國“沿海地區的海運確已相當發達”[5](P686),雖然漢武帝時期已打通了出使西域的陸上“絲綢之路”,但由于陸路交通不斷被阻斷,“我國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大秦諸國的國外交通線”,首要的還是“海上交通線”,即“海上絲綢之路”。到漢末三國前,人們甚至一度忘記了陸上通道,“只知道有通往大秦的水道”[5](P686)。
以上充分說明了兩點,一是包括不其地海域和女姑口在內的膠州灣兩岸,早在春秋時期已是由海上出入齊國的必經之地,已成為具有戰略意義的海上運輸和海路交匯之地。公元468年,為爭膠州灣和不其地的控制權,建都南京的劉宋政權,同北方的北魏,曾在女姑口海域,爆發了一次大海戰,這也是我國少有的幾次大海戰之一。可見,至少從春秋戰國起,膠州灣和不其地,在海運和航海方面已具有巨大的意義。我們今天對這方面意義的估價,可能仍然不足。二是由于我國南北海上航行和貿易的通暢,北方的黃海和渤海,不可能不參與到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之中。為此,膠州灣和不其地海域,在古代北方絲綢之路中,也必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從秦漢到東晉年間,曾有過三次大的航海活動涉及不其地海域,并對“不其文化”產生重大影響,這包括:公元前219-前210年,徐福兩次東渡,到達日本和朝鮮;公元前182年不其人王仲,因“諸呂之亂”而避禍海外,由不其東渡朝鮮;公元413年,東晉高僧法顯,在歷經14年的印度取經后,由海上返回,在嶗山登陸,入住不其城。這三次航海或經不其海域,或直接從不其出海,或在不其地沿岸登陸。
特別是法顯的這次航海,不僅對不其文化影響巨大,而且是中國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公元399年,即佛教傳入中國300余年后,高僧法顯為解決佛經中的難題,毅然走上了徒步西域取經之路,直接到達印度,攜經而歸。他的西域取經,不僅早于唐玄奘230余年,而且開創了佛教史上的“法顯時代”。按湯用彤先生的說法,“故海陸并尊,廣游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返者,恐法顯為第一人”[6](P380)。法顯由印度到達斯里蘭卡,轉海路返回,經孟加拉灣、跨印度洋到南中國海,又經廣州,到東海、黃海,在嶗山登陸。
法顯的這次航海說明,早在鄭和七次下西洋(1405-1433年),達伽馬(1498年)繞過好望角,從西歐到達印度1000余年前,法顯的船隊已經完成了由印度洋到達黃海、渤海的航程。這同時也證明,由不其地海域、膠州灣,可直接到達印度洋。這就為古代北方海上絲綢之路,為不其地沿海口岸、女姑口等,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作用和地位,提供了更具體的證據。
同時,它對“不其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法顯登陸后,郡守李嶷躬自迎勞,法顯“持經像隨還”,進入不其城。法顯駐不其城期間的談話和活動,必然涉及佛經、佛事等內容,所以他到達不其城,以及他對此地佛教興盛的影響絕不可低估。正如本書所說“在不其地,高僧法顯必有講經之為”。同時,他到達本身,也“提示了佛教海上傳播路線的相關問題”,“法顯登陸對不其文化的意義不可估量,在佛教中國化和海上絲綢之路時空中打下深深的不其烙印”[1](P173)。
上述事實已經揭示了漢武帝把不其作為走向海洋東方的大門與橋頭堡,設立明堂、太一祠、交門宮的真實原因,同時也證明了本書提出的“海陸一體化”和“東方中的東方”命題的正確性。當然,這兩大命題還如點睛之筆,使人們豁然開朗,茅塞頓開,它不僅是解開“不其文化”謎團的鑰匙,而且在本書提出的構建我國海洋歷史文化體系任務中也具有重大意義。
三
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文化形態,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已基本形成。所以,漢以后在不其縣名下發展的“不其文化”,既是“存在于中國東方的一種地域文化形態”,又是傳統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部分。本書認為:“不其文化”包括了“帝王巡狩史、海上求仙史、明堂淵源史、太一崇拜史、道教史前史、經學流變史、佛教傳播史、海上交通史、中外關系史”[1]等九重內涵。它在漢后800余年發展過程中,不僅內容不斷豐富,而且高峰迭起,包括漢初的明堂文化和太一文化;王吉、房風等不其儒學家、經學家群體,伏湛、鄭玄等集結于不其的知名碩儒,在這里創造了幾度輝煌的兩漢經學;佛教在這里的興盛,以及由此導致的關于我國佛教傳播路徑的思考等等。由此可以看出,發生于這里的一系列重大歷史文化現象,雖然有著鮮明的地域烙印,但它實際已完全超出了地域的范疇,已屬于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重大課題。
正確把握“不其文化”內涵的豐富性和雙重性,既是完成課題的基本要求,也是構成它文化特色的基本要素,同時,由此也決定了這一課題的艱巨性,并考驗著作者的意志和水平。當然,課題的完成、成果的優秀,其成功的奧秘在這里,給人們的啟示也在這里。
盛世修史,當今縣域、區域歷史文化研究方興未艾,而本書把地域、區域文化研究,放到了中國歷史和文化,齊魯和山東歷史和文化的大格局中加以探索,比較和研究,把“不其文化”,放在東夷文化,中國歷史文化起源,歷史文化發展與演變的大趨勢中,探其源流、觀其發展、述其意義、升華理論。正如本書所說:“闡述不其的歷史基脈和文化精神……完全可以將其結合到我們對古代中國文化精神的理解中去,結合到我們對大歷史的對話中去,結合到我們對古代中國海洋文化的體系的反省中去。在宏闊的歷史景深和文化背景上,同樣具有適應力,而且在中國本土文化與域外文化多元對話中同樣具有適用力。這也是參透中國傳統意識,并完善天人合一關系思維的一個合理的渠道”[1](P104)。這段近乎哲學意義的論述,實際在指明一種方法論的思想,那就是既要登高望遠,使“不其文化”與中國、齊魯和山東歷史文化的起源、發展,多元比較渾然一體。由此把握“不其文化”的發展演變規律,總結歷史經驗,展現其歷史意義和光輝。同時又要俯視不其,扎扎實實的收集、整理、探索、研究各種資料,再現歷史軌跡和真貌。把握基本特色和特點,從而既避免就事論事,就縣論縣,先天不足,落入俗套,同時也能以小見大,在“小史”研究中,展現博古通今的“大學問”。這種方法和結果,無疑為區域歷史文化研究闖出了一條成功之路。
歷史文化研究并非總是古語、古董、古事與古板,重要的在于總結和反思歷史經驗,本書實現了這一基本要求。作為“史書”,它清晰的展現了基本歷史線索,使讀者較容易的把握歷史順序和歷史過程。作為總結經驗和反思,作為文化研究,它又處處閃爍出仰望星空、說古論今、升華理論和哲學反思的光芒。當然,文化浪漫和暢想,也使本書文字活潑、引人入勝、發人深思。如本書提出的“一地之興,必有一地之史”。“海洋是大地的載體,大地是海洋的歸宿”。“中國思維是圓的,起點和終點合一”。“今天看到的是自然,上古看到的則是神奇”等觀點。再如“今天是歷史和未來的聯結者、溝通者,今天的精神世界有歷史和未來同時貫注的光輝”。“大自然構成的文化基因,在自然與文化的融合中形成地脈、文化之脈”。“中國文化精神統一而多元、南北分殊、東西異稟”。“一瞬與亙古之間,如星辰般稀有,而豐富的語言可以參透自然、參透世界”。等等。這些極富哲學意義和哲理的語言,在文學浪漫的表達方式下,顯示出它的優美、通透和理性。這是本書的又一成功之處,也啟示著人們如何作好歷史課題。
一部優秀的著作,雖然包含了艱苦的文字和寫作功夫,但它也決非僅僅是“寫出來的”,它首先是作者長期探索和研究的結果,淵博學識,扎實的功底,豐富的歷史文化積淀厚積薄發的結果,說到底還是“面壁十年圖破壁”,“十年磨一劍”和“甘做冷板凳”等學術精神的結晶。這既是完成課題的基本條件,成功的基本奧密,也是學人應有的本色和科學精神。
在《海陸一體化維度上的東方秘境——不其文化研究》出版之際,我們看到了它為新一輪區域歷史文化研究所提供的這一范本,探索的新途徑和經驗,它對青島歷史文化研究等多方面的意義和啟示。同時,我們也看到,作者以極為嚴肅、認真和負責的態度,已經開啟了新的研究與探索的航程,即直面由于史料、時機、個人認識等因素所導致的某些缺憾,繼續深入探討在膠州灣沿岸,以及日照、泰山一線,古東夷各部族的關系、文明與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古不其人航海,以及古港口發展的研究;古不其文化、瑯琊文化、即墨文化、膠州文化、嶗山文化等關系,它們對青島歷史文化起源與發展的整體意義,及一體化研究;關于佛教在我國東部地區,特別是膠東和青島地區的傳播路徑、發展狀態、獨特意義等方面的研究;關于重構我國海洋文化體系方面的研究等等。
生命不息,研究未終,學人歸宿,可貴可泣。
[1] 鞏升起.海陸一體化維度上的東方秘境——不其文化研究 [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2] 李白鳳.東夷雜考[M].濟南:齊魯書社,1981.
[3] 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M].青島:青島出版社,2006.
[4]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作者為山東省政協常委,青島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