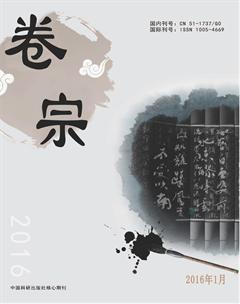淺議馬克思的歷史研讀方式及阿爾都塞“歷史無主體”論
崔琳菲
摘 要: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人——即“歷史的主體”的論述,在其后時代不斷被人深入研究。其中,阿爾都塞提出了一種新型的歷史研讀方式和生產方式總結理論,并提出“歷史無主體”理論。今天,我們從20世紀著名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那里,尋求“人在歷史上是否具有主體地位”這一問題的答案。
關鍵詞:《資本論》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解讀;阿爾都塞;無主體
曾有人說,21世紀是“人”的世紀。對于這句話的解讀,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認識。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史。上兩個世紀中,人類科學技術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然而,隨之而來的是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枯竭,人們慢慢將視線更多轉移回我們的生存環境——可以稱之為“人本主義”或者說“人文關懷”。不僅如此,我們還發現,人們越來越急功近利,追求所謂的成功,無非也就是在當代生產環境中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各類資源財富,這樣的情況愈演愈烈,人們逐漸開始反思——“人”本身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人是否具有主體性地位?
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論述過抽象的人的具體問題,將人置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探討人在其中與其他人、物以及整個社會的關系。在他看來,人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形成了異化,即我們所知道的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論述的異化勞動理論。
“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審視歷史的視角是一種歷史的觀點,只有基于現狀,對過去有著深入的把握和認識,才能在對比古今異同的基礎上,認識到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跡和文明智慧的留痕。正如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中說到的:“這種必然的回溯只有在現實存在達到科學自身、批判自身、自我批判,也就是說,只有在現實存在是一種使本質變得可見的‘本質切割時,才是科學的。”
阿爾都塞在其著作中就曾這么描述:“《資本論》的敘述方法就是同概念的思辨起源混在一起了。而且這種概念的思辨起源又同現實具體本身的起源,也就是經驗歷史的過程相一致。”阿爾都塞從馬克思的這種歷史分析方法入手,尋求到了一把歷史研究的鑰匙。
“生產關系的結構決定著生產者地位和擔負的職能,因此,構成過程的真正主體不是占有者和執行者,不是‘既定存在的事實,不是‘具體的個體、‘現實的人,而是這些地位和職能的規定者和分配者,即生產關系以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生產關系理解為社會中的一張大網,或者說一種規則嚴明的游戲規矩,每個具體的參與主體必須依照其指定的規章,進行有度的自由活動,不論其中抽象的人還是具體的人,都只是大機器運作下的一個參與者,并不能直接對生產方式這臺大機器做出任何反作用,因此,我們可以把其中的參與者抽象化,使之不會因其發揮了過多的主觀能動性而對整個社會進程造成影響,在阿爾都塞看來,如此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生產構造和主體性。
類似的,從近代哲學以來的歷史上看,“主體”一詞的通常指“人”,由于“關系”并非與“人”屬于同一類別,因此不能把關系設定為主體的范疇。因而可以說,人不是歷史的主體,而是被歷史決定的。人只是一定歷史結構中的地位和職能的“承擔者”與“執行者”,其歷史地位和作用是由社會關系的總體結構所決定的。歷史關系本身不能被理解為主體,因此,從哲學史發展的這一角度看,仍然可以得出“歷史是一個無主體過程”這一結論。
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哲學中的歷史是無主體的,而凌駕于具體個人之上的社會結構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主體,但由于它是無人身的存在、不可還原為人的東西,因此它又不能被理解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主體范疇。阿爾都塞寫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的,是使歷史產生的結果作為社會而存在的機制……而不是作為一盤散沙、一群螞蟻、工具的堆砲、人的簡單集合而存在的機制。”馬克思也曾直言到:“我的分析方法……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時期出發”阿爾都塞還深刻地看到,將抽象的人作為思想的基點,不僅在理論上是反科學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這是因為,“一切人道主義的意識形態全都求助于道德,而道德對于解決真實問題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
在這里,我們暫且不談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否涉及了道德領域,以及即便談到道德,又是如何論證道德與社會發展及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的。我們可以從上述引文中清晰地明白阿爾都塞解讀馬克思關于“歷史主體”問題的思路:個體的人是零散雜亂的,我們在對歷史進行宏觀把握的時候,需要將研究問題的視角上升到一個更具有概括性的層面——那就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因為只有生產關系才像一個網格一樣,可以讓每個個體的人對號入座,并且可以很好地解釋人類活動的共性及差異。然而,很遺憾的是,生產關系并不能算作“主體”概念,其抽象性、可變性與非實在性決定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無主體性。
進一步的,我們需要了解為什么生產關系不能算作“主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提出反對讓具體的個人向歷史運動負責,因為具體的個人被牢牢綁定在生產關系、社會結構的鐵鏈之中。馬克思曾明確提示到:“這里涉及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
然而,阿爾都塞進一步對這一思想進行了豐富和拓延,將其從歷史領域推及到了社會和科學領域,形成了涵蓋從科學到社會歷史領域全方位的“無主體”思想。歷史領域的“主體”——生產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社會結構關系,是一種異己性存在,決定了人在社會領域的地位和作用,這樣人就在社會領域中喪失了主體性。“人,或者主體被放在具體的矛盾中,即所謂‘社會歷史無主體,但主體存在于社會歷史中。結構的復雜性和異質性決定了人在其中的離散,阿爾都塞引入歷史時間和差異時間等概念說明人的存在狀態和方式,總體性的時間與個體的時間是不同一、不一致的。”至于對科學無主體的說明則用不了多少筆墨,甚至不用引入復雜的結構性思維和概念。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實證性不論在法國傳統的科學認識論中還是在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認識論中都被廣為認同,科學真理的客觀標準使科學“無主體”思想成為三個層次“無主體”思想的邏輯牽引。
任何哲學理論在某種意義上說都是開放的,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資本論》問世之后,各個時代各個國家都有大量哲學家為其做注腳,由“無主體”性演化出來的人道主義觀點也是多年來討論的一大熱點,在后現代哲學那里,其理論確定的主要標志就是對人道主義理論基石的“人”,即“主體”概念的否定。在反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后現代哲學與阿爾都塞是完全一致的。至少從 17 世紀以來,“人”的概念已充斥宗教、科學、政治學各領域,并匯聚成人道主義的洪流。只有解構了“人”的先在性、中心性、絕對性、超驗性、自主性等一系列傳統人道主義賦予“人”的特權之后,在宣告了被傳統人道主義奉為神明的“人”的死亡之后,用福柯的話說,就是用“人的死亡”時代取代“上帝死亡”時代之后,才能從根本上摧毀傳統人道主義。理查德·舍希納在《人道主義的終結》一書中就稱,“所謂人道主義的終結”就是人的“自大傳統的終結”。
在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和快速集約的時代,生產方式確實可以像一張網格一樣將個體的人控于其中,因此,不論抽象的人還是具體的人,都是一定生產方式下勞動的個體,是“散沙”,這是把歷史主體視為“生產結構”這一更本質的要素,本無可厚非。然而,任何理論需要因時而異,當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后現代時期時,我們發現,我們更加關注人們的文化活動和精神現狀,相應的,生產模式已不再像馬克思所處的年代那樣,大規模的集約化生產,相反,人力更多被智能取代,人的主體地位慢慢凸顯。因此,我們現在并不急需下結論“人是否為歷史主體”,但是,我們必須明確兩點:其一,任何理論要結合時代背景,不同時代人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其二,不管何種年代何種背景,不管思想主流是否承認人的主體地位,但“人”一定是我們關懷的主要對象和服務和終極方向,任何時候我們都要明確自己所處在的地位與應該在的地位。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第756、757頁
[2]阿爾都塞 《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第139頁
[3]阿爾都塞 《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第139頁
[4]《阿爾都塞“無主體“思想及其對后現代哲學的影響》 關凌凱著
[5]阿爾都塞 《讀<資本論>》 李其慶,馮文光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第53頁.
[6]馬克思 《評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7]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 商務印書館2006版 第245頁
[8]《資本論》 第一版序言
[9]《阿爾都塞“無主體“思想及其對后現代哲學的影響》 關凌凱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