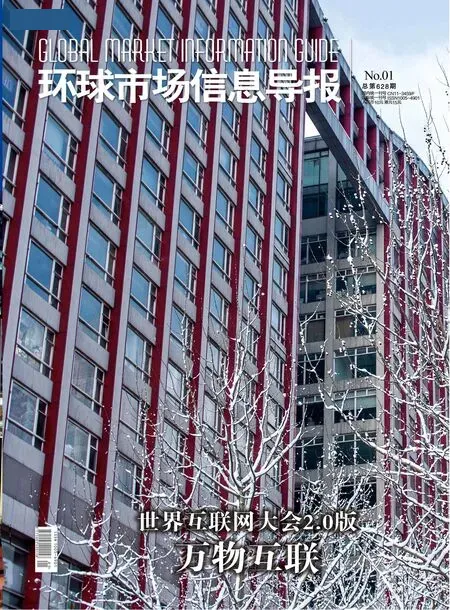申舶良專欄 | 《安提戈涅》在美國
?
申舶良專欄 | 《安提戈涅》在美國
申舶良:

1984年生,2008年起在全球當代藝術領域從事批評、策展、翻譯工作,2010至2013年任ARTINFO中文站資深記者,現就讀于紐約大學博物館學系。從9月24日在紐約布魯克林音樂學院的哈維劇院(BAM Harvey Theater)開場,經過在卡羅萊納表演中心和密歇根大學的短暫逗留,至10月25日在華盛頓的肯尼迪中心結束,正好在美國度過秋意最濃的一個月。
作為曾以觀看朱麗葉·比諾什主演的《藍》《布拉格之戀》《屋頂上的輕騎兵》等影片的盜版光碟為電影啟蒙的一代人,我自會興沖沖地趕去觀看紐約的首演。除去在影壇璀璨的榮譽——諸如出演《英國病人》榮獲奧斯卡最佳女配角,出演《濃情巧克力》榮獲歐洲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等,比諾什的全球戲劇舞臺經驗也一直耀眼。除去從影之前的早年戲劇生涯,還包括1988年在巴黎出演契訶夫的《海鷗》,1998年在倫敦出演皮蘭德婁的《赤裸》,2000年首次登臺百老匯出演品特的《背叛》并獲美國戲劇界最高榮譽托尼獎提名,以及2011年在阿維尼翁戲劇節出演斯特林堡的《朱莉小姐》。
在《安提戈涅》巡演紐約的一周,美國東部正經歷一場史上罕見的暴雨,周邊州城被水淹沒的照片不斷現于社交媒體,學校連續發出颶風警報,朋友分享當年親歷“桑迪”的慘狀。雖然颶風最終繞路,整座紐約城中還是像冬天一般潮濕和寒冷,密雨不止,連串的咳嗽聲回響在首演當天哈維劇院的表演空間——該劇院的前身壯麗劇院(Majestic Theatre)成立于1904年,盛極一時,在上世紀60年代電視文化興起對劇院產業的沖擊下關閉,荒棄20年。直至80年代布魯克林音樂學院院長、戲劇出品人哈維·利希滕斯坦為英國戲劇導演彼得·布魯克長達9小時的劇目《摩訶婆羅多》尋找表演場地時看中此處,改建為哈維劇院,傾頹的磚墻、朽壞的建筑構件、褪色的彩繪,卻都盡數保留,充滿古舊、空闊、詭異、破敗之感。這樣的季節,這樣的場地,正完美地適合《安提戈涅》中死亡與埋葬的主題。
《安提戈涅》是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代表作,也是一部政治神學的經典文本,與《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洛諾斯》合稱“忒拜三部曲”——俄狄浦斯被命運操弄,弒父娶母,成為忒拜國王,生子波呂尼刻斯與厄忒俄克勒斯,生女安提戈涅與伊斯墨涅。俄狄浦斯死后,波呂尼刻斯與厄忒俄克勒斯為王權兄弟相爭,引發“七雄攻忒拜”一場酣戰,終至同歸于盡。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即位,宣布守衛忒拜的厄忒俄克勒斯為英雄,為其舉行隆重葬禮;宣布攻打忒拜的波呂尼刻斯為叛國者,下令禁止下葬,曝尸荒野,為鳥獸食。波呂尼刻斯對于克瑞翁是國家的敵人,對于安提戈涅是同父同母的兄長。對于克瑞翁,將叛國者曝尸荒野是對治理國家有益的法令。對于安提戈涅,埋葬死者是天道,也是神意,神的律法高于人的律法,她因此自行埋葬自己的兄長,觸犯了人的律法,遵行了神的律法。安提戈涅心中的神意、天道與克瑞翁心中世俗王法的沖突正是《安提戈涅》的悲劇起因,在兩人就如何對待死者的問題上產生的爭論中激烈痛苦地展開。
本劇導演伊沃·馮·霍夫是荷蘭阿姆斯特丹劇院(Toneelgroep Amsterdam)的藝術總監,1996 年起同時活躍于紐約戲劇工坊(NYTW),相繼執導過尤金·奧尼爾的《更莊嚴的大廈》,田納西·威廉斯的《欲望號街車》和蘇珊·桑塔格的《床上的愛麗絲》等劇,還將在今年冬季與大衛·鮑伊合作推出由沃爾特·戴維斯的小說《天外來客》改編的劇目《拉撒路》。他在《安提戈涅》的導演闡述中提到排演此劇的靈感部分源自 2014 年 7 月馬來西亞航空阿姆斯特丹至吉隆坡航線MH17 班機在烏克蘭沖突地區上空被擊落后,荷蘭政府舉辦莊嚴的儀式迎接遇難者遺體回國,被國際新聞界視為文明、人性的舉動——在死者總是被作為新聞報道中的一串數據簡化的當下,通過一部古希臘經典悲劇重新思考應當如何對待死者的問題別具意義。
今年7月,正是本劇導演提到的“馬航”事件一周年,《安提戈涅》在美國巡演的海報貼滿了紐約的地鐵,海報上標語印得無比醒目——“埋葬死者,還是奉行法律?”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法律一詞在美國變得有些吊詭。6月26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用5:4的投票結果,宣布同性婚姻合乎憲法,一時間我的微信朋友圈和Facebook全被一種時髦的歡呼和對于美國自由民主平等開放的贊美刷爆。然而,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在司法原則的層面上發文表達了對此事的憤怒,涉及法治與人治的問題,《安提戈涅》中兩方的沖突被再度觸碰:“最高院宣布超過半數州的婚姻法無效,強制改變一個數百萬年來形成的人類社會基礎的社會制度……多數法官今天忽視了司法角色的局限性。他們,在人民還在激烈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把這個問題從人民的手中剝奪了。他們的決定,不是基于憲法的中立原則,而是基于他們自己對于自由是什么和應當成為什么的理解(引自袁幼林譯文)。”

對于美國的基督教信仰群體,這條法令使人為難。《圣經》有禁止同性戀的篇章,但如果一位牧師執著于此,拒絕為同性婚姻祝福,便是違背憲法,這便有如《安提戈涅》幽靈的當代回歸,神意與世俗法律間張力的再臨。對于美國的普通民眾,這條法令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一個禁忌話題,加深了冷漠與誤解。我剛來美國時不斷被新朋友告誡說種族與性取向的話題在美國是禁忌,談論者會被扣上歧視與憎恨的大帽子,我這樣做策展和寫作的文化工作者就更要注意,必須政治正確,只能在被允許的范圍內積極、正面地談論。每個人都能給我舉出大量因無心觸犯禁忌招致公眾輿論之怒而身敗名裂的文化人的事例,頗像菲利普·羅斯的小說《人性的污穢》中的情節。作為少數族裔,又是學生,我很多時候能感到自己受到美國生活中平等、包容、多元、相對主義的普遍氛圍的保護。但也有很多時候,如果對某些話題懷有觀察和了解的興趣,又因此發現問題而提出不合時宜的見解,就很容易被視為這種平等、包容、多元、相對主義的普遍氛圍之基礎的惡意破壞者,瞬間變為某種不可救藥的壞人形象,遭到義正辭嚴的斥責,這樣一種氛圍也彌漫在本版《安提戈涅》全劇中。
在索福克勒斯的原作里,歌隊既扮演克瑞翁身邊的長老,又扮演忒拜城中民眾,時而傾聽克瑞翁的宣告,時而傾聽安提戈涅的哀哭,不斷思考,動搖,做出熱烈的回應,有飽滿的思緒和情感。在本版劇中,歌隊被拆散為單獨的個體,每個人都以一種平等、和氣、包容、冷漠、單向度的方式進行勸導,重復著克瑞翁的道理,有如一池死水,也因此失去傳統古希臘悲劇中歌隊的儀式感和莊嚴感。
克瑞翁這樣一個暴君的角色也被帕特里克·奧凱恩(Patrick O’Kane)演得好像一個略具威嚴的當代公司管理者,以一種看來周詳得體的方式表述懲罰叛徒有益國家群體這一看來完全正當的理論。只有安提戈涅表現得歇斯底里, 激烈抗爭——在這樣的氛圍中,抗爭也難免顯得單調,比諾什好像一個女憤青在與她完全無法交流的人群中徒然喊叫、摔打,有些讓她的影迷們失望。

紐約布魯克林音樂學院的哈維劇院(BAM Harvey Theater)
安·卡森對于《安提戈涅》的翻譯接近一種當代詩劇的再創作,以極少主義文本的方式,將長段對白簡化為許多孤立的詞語,并對詞語進行發明和重構。克瑞翁對安提戈涅的一段斥責由十個“自我”(auto-)作為前綴的詞語構成,如“自治的”“自我說教的”“自我移情的”“自我治愈的”“自我歷史化的”“自我欺騙的”。這也是當下世界交流狀況的縮影,人們不再關心連串的句子中的運思過程,只憑借孤立的詞語來進行判斷。社交媒體對于詞語的迅速掃視和迅速定論,人因為言論中不當的詞語觸犯公共禁忌,又因而被“歧視”和“憎恨”等簡單的詞語所否定。克瑞翁堅信個人的親情不能大于國家的秩序,安提戈涅則說“我生來是為分享愛,而非仇恨。”在當今美國,關于普世之愛與關于民主秩序的論調卻合而為一,形成一個鋒利的大幻影, 使思想與言說著的個體驚恐躊躇。
在索福克勒斯原劇的結尾,安提戈涅被克瑞翁下令活葬在波呂尼刻斯墓穴,克瑞翁的次子、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海蒙聞訊自殺,克瑞翁之妻歐律狄克慟子之喪亦自盡身亡——克瑞翁的家庭崩塌,只求自己的末日到來,最后以歌隊告誡人不可狂妄觸犯神意,年歲增長更應學習智慧而劇終。二戰結束后,在瑞士流亡的德國戲劇家、詩人布萊希特由荷爾德林的德譯本改編《安提戈涅》,將克瑞翁寫成一個窮兵黷武的軍事獨裁者,有面戴酒神面具與忒拜長老們狂歌狂舞的場面。劇中核心矛盾不再是神意與王法,而是克瑞翁代表非理性的酒神精神之惡與安提戈涅代表的正義和人道。結尾不再是家庭的崩塌,而是克瑞翁的長子墨伽柔斯率兵攻打阿爾戈斯陣亡,軍隊覆滅,克瑞翁的獨裁統治和軍事宏圖化為泡影。
本版《安提戈涅》的結尾則顯得非常困難,導演頻繁使用間離手法,人物激烈地死去,又忽然起身扮演旁觀者發表大段議論,使本就很難產生代入感的觀眾更加不斷地出戲。最終人物散去,兩分鐘的短片投射在舞臺背景:克瑞翁凝視安提戈涅蒼白的尸體,用布遮蓋,鏡頭移向當代都市的夜景,樓群矗立,車燈閃爍,一切都沒有被動搖——這個時代已難以產生一種悲劇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