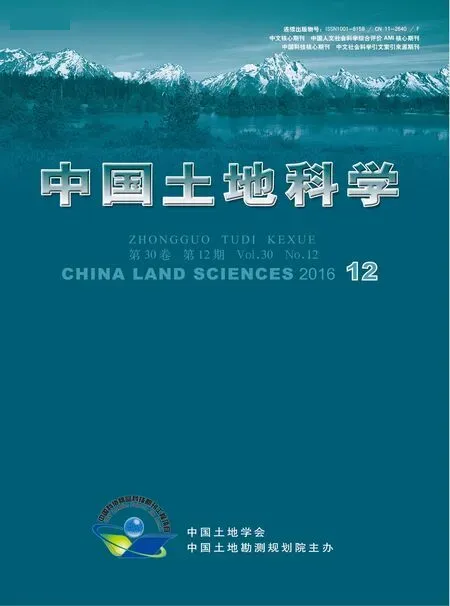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影響因素及區域比較
——地級城市面板數據分析
許明強
(1.成都大學旅游與經濟管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6 2.西南財經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四川 成都 610074)
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影響因素及區域比較
——地級城市面板數據分析
許明強1,2
(1.成都大學旅游與經濟管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6 2.西南財經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四川 成都 610074)
研究目的:發現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影響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和區域差異,提出相應對策以促進工業集約用地。研究方法:根據土地功能理論和經濟主體動力學關系導向原則構建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利用地級城市面板數據估計并檢驗工業用地產出率影響因素及作用程度并進行區域比較。研究結果:城市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就業密度和全要素生產率對1999年來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21.3%、-7%和85.7%;它們對工業用地產出率的邊際貢獻由于東中西部工業用地集約度、產業類型、勞動素質不同而呈現出區域差異。研究結論:應遏制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工業新區建設中粗放用地行為、促進工業投資并加強工業區生活配套以提升投資強度和就業密度,應在工業用地配置和評價中更加重視全要素生產率指標,應推動中西部地區工業升級并在營商環境、基礎設施等方面縮小與東部的差距。
土地利用;全要素生產率;雙向固定效應;工業用地產出率;投資強度;就業密度
1 引言
如何抑制工業粗放用地現象以提升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是中國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中面臨的重要問題。習近平、李克強都鮮明地批評了工業園區鋪大攤子和城鎮土地低效利用問題[1-2],即便在中國工業化先行區上海和廈門等地,工業用地產出率亦偏低[3-4]。在政策實踐上,遵循《工業項目建設用地控制指標》(國土資發[2008]24號)等政策法規的精神,工業用地固定資產投資強度被作為各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重要門檻,那么,重視投資強度的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進了工業用地高效產出?除了投資強度,其他因素——工業就業密度、全要素生產率(TFP)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工業用地產出率的提升?它們有何區域差異?
在CNKI和EBSCO數據庫檢索發現近幾年來關于工業用地利用效率影響因素問題的文獻逐漸增加,這些文獻發現投資強度、就業密度、全要素生產率、土地市場化、政府競爭、區位、產業結構等都是工業用地產出率的重要影響因素,這些因素可分為直接因素和間接因素兩大類,間接因素通過影響直接因素進而影響用地效率。關于直接因素——投資強度、就業密度和TFP的研究觀點包括:(1)工業用地地均資本對產出率的彈性系數為0.346,地均勞動對它的彈性系數為0.142[5],容積率和投資強度達不到建設控制標準[6-8]、工業園土地供需比例過高[9]、土地和勞動力投入冗余[10-11]使得工業用地效率較低;(2)全要素生產率(TFP)尤其是技術進步對工業用地產出率具有重要影響[12-13],對2001—2012年工業用地生產效率實證研究表明全國總體和絕大多數省份的工業全要素生產率呈遞增趨勢[14]。
關于間接因素的研究觀點包括:(1)工業用地市場化改革能顯著提高中國工業用地利用效率,政府干預會降低城市工業用地效率[15],應減少地方政府對工業用地出讓程序和出讓價格的干預[16-17];(2)工業用地價格調控可以有效促進工業用地集聚,從而提高工業用地效率[18];(3)不能忽視廢水廢氣等工業非期望產出,否則會高估工業用地生產效率[19],需通過產業升級以提升工業用地效率[20];(4)政府競爭對城市工業用地利用效率有明顯影響[21];(5)區位因素與土地利用效率緊密相關,城市化率更高的地區比外圍地區更能實現工業用地高效利用[9],需促進制造業的空間布局優化[22],與區位因素類似的還有土地等別影響用地效率的觀點[23]。
在工業用地產出率研究中的計量經濟模型設計上,較多學者采用了生產函數模型,不過土地要素在工業生產函數中出現的形式并不統一。(1)土地屬于資本: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模型的原形中,在索洛[24]、肯德里克[25]和周方[26]關于生產函數的分析中,土地作為資本的一部分并不單獨出現。(2)土地與其他要素并列:丹尼森[27]、陳利根和龍開勝等[12]、林榮茂和劉學敏[28]、楊楊和吳次芳等[29]、王克強和熊振興等[30]、李谷成[31]等學者將土地和勞動、資本并列納入生產函數中作為產出的解釋變量①李谷成、陳利根和龍開勝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將該函數變換為地均產出關于地均資本和就業密度的函數形式,但這種假設與其推導出的函數形式不能兼容。。(3)土地為其他要素的分母:在少數學者構建的生產函數中,土地是作為產出、投資和勞動的分母出現的,比如Antonio Ciccone和Robert E. Hall[32]、黃大全和梁進社[33]、林堅和張沛等[23]。
文獻梳理表明,當前關于工業用地產出率的研究不僅包括了具有基礎影響的直接因素,也深入到了這些直接因素背后的影響因素。不過,關于直接因素的研究更需要得到重視,因為:(1)僅有很少成果呈現了投資強度、就業密度和TFP各因素對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的具體影響程度;(2)對各影響因素地位的觀點仍然存在分歧,比如,吳群教授等認為容積率和投資強度達不到建設控制標準是工業用地投入損失的主要原因[8],陳利根等認為技術進步和投資強度是更主要因素[12],而郭貫成和熊強認為工業行業技術水平對城市工業用地效率的影響還有待檢驗[34];(3)現有文獻大多利用省級面板數據展開研究,僅有個別學者利用地級以上城市工業用地相關數據展開研究;(4)土地要素在工業生產函數中出現的形式并不統一,如何在工業生產函數中以恰當的形式反映工業用地的作用。
本文將以適當的方式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D函數)中反映土地要素的作用,基于中國地級城市工業面板數據,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探討投資強度、就業密度和TFP對工業用地產出率的影響程度,并提出政策建議。
2 模型
如上所述,在工業生產函數模型構建時,有的學者把土地視為資本的一部分將其納入資本之中,但是這與農業領域不一樣,土地在工業生產過程中并不發生消耗和轉移,工業用地與資本具有不同屬性,將其納入資本必須滿足一個很強的假設條件:工業用地總是與資本和勞動相匹配的,恰好滿足資本和勞動的承載需要——這顯然不符合實際。有的學者將土地與資本和勞動要素并列,但在工業生產領域,“土地主要是作為地基、操作的場地與空間發揮作用”[35],在勞動和資本的土地承載需求得到滿足的正常生產情況下,土地對于勞動和資本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邊際替代關系,比如如果減少資本投入,無論增加多少土地都無法實現工業產量不減少。所以,在工業生產函數中把土地作為資本的一部分,或者將資本、勞動和土地三要素并列作為產出的解釋變量都是不夠妥當的,應將工業用地作為其他要素的分母。另外,根據經濟主體動力學關系導向原則[36],模型解釋變量應由被解釋變量的直接影響因素擔任,間接因素與直接因素共同作為解釋變量的做法會帶來多重共線性等問題。由此發展C-D函數構建工業用地產出率面板模型(式(1)):

式(1)中,yit為城市工業生產總值,mit為城市工業用地,kit為城市工業固定資產,lit為城市工業就業量,α和β分別為地級城市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和就業密度②為表述方便,下文一般將“地級城市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地級城市工業用地就業密度”、“地級城市工業用地產出效率”簡稱為“投資強度”、“就業密度”、“產出效率”。的產出彈性。Ait為中性技術進步,是“生產函數任意一種形式變動的簡稱”,“經濟的加速或減速、勞動力教育質量的改進、各種各樣移動生產函數的因素都可歸入‘技術變化’之中”[24],這種技術進步既隨時間而變,也可能因個體而異。
這里討論工業用地單位面積上的資本、勞動和產出,相當于控制土地要素投入使其保持不變,適用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所以α + β<1。也就是說,在包括技術在內的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讓一塊正常發揮承載功能的工業用地的投資強度和就業密度同時增加φ倍(φ>0),其產出率的提高幅度φα+β將在開區間(0,φ)之內。
考慮到樣本點的個體特征、不可觀測的遺漏變量和數據獲得性問題設計以下工業用地產出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

式(2)中,λt為不隨個體變動但隨時間而變的時間固定效應,包括技術進步、宏觀經濟變動、產業政策影響等變量;zi為不隨時間而變的個體特征變量向量,ui為不可觀測的個體異質性,表示不隨時間變動但隨個體變動的遺漏變量,它與zi的差別在于“不可觀測”,z'iδ + ui= ηi為全部不隨時間而變的個體固定效應,包括區位、自然環境、歷史人文環境等變量;ui+ εit構成復合擾動項。
對模型(式2)兩邊取對數得:

3 數據與描述性統計
出于樣本代表性和經濟性的考慮,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從全國27個省級行政區②不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4個直轄市。中按1/3比例抽取地級城市樣本點,當“層個體數×1/3”不為整數時,采用舍棄小數的辦法確定層樣本量,得到包含93個城市的總樣本,其中東部城市29個,中部城市31個,西部城市33個。從《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或《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報》中采集1998③因為《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年報)》自1998年開始編制,筆者沒有發現獲得1998之前年份城市工業用地數據的其他途徑。—2014年各樣本城市市區的工業用地、工業就業、工業企業固定資產和工業總產值等數據形成短面板數據。
關于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指標選取具體說明如下:(1)選取地級城市市轄區數據進行分析,有利于排除因為城市層級不同而形成的差別,有利于排除城市工業與鄉鎮工業和獨立工礦區工業的差別,從而增強數據的可比性;(2)工業就業、固定資產和總產值只能得到規模以上工業數據,和工業用地之間不完全匹配,鑒于地級城市規模以下工業企業占地數量少,在各類工業發展數據中占比也很小,假定它對本文研究產生的偏誤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3)投資強度采用“工業固定資產/工業用地面積”得到,沒有以“年度工業投資/工業用地面積”衡量, 一方面因為所有固定資產都參與了工業生產,另一方面這也是工業用地評價實踐的做法;(4)工業固定資產為經過扣減折舊、減值準備之后的期末余額;(5)由于地級城市市轄區缺乏部分年份的工業增加值統計數據,采用“規上工業總產值/工業用地面積”衡量市轄區工業用地產出率;(6)以 “工業就業人數/工業用地面積”衡量就業密度。
數據處理工作包括:(1)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GDP平減指數,然后把歷年工業生產總值、固定資產價值都按照1990年價格進行折算,以實現可比性;(2)對樣本個體時間序列中個別遺漏數據、明顯畸高或畸低的數據,推斷其出現統計工作失誤,以該樣本點前后年份數據的平均值代替,或以之前幾年的平均增速推斷;(3)如果樣本點的某一變量出現連續2年以上的明顯異常值或缺漏值,則刪除該年份觀察值;(4)以普通箱形圖——以“75%分位數+1.5倍4分位間距”為箱形圖上側內籬笆,以“25%分位數-1.5倍4分位間距”為箱形圖下側內籬笆——找出離群值并刪除。

圖1 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投資強度、就業密度變化趨勢Fig.1 The change trend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investment intensity and employment density
觀察歷年樣本均值,可以發現產出率和投資強度呈現逐年上升態勢,而就業密度則呈總體下降態勢(圖1)。直觀顯示,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對產出率存在積極貢獻,而就業密度可能存在負的影響,就業密度的下降態勢折射出持續的技術進步等全要素生產率的存在,后者可能是影響工業用地產出率的重要因素。
為了回歸分析的需要,對地級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投資強度和就業密度數據取自然對數,基本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整體上看,各變量均值和中位數很接近,偏度接近0,峰度接近3,近似正態分布。

表1 基本統計量Tab.1 Basic statistics
4 參數估計、模型檢驗
4.1 混合回歸還是個體效應:F檢驗和LSDV檢驗
首先對模型(式(1))等式兩邊取對數,通過stata 13按固定效應模型(FE)估計且不采用聚類穩健標準誤,進行F檢驗,發現F(92,1170) = 16.93,p值為 0.0000,強烈拒絕不存在個體效應的原假設,應允許各樣本個體擁有自己的截距項。對模型(式(1))增加個體特征并將其視為參數,對每個樣本個體定義一個虛擬變量,然后把92個個體虛擬變量納入回歸方程中(未包括的第一個個體虛擬變量為共同截距項),取自然對數后得到:

式(4)中,個體虛擬變量d2i= 1,如果i = 2;d2i= 0,如果i≠2;以此類推。采用最小二乘虛擬變量(LSDV)法回歸式(式(4)),發現絕大多數個體的虛擬變量都很顯著,所以拒絕“所有個體虛擬變量都為0”的原假設,認為存在個體效應。
4.2 隨機效應還是固定效應:豪斯曼檢驗和過度識別檢驗
根據反映個體異質性的遺漏變量ui與其他解釋變量是否相關,個體效應的形態可分為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有必要通過檢驗在二者之中做出選擇。通過豪斯曼檢驗(Hausman test),得到χ2(3)等于21.36,p值為0.0001,故拒絕原假設“H0:ui與xit、zi不相關”,宜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而非隨機效應模型。鑒于豪斯曼檢驗不采用穩健標準誤,隱含一個比較強烈的假設——ui與εit都是獨立同分布的,而且通過估計發現聚類穩健標準誤和普通標準誤存在較大差異,豪斯曼檢驗效果值得質疑,有必要開展進一步檢驗。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相比,多了“個體異質性ui與解釋變量xit、zi不相關”的約束條件,可以視為過度識別條件,所以用xtoverid命令進行過度識別檢驗(overidentification test),得到統χ2(2)計量為12.437,p值為0.0020,拒絕隨機效應,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
4.3 雙向固定效應估計和檢驗
固定效應包括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可解決不隨時間而變但因個體而異的遺漏變量問題;那些不隨個體改變但因時間而異的遺漏變量問題則需要引入時間固定效應予以解決。上述LSDV檢驗表明,個體固定效應確實存在,但工業用地就業密度對產出率的彈性系數為-0.513,標志著就業密度對產出率存在負的邊際效應,這與生產理論和實踐相悖。所以,有必要同時考慮時間固定效應的影響,估計雙向固定效應(Tow-way FE)模型(式(3))得到的結果見表2。

表2 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估計Tab.2 Regression of tow-way fixed effect model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表2顯示,多數年份虛擬變量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少數年份不顯著,對時間虛擬變量系數進行Wald檢驗得到統計量F(16,92) = 41.69,p值為0.0000,強烈拒絕不存在時間效應的原假設。同時,工業用地就業密度對產出率的彈性系數估計為0.181,不再呈現負數,具有了與生產理論和實踐相吻合的經濟意義: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就業密度每提高1%,可使產出率提高0.181%。而且,雙向固定效應估計的擬合優度達到0.842,明顯高于FE估計的擬合優度0.594。此外,聯合檢驗表明工業用地投資強度的和就業密度彈性系數之和小于1,印證了上文的系數約束假設,反映了其他條件不變前提下單位面積工業用地上資本和勞動要素邊際報酬遞減的規律;這種系數約束特征也可以從它們的95%置信區間[0.411,0.670]和[0.047,0.316]直觀發現。綜上,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式(3))及其估計結果是可信的。
這里得到的工業用地產出率的投資強度彈性系數為0.541,高于林堅和張沛的0.282、張琳和王亞輝的0.346;就業密度彈性系數為0.181,介于林堅和張沛[23]的0.346與張琳和王亞輝[5]的0.142之間。這種區別可能是由于數據不同形成的,林堅和張沛使用的是國家級開發區數據,筆者分析的是地級城市數據,一般而言,地級城市工業區比國家級開發區的資本更稀缺、投資強度更低,會推高投資強度彈性系數;地級城市工業職工比國家級開發區職工平均勞動素質存在一定差距,會拉低就業密度彈性系數。因此,這種彈性系數的差別有助于印證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式(3))及其估計結果的可信度。
4.4 分區域聚類回歸分析
利用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數據分別對模型(式(3))做回歸,與全國樣本數據回歸結果做對照,可以進一步檢驗Two-way FE估計的穩健性,其回歸結果見表3。

表3 分區域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影響因素回歸分析與對照Tab.3 Regression and comparison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factors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表3顯示,區域聚類回歸分析可以得到統計性質良好的參數,且能夠通過經濟意義檢驗,進一步表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式(3))的回歸結果是可信的。
5 投資強度、就業密度、TFP對地級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的貢獻及區域比較
5.1 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的衡量
采用雙向LSDV法,對個體特征和時間固定效應都定義虛擬變量,采用穩健標準誤,回歸模型(式(3))得到與Two-way FE相同的回歸參數和高達0.9317的擬合優度,并可同時查看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對統計顯著的個體虛擬變量的參數與常數項相加后取均值,發現城市個體固定效應因地區不同而相異,東部以3.41居高,西部以2.92居末,個體固定效應的全國平均值為3.071;同時發現,時間固定效應逐年遞增,其平均值為4.521。
5.2 地級城市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和就業密度對產出率的邊際貢獻
將上述個體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和殘差對工業用地產出率的影響合并記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對數(lnA),并將上述回歸參數代入模型(式(3)),經適當變形可得:

進行樣本平均,利用式(5)計算不同年份的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和就業密度對產出率的邊際貢獻(表4),發現投資強度和就業密度對工業用地產出率的邊際貢獻逐年遞增。在1998年地級城市工業用地投資強度每增加1萬元,可使產出率增加0.828萬元,到2014年則可增加1.835萬元;在1998年就業密度每增加1個單位(104人/km2),可使產出率增加1.315億元,到2014年則可增加8.662億元。

表4 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和就業密度對產出率的邊際貢獻Tab.4 Marginal productivity contribu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investment intensity and employment density
5.3 分區域地級城市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就業密度的邊際貢獻和全要素生產率
對各區域的比較可以發現,中部和西部地區地級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投資強度和就業密度在絕大多數年份都低于東部地區(圖2)。其中,產出率和投資強度低于東部地區通常可理解為“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更低、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更高”,這意味著更高的就業密度。但是,就業密度的數據比較結果恰恰與此相悖,表明中西部城市工業用地集約利用度和東部相比存在較大的差距。
用分區域聚類回歸所得參數替代式(5)的參數,可計算中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地級城市工業用地的全要素生產率以及投資強度、就業密度的邊際貢獻(表5)。為增強現勢性而分析2010—2014年均值①若考察1998—2014年均值,可以得到類似結果。,發現全要素生產率呈現“東部>中部>西部”態勢,吻合中國工業總體布局:東部以技術密集型為主,中部由于老工業基地較多而以資本密集型為主,西部則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表5顯示西部投資強度邊際貢獻較高,可能的解釋是西部用地粗放,投資強度較低,資本稀缺度較高;西部就業密度邊際貢獻最低,可能的解釋是西部勞動密集型產業工人人力資本較低。中部投資強度邊際貢獻最低,可能的解釋是中部布局了較多技術進步慢的資本密集型工業;中部就業密度邊際貢獻最高,可能的解釋是用地較粗放,就業密度低。東部地區投資強度邊際貢獻最高,可能的解釋是東部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全要素生產率最高;東部就業密度邊際貢獻低于中部,可能的解釋是東部工業用地集約度高,就業密度高。

圖2 三大區域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投資強度、就業密度變化趨勢Fig.2 The change trend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investment intensity and employment density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
5.4 地級城市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就業密度和TFP對產出率提升的貢獻率
工業用地產出率的直接影響因素分為投資強度、就業密度和全要素生產率(TFP),其中全要素生產率包括技術進步和殘差的影響,技術進步又反映在個體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之中。借鑒索洛余值法計算全要素生產率(A)的增長率(),存在:

計算式(6)可得1999年以來中國地級城市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就業密度和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率提升的貢獻率。經計算,地級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年均增速約為8.7%,投資強度年均增速為3.4%強,就業密度年均下降近3.4%,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約為7.46%。謝花林、王偉等學者[11]發現中國主要經濟區城市工業用地TFP在2002—2012年間年均增長8%,筆者的發現與其接近,實現了相互印證。納入彈性系數因素計算發現,投資強度年均增速帶動工業用地產出率年均增長1.86%,貢獻率為21.3%;同樣方法計算發現就業密度和全要素生產率對1998年來城市工業用地產出率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7%和85.7%。
6 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對產出率的提升作用與人們的預期存在較大的差距,地級城市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對產出率增長的貢獻率只有21.3%。表4顯示,由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積極作用和較慢的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增速的影響,工業用地投資強度的邊際貢獻逐年遞增,從2014年數據來看,單位工業用地的固定資產每增加1萬元,可使產出率增加1.84萬元。所以,當前通過遏制工業用地粗放利用、提高工業用地容積率、嚴格執行工業項目用地投資強度標準、鼓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等政策措施適度提高工業用地投資強度是必要的,分區域比較分析則表明對于西部地區尤其需要加強實施工業用地投資強度促進政策。

表5 分區域地級城市工業用地投資強度、就業密度的邊際貢獻和全要素生產率Tab.5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the prefecture level urban industrial land investment intensity and employment densit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城市工業用地就業密度逐步下降是大勢所趨,但存在非正常下降因素,應予以遏制。城市工業用地就業密度對產出率的彈性系數為0.181,但由于工業用地就業密度呈現逐漸下降態勢,1999年來對產出率提升的貢獻率為-7%。由于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勞動者素質提升等因素影響,長期來看,就業密度必然呈現下降態勢。不過,一些非正常因素也可能對就業密度下降做出了貢獻,比如工業從業人員待遇過低、生活保障不足、工業用地供地冗余等。5.2節表明,2014年新增1位工業從業人員的邊際貢獻是8.66萬元,與工業從業人員(含管理層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年薪均值相近,符合勞動報酬與其邊際貢獻相等的原則。這表明目前遏制工業就業密度非正常下降的主要著力點不宜放在工資水平調整上。鑒于目前工業園“孤島”[39]和粗放用地并存的現象,應注重強化各工業園區員工的生活保障,并應采取有力措施遏制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工業園區、工業新城建設中出現的盲目鋪大攤子行為。
全要素生產率是推進城市工業用地產出效率提升的首要因素,顯示工業經濟發展方式呈現了積極的轉變,應加強其作用以加速這種轉變,在工業用地配置和集約性評價中高度重視全要素生產率相關指標,并賦予足夠高的權重。TFP包括個體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和殘差的影響,其中,個體固定效應包括區位、自然環境、歷史人文環境等變量,時間固定效應包括技術進步、宏觀經濟變動、產業政策影響等變量。分析顯示,無論在統計意義上還是經濟意義上,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對工業用地產出效率都存在顯著影響。所以,一方面要積極推進技術進步,還要注重改善營商環境、健全基礎設施,要縮小中西部與東部地區在這些方面的差距,并要加快中部地區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加速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鑒于數據可得性,本文沒有把地均人力資本從就業密度中剝離出來,沒有在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之外探討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有待進一步完善。
(References):
[1] 習近平. 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A]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 .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589 - 607.
[2] 李克強. 凝聚共識、形成合力推進城鎮化更穩更好發展[A]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 .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608 - 622.
[3] 曹建海. 中國城市土地高效利用研究[M] . 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102 - 104.
[4] 鄭振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創新存量工業用地管理探析[J] . 中國土地,2016,(8):15 - 17.
[5] 張琳,王亞輝. 微觀企業視角下工業用地產出效率的影響因素研究[J] . 華東經濟管理,2014,28(9):43 - 48.
[6] 舒幫榮,劉友兆,王家富,等. 欠發達地區經濟開發區工業用地低效利用問題初探[J] . 開發研究,2009,(2):80 - 83.
[7] 王成新,劉洪顏,史佳璐,等. 山東省省級以上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研究[J]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24(6):128 -135.
[8] 陳偉,彭建超,吳群. 城市工業用地利用損失與效率測度[J]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1):15 - 22.
[9] Erik Louw, Erwin van der Krabben, Hans van Amsterdam. The Spatial Productivity of Industrial Land[J] . Regional Studies,2012,46(1):137 - 147.
[10] 馮長春,劉思君,李榮威. 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工業用地效率評價[J] . 現代城市研究,2014,(4):45 - 49.
[11] 謝花林,王偉,姚冠榮,等. 中國主要經濟區城市工業用地效率的時空差異和收斂性分析[J] . 地理學報,2015,70(8):1327 -1338.
[12] 龍開勝,陳利根,占小林. 不同利用類型土地投入產出效率的比較分析[J]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18(5):174 - 178.
[13] 王希睿,許實,吳群,等. 江蘇省建設用地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時空差異分析[J] . 中國土地科學,2015, 29(5):77 - 83.
[14] 張琳,王亞輝,李影. 全要素生產率視角下的城市工業用地生產效率研究[J] . 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6(1):57 - 62.
[15] Tu Fan, Yu Xiaofen, Ruan Jianqing. 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und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Evidence from Hangzhou, China[J] . Habitat International,2014,43(7):1 - 10.
[16] 趙愛棟,馬賢磊,曲福田. 市場化改革能提高中國工業用地利用效率嗎?[J]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26(3):118 - 126.
[17] Du J. Urban land market and land-use changes in post-reform Chin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J] .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4,124:118 - 128.
[18] Gao By, Li Wd. State land policy, land markets and geographies of manufacturing: The case of Beijing,China[J] . Land Use Policy,2014,36:1 - 12.
[19] 郭貫成,溫其玉. 環境約束下工業用地生產效率研究[J]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24(6):121 - 126.
[20] 陳逸,黃賢金,陳志剛,等. 城市化進程中的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研究[J] . 中國土地科學,2008,22(6):11 - 16.
[21] 羅能生,彭郁. 中國城市工業用地利用效率時空差異及地方政府競爭影響[J] . 中國土地科學,2016,30(5):62 - 71.
[22] 孟媛,張鳳榮,趙婷婷,等. 北京市順義區制造業用地集約度評價及影響因素分析[J] . 中國土地科學,2011,25(2):11 - 17.
[23] 林堅,張沛,劉詩毅,等. 基于生產函數的工業用地級差收益研究[J] . 城市發展研究,2010,17(6):80 - 85.
[24] Robert M. Solow.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 .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312 - 320.
[25] John W. Kendrick, Ryuzo Sato. Factor prices,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J]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53(5):974 - 1003.
[26] 周方. 科技進步與“增長函數”[J] .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9,(10):32 - 50.
[27] 譚崇臺. 發展經濟學[M] . 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1:113.
[28] 林榮茂,劉學敏. 中國工業用地利用的數理分析與實證研究[J] . 財經研究,2008,34(7):51 - 62.
[29] 楊楊,吳次芳,韋仕川,等. 土地資源對中國經濟的“增長阻尼”研究——基于改進的二級CES生產函數[J] . 中國土地科學,2010,24(5):19 - 25.
[30] 王克強,熊振興,高魏. 工業用地使用權交易方式與開發區企業土地要素產出彈性研究[J] . 中國土地科學,2013,27(8):4 - 9.
[31] 李谷成. 資本深化、人地比例與中國農業生產率增長——一個生產函數分析框架[J] . 中國農村經濟,2015,(1):14 - 31.
[32] Antonio Ciccone, Robert E. Hall. 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J]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1):54 - 71.
[33] 黃大全,洪麗璇,梁進社. 福建省工業用地效率分析與集約利用評價[J] . 地理學報,2009,64(4):479 - 486.
[34] 郭貫成,熊強. 城市工業用地效率區域差異及影響因素研究[J] . 中國土地科學,2014,28(4):45 - 52.
[35] 畢寶德,柴強,李鈴,等. 土地經濟學(第六版)[M]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8.
[36] 李子奈,葉阿忠. 高級應用計量經濟學[M] .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10.
[37] 靳云匯,金賽男.高級計量經濟學(下冊)[M]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79.
[38] 陳強.高級計量經濟學及Stata應用(第二版)[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251.
[39] 王慧. 開發區與城市相互關系的內在機理及空間效應[J] . 城市規劃,2003,27(3):20 - 25.
(本文責編:陳美景)
The Impact Factors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and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XU Ming-qiang1,2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China; 2. 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 of Applied Economics,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China)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find out the impact factors, impact degre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and to come up with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to impel the intensive use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Based on the relatively extensive use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and the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regarding the impact factors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is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land function theory and the two-way fixed effects panel data model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is established, which takes the urban industrial land capital intensity and its employment density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ata of 93 prefecture-level cities since 1998 shows that the coefficient ofelasticity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capital intensity and the employment density towards its productivity are 0.541、0.181 respectively. Beside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towards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se three factors to the growth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since 1998 was 21.3% and -7% and 85.7% respectively. And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rates in terms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present regional differences due to the intensity of industrial land, industrial types and labor quality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 In conclusion, the extensive use of land is supposed to be curbed especi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industrial zon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 and industrial investment should be promoted in order to increase capital intensity and employment density; indicators that reflec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allo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the gap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and other areas should be narrowed.
land u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wo-way fixed effects; industrial land productivity; capital intensity; employment density
F293.2
A
1001-8158(2016)12-0071-12
10.11994/zgtdkx.20161217.013049
2016-08-14;
2016-10-31
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產城融合關鍵因素和影響機制研究”(15YJA790074);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基于中外工業園經驗數據的產城融合實現機制實證研究”(2015M572487)。
許明強(1975-),男,四川安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城鎮化與工業化。E-mail: thinker1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