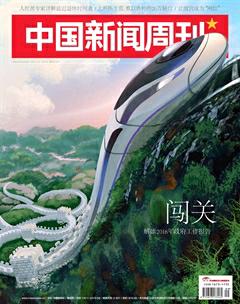民企“走出去”,是供給側改革落地的極好機會
徐天
對于供給側改革,國家提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
補短板”等五大任務,前面三個都是“去”,最后一個是“補”,現在的短板
對企業就意味著巨大的機遇,也就是企業發展的方向
2016年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政協委員駐地,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工商聯和民建聯組討論。
駐地會議室內,回形的桌子旁坐滿了代表。三胞集團董事長袁亞非坐在習近平的正對面,他在手掌大小的筆記本上寫滿了三四頁的關鍵詞,以至于第二天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他仍然能復述出習近平的講話內容。
“習總書記針對我們民營企業作了講話,給我們定了心。他說,國家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他希望民營企業能參與到這一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來,包括一帶一路,包括長江經濟帶,國家會加大政策的落地。他說,這30年來,中國經濟經常被人唱空,但是每一次唱空都沒有讓它實現。現在是中國經濟的轉型時期,民營企業應該大有作為。”
“國家制度每兩年就應該重新審視一遍”
中國新聞周刊:這次你提交了幾個提案,都是什么內容?
袁亞非:我提交了四個提案,分別是大力發展精準醫療產業、推進健康服務業供給側改革;進一步完善《重組管理辦法》、促進上市公司長遠健康發展;還有一個是希望國家能大力支持民營企業走出去;另外這幾天在會上,我還形成了一個希望國家進一步修改完善《商標法》的提案,得到了很多委員的聯名。
中國新聞周刊:精準醫療的提法最近常常見諸報端,尤其在科技界、醫療衛生界。作為企業家,你為何提出這個提案?
袁亞非:精準醫療,實際就是加強民生的投入。我認為,這是“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投資渠道和經濟拉動的載體。
我國的基礎醫療基本完整。但我們研究發現,有些事情靠基礎醫療解決不了,比如跟基因有關的病癥。以癌癥舉例,目前并沒有一種有普遍性成效的藥物出現。每個人的基因不一樣,病理、治療手段也就不一樣,所以,精準醫療就是根據個體的不同“對癥下藥”。
精準醫療的基礎,是人類的基因圖譜。研究越多人的基因,才能發現越多的共性和演變規律。我覺得人類在未來的十年能夠攻克非常多的重大疾病,但都要靠精準醫療。
客觀講,精準醫療非常貴,全程下來要50萬到80萬美金。但如果這種醫療方法能夠發展起來,隨著規律的顯現,將來能形成方法論,精準醫療的價格就會下來了。
2015年2月,習總書記批示科技部和國家衛計委,要求國家成立精準醫療戰略專家組。這說明中國的精準醫療即將發展。而我們公司又將擁有全球最大的臍帶血庫,這就可以下功夫去研究基因圖譜,找尋演變規律。
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來說,民營資本進入醫療行業,在準入方面是否還有很多的限制?
袁亞非:國務院有相關政策,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健康服務領域,已經放開了,沒有過多的限制。
不過,我認為,有些針對國企的限制,不能來限制民企。比如說,非營利醫院進口醫療設備需要審批,因為這是國家的資金,我能理解。但是民營醫院為什么也不能進口醫療設備呢?在這些問題上,我覺得有關部門還需要解放思想,繼續放開。
中國新聞周刊:談到限制,你的另一個提案,好像也是呼吁國家要放開相關的政策。
袁亞非:是的,是針對上市公司。
最近10年來,我國GDP已經從18萬億增長到了68萬億,A股總市值從5萬億增長到了近60萬億,經濟總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我們還有很多政策沒有跟上經濟形勢的發展。
證監會有關上市公司的一個制度規定,如果這個上市公司發生第一次實際控制人變更,今后再做資產重組,放入的資產一旦超過第一次變更前一年的資產總額,就算借殼上市。
但實際情況是,十年前中國的經濟體量是多大,現在是多大?十年前,很多公司的資產就幾個億,如果那時發生了實際控制人變更,現在隨便往里放點優質資產,就是十個億、八個億,按照目前的規定,那就都算借殼上市。這種制度顯然沒有跟上時代的發展,我覺得應該改。
另外,我認為,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國家的制度每兩年就應該重新審視一遍。
希望國家能為民企“走出去”提供“保護傘”
中國新聞周刊:這兩年你接受采訪時,一直呼吁民營企業和國企的話語權應平等,你提到一個詞,叫“同股同權”。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有什么進展嗎?
袁亞非:客觀地講,進展不大,但我們對2016年都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們認為,國家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落地落得不太好,習總書記也談到了這個問題。我希望今年能有所改變。
中國新聞周刊:你去年的提案也有民營企業“走出去”,連續兩年提這個提案,是否有什么時機的考慮?
袁亞非:是的,“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為民營企業“走出去”指明了方向。中國政府牽頭成立的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在資金上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便利。同時,“一帶一路”的倡議獲得了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結構與自然環境俱佳,即將迎來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中國民營企業需要把握這個機遇,參與到這一建設進程中。
2012年,國家發改委會同多個部門,出臺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開展境外投資的實施意見》,從加強宏觀指導、完善政策支持、簡化和規范境外投資管理等方面給予了鼓勵和引導。
相對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由于不存在國家背景和政治因素,在對外投資過程中更容易被投資國接受。比如機械、化工、鋼鐵、汽車、水泥、基建等海外需求很大的產業領域,很多民營企業表現優秀并已經先行在境外取得了良好成績。
另外,民營企業經營機制靈活,對市場反應敏感,適應國際市場的能力也比較強。
現在,國家產能過剩,強調供給側改革,通過改革提高產品的質量。國外的品牌能活幾百年,它的背后總有自己的邏輯和文化背景。我們走出去,引進來,可以把這些東西為我們所用。我認為,這是供給側改革落地的極好機會。
中國新聞周刊:你提到了供給側改革。你覺得民營企業在這場改革中,會有什么機遇和挑戰?
袁亞非: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是機遇大于挑戰。供給側改革可以倒逼傳統民營企業順應改革趨勢,發揮更多主動性和創新性,進行轉型升級,增加供給的活力和質量,否則就會在這一輪改革中被淘汰。
我覺得,企業發展的觀念首先要改變,發展之道,觀念先行。
其次,要從國家的層面考慮企業發展方向。對于供給側改革,國家提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任務,前面三個都是“去”,最后一個是“補”,也就是我們現在還欠缺的。從國家層面去看問題,現在的短板對企業就意味著巨大的機遇,也就是企業發展的方向。
再次,如同我上一個問題最后回答的,提升供給的質量,除了自身創新之外,也可以考慮“走出去”、引進來,這是一條捷徑。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一種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所以海淘、代購、出國旅游購物越來越多。中國消費者不是覺得海外的東西好嗎?那我們就把這些好東西引進來,既促進了企業的轉型升級,也提高了供給的質量。
世界上最好、最先進的東西就是我們未來的方向,那我們就把未來的東西買過來,然后借此來建立自己的未來。這其實就是把國外優秀的產品和先進的技術引進國內,在供給側進行改革,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
中國新聞周刊:你今年在提案中特別強調,民營企業應該抱團“走出去”,這是出于什么考慮?
袁亞非:在國外發展,靠單個的民營企業是不夠的,我說的不僅僅是經濟實力,還有見識、經驗、教訓、人才等各方面。大家抱團“走出去”,抗風險能力增強,這樣也會贏得國家支持。
另一方面,民營企業抱團“走出去”,更有利于打造區域品牌,比如蘇商企業抱團“走出去”,就容易在海外打響“蘇商”這個群體的品牌。
此外,民間資金相對分散,如果抱團,可將分散在民間的大量資金轉化為資本,統籌運營,對接海外優勢產業,提高“走出去”成功的可能性。
中國新聞周刊:剛才你提到了“國家支持”。你希望國家能提供什么樣的支持?
袁亞非:我們希望政府能在這個過程中提供一些“保護傘”。比如說,需要國家相關的投資促進機構,帶領民營企業尋找商機;也需要非常細致的國別投資操作指南、行業的投資指南,讓民營企業了解更多東道國的信息;還需要更多的教育培訓機會,讓民營企業能利用工具,規避風險。
(實習生國佳佳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