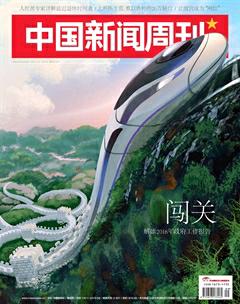供給側改革離不開做強傳統產業
張杰
中國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應該落在扎實構筑精益制造生態體系以及相關核心支撐條件方面,切不可犯冒進主義,盲目追求智能制造和互聯網制造
當前,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的不少地方政府對于如何定位經濟增長動力機制的認識,存在兩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不少地方政府忽略了傳統產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忽略了中國仍然需要通過傳統產業特別是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在保證中國制造業出口優勢、維持制造業全球競爭力方面的極端重要性。相反,片面夸大新興戰略產業對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這在不少地方政府制定的十三五規劃以及相關產業規劃中可見一斑。
第二個誤區是過度強調服務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忽略了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部門和第三產業之間的密切聯動性及相互支撐作用。對于中國大多數地區而言,沒有強大的傳統制造業,沒有依據條件變化而持續轉型升級的傳統制造業,無論是第三產業中的生活服務業還是生產服務業,均無法獲得可持續增長的基礎支撐條件。
在這些認知誤區的引導之下,中國不少地方政府,在貫徹和落實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方向方面,以及在應對當前傳統產業特別是傳統制造業所面臨發展困局的政策思路以及制定解困措施方面,在不同層面均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
具體表現在: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帶著短視的眼光和路徑依賴式的既有發展思路,來看待傳統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完全不顧地方既有產業發展基礎和自身稟賦條件,一窩蜂地將發展重點都放在搶奪有限的新興戰略產業方面。大量運用有限的政府財政補貼資金,依靠稅收、土地等直線思維式的簡單優惠政策,不切實際地一味要做大做強新興戰略產業,這些違背市場公平競爭原則的招商引資優惠政策模式以及對大項目的盲目偏好與扶持,既可能對既有傳統產業造成了擠出效應,又有可能造成新一輪的新興戰略產業及高新技術產業泡沫化現象。
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對制約中國傳統產業的關鍵短板和發力方向,存在普遍的認知和政策操作偏差。當前制約中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突出短板是中國并未形成一個精益制造的生態體系,突出表現為“小而散”的制造業企業在產品質量以及產品設計的基礎能力普遍不足,關鍵零配件和高端生產設備的創新研發能力嚴重缺失,“工匠精神”和專業化精神嚴重喪失。
對于中國多數地區的發展邏輯而言,不可能超越工業2.0和3.0階段,而依靠所謂的“彎道超車”技巧一步跨越到工業4.0階段。中國當前的核心問題不僅僅是要全面發展工業4.0,更重要的是要彌補工業3.0和2.0的短板。
因此,中國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應該落在扎實構筑精益制造生態體系以及相關核心支撐條件方面,切不可犯冒進主義,盲目追求智能制造和互聯網制造。
核心任務是做強傳統產業
依據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約束條件來看,要充分認識到,強大的傳統產業是建立優秀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戰略產業的基礎和前提。傳統制造業以及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然也必將是維持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基礎性力量。
從外部環境來看,全球貿易投資一體化正在發生的區域性碎片化,由此可能引發全球貿易的大停滯以及全球化貿易投資體系面臨的根本性重構,這對中國做強傳統產業,既造成了巨大的挑戰,也帶來了關鍵的機遇期。
當前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多種因素的變化導致中國多數傳統優勢產業的既有優勢發生了問題,但全球對傳統產品的世界需求仍然存在,這決定了中國傳統產業在全球市場仍然具有生存和發展空間,決定了經過轉型升級改造后的中國傳統產業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是經濟增長支撐力量的客觀事實。
在繼續深入推進對外開放的戰略背景下,如果面對發達國家的殘酷競爭,中國既沒有獲得足夠的新興戰略產業的發展空間,同時,面對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又守不住傳統制造業的既有全球市場份額,把握不了傳統制造業新型化的全球發展機會,過早過快地喪失了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發展機遇期,這可能才是中國今后經濟發展過程中會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我們尤為需要清醒認識到的是,中國新興戰略產業的發展必將面臨來自發達國家殘酷的競爭和擠壓,而傳統產業所面對的競爭壓力相對仍有回旋余地,這為中國傳統產業的“脫胎換骨”提供了難得的外部機遇。
從國內環境來看,中國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亮點是,中國的消費需求結構正發生由低端需求向中高端升級的顯著變化現象,這對中國傳統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立足產品質量提升、產品設計多樣化等高質量投資活動,創造了極為重要的本土市場需求發展機會。
然而,中國制造業在產品質量、產品設計以及品牌構建維護等方面所體現的基本精益制造能力,卻嚴重滯后于中國消費者需求結構的變化。造成的后果是中國國內消費者將迅速增長的巨大規模的高端需求,轉移到對發達國家產品的需求方面,這就切斷了中國情景下消費者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內在傳導機制,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造成重大挑戰。
反過來思考,如果中國制造業企業能夠通過迅速提升產品質量和產品設計等基礎能力,扎實做好精益制造生態體系,充分利用好中國國內消費者迅速增長且規模巨大的高端需求,這也就會為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最為根本的支撐力量。
傳統產業不再“傳統”,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過程中孕育著大量的創新創業機會,既是中國高質量投資增長點的方向所在,也是落實創新驅動發展國家戰略的基礎所在。
在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的情形下,傳統產業的生產、組織、管理方式已經不再傳統,孕育著大量的創新創業機會和高質量投資機會。轉型升級后的傳統產業將不再是過剩產業或過時產業,仍然是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最具有出口競爭力的支撐產業。
客觀來看,當前中國新興戰略產業及高新技術產業對中國經濟增長還未形成足夠的支撐力,2015年其對GDP增速的貢獻也只有15%~20%,因此,當前的客觀現實就是小馬拉不了大車。
相反,中國制造業不僅僅在產品質量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在多數傳統制造業的關鍵材料、核心零配件以及先進生產設備等方面的自主研發與生產能力嚴重不足。當前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增加值率較低,僅相當于美國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國的5.56% 。依據波士頓咨詢集團的2015年最新報告,目前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與美國的差距縮小為只有4% 。
這種情形下,中國傳統制造業在產品質量、關鍵設備研發生產、生產效率提升、綜合成本降低等方面,蘊含著巨大的自主創新以及效率提升型的投資機會,這才是驅動今后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投資方向和改革重點方向所在。
工匠精神和專業化精神
中國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還面臨一系列突出的制約性因素,需要將之納入到供給側改革的綜合配套范疇之內。
就如何破除當前束縛中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突出制約性因素而言,當下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應該落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將做強中國的傳統產業上升到供給側改革的國家戰略層面。對于中國在新常態下今后經濟發展的支撐力量來看,要愈加清晰地認識到中國傳統產業特別是傳統制造業的基礎性作用。明確推進中國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做強中國傳統產業,是中國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供給側改革的核心任務。
要努力提升制造業產品質量和產品設計基礎能力,以及關鍵零配件和高端生產設備的創新研發能力,以“工匠精神”和專業化精神提升精益制造生態體系,推進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逐步提升為主要取向的供給側改革。要高度警惕中國的傳統產業丟了,而新興戰略產業又沒有發展起來的雙重風險,特別是要警惕日本印度全面經濟合作以及持續擴容的TPP,對中國傳統產業出口優勢和轉型升級的巨大沖擊。
第二,以短期政策來穩定中國傳統產業出口規模和長期改革來切實降低中國傳統產業不合理成本負擔的雙重視角,作為針對做強中國傳統產業的供給側改革的基準框架。
從短期來看,面對人民幣高估以及其他主要制造業大國貨幣大幅度貶值導致中國傳統產業出口競爭優勢急劇下滑的壓力,需要持續推進針對制造業企業的全面減稅以及出口退稅,大規模取消政府對實體經濟部門的不合理審批權力清單,加快出口便利化改革等措施,來守住中國傳統產業的全球份額和中國制造業的全球地位。
從長期來看,不要將中國傳統制造業出口優勢弱化的原因,全部歸結到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方面,而是要扎實依靠合理壓縮中國政府規模來降低稅收水平、打破壟斷來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徹底取消政府不合理權力來規范政府權力清單等手段,大幅度降低中國制造業面臨的高額交易成本和制度扭曲成本負擔,重塑中國傳統產業的成本優勢。
第三,加快構建與中國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以及自主創新能力提升需求相匹配的、金融風險可監管的新型系統性金融體系。
第四,加快構建與中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活動對各層次的創新研發人才以及技術工人的現實需求相切合的教育培訓體系。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