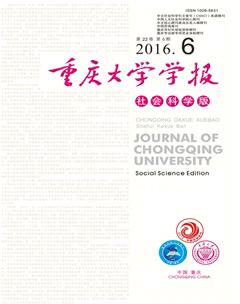油污損害防治的法經濟學解釋
摘要:在法經濟學領域中,“卡-梅框架”將侵權救濟規則抽象成財產規則、責任規則與不可讓渡規則三種類型。這一框架從分析法律規則的效果模式出發,以尋求“最有效率的權利保障”作為規則選擇的取舍標準。“卡-梅框架”對于油污損害防治理論和實踐的價值在于有助于重新審視相關法律規則的設置目的、適用場合及實踐效果。油污防治法律規范的修改與完善需要對克服油污損害的外部成本以及實現法律的效率價值給予更多關注。
關鍵詞:油污損害;責任規則;財產規則;不可讓渡規則;環境公益
中圖分類號:D91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16)06-0162-07
1973至2014年,中國沿海共發生船舶溢油事故3 200起,總溢油量約42 936噸。如2010年大連新港“7·16”油污染事件、2011年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2012年“11·22”青島輸油管道爆炸事件、2013年福建莆田“巴萊里”集裝箱船擱淺事故等都對生態環境造成了難以修復的創傷,而法律途徑尚未成為油污損害救濟的主導方式。可見,中國有關油污損害防治的法律規范還有很大的完善空間。為提升油污損害的救濟效率,筆者借鑒了法經濟學視域下“卡-梅框架”的邏輯思路,從分析救濟規則的法律效果出發,對現行油污損害的防治措施進行評價,并據此提出改進建議。
一、“卡-梅框架”之于油污損害防治的實踐價值
作為法經濟學領域的集大成者,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A.Posner, 1939-)將法經濟學定義為“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應用于法律體系的核心制度中”。目前,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廣泛運用于刑法、知識產權法、壟斷法等法律規范之中,尤其在侵權法領域的應用最為廣泛且富有成效[1]。在如何解決環境侵權這一問題上,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羅納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1910-2013年)撰寫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在無交易成本的情況下討論了排污權的初始分配問題[2]。
然而,環境侵權的產生往往涵蓋了各種成本。例如,石油開采屬于高風險行業,易發生地質勘探污染、事故污染、作業污染、設施處置污染。當大量原油進入海域,會改變海域的化學環境,對海洋生態系統以及周邊區域居民的生存環境和生計產生重大影響,而生態系統的恢復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這是因為油污損害油污損害往往涉及生態損害。理論界關于生態損害內涵的解釋主要有兩種。一是廣義上的生態損害,即包括生態環境本身的損害,也涵蓋以環境為媒介的財產損害、人身損害、精神損害等傳統私益損害。如王樹義教授在《俄羅斯生態法》、曹明德教授在《生態法新探》中對生態損害的定義;又如《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5條第1項關于“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定義,充分借鑒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條第4款的相關規定,可歸納為人身財產損害、自然資源損害、生態功能損害三個主要方面,包含了對私益和公益雙重侵害。二是狹義上的生態損害,指環境侵害行為所導致的自然環境本身的損害。參見陳紅梅《生態損害的私法救濟》(《中州學刊》2013年第1期)。不僅包括以生態環境為媒介所造成的民事主體的財產損失、人身傷害或精神損害等傳統私益損害(damage through the eco-system or environment),還包括生態環境本身的損害(damage to the eco-system or environment perse)[3]。因此,油污損害的防治至少需要考慮污染者與受害人確定私益損害賠償金的協商成本,污染行為對生態環境造成損害的外部性成本以及法院為維護環境公共利益所消耗的司法成本。
與“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關于“交易成本為零”的討論有所不同,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 和梅拉米德(Douglas Melamed)在其論文《財產規則、責任規則與不可讓渡性:大教堂的一幅景觀》(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中,將社會成本、法的實效法的實效一般是指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定法在社會生活中被執行、適用、遵守的實際情況,即法的實際有效性。參見李清偉、李瑞《法理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頁)。與外部性等議題作為規則選擇的考量因素,這些規則被抽象為財產規則(Property Rule)、責任規則(Liability Rule)和不可讓渡規則(Inalienable Rule)See,e. g. ,Saul Levmore,Unifying Remedies: Property Rules,Liability Rules,and Startling Rules,106 The Yale Law Journal 2149,2172(1997) .,被學界簡稱為“卡-梅框架”( CM Framework),成為法經濟學領域研究規則類型及效率比較的一個主導范式早在1997 年,《耶魯法學雜志》舉辦紀念“卡-梅框架”25周年學術研討的時候,這一框架就已經成為了公認的規則分類和效率選擇的基礎理論。。
基于“卡-梅框架”分析油污損害的防治問題,具有以下理論和實踐價值。第一,油污損害因侵犯了不特定多數人的環境公共利益而具有外部性外部性(externalities,或溢出效應)指企業或個人向市場之外的其他人所強加的成本或效益。參見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蕭琛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典藏版第42頁)。,使其區別于傳統私益侵權,對現行《侵權責任法》中某些侵權責任的成立要件構成挑戰。而“卡-梅框架”對外部性的估價主體以及控制方法等問題提出了頗有建設性的解決思路,使油污生態損害的防治越過了私法救濟的“藩籬”,并開始走向公法與私法協同共治的道路[4]。第二,傳統的環境侵權責任往往以法律規則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應當包含三個要素: 假設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參見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32頁)。的“行為模式”為分析起點,即關注于一個污染行為是否符合提起訴訟和損害賠償的法定要件,忽視了油污損害事件存在污染事實難以認定、賠償范圍過于籠統、環境修復不易執行等現實困境,使油污防治法律規范的實效性大打折扣。而“卡-梅框架”注重分析污染防治的“效果模式”,即以“最小的成本消耗(例如法院審理的司法成本、環境損害的估價成本等)實現權利保障”作為規則選擇的最終目的。這既更新了侵權救濟的思維方式,又彰顯了法律的效率價值[5]。
二、 “卡-梅框架”的規則類型
“卡-梅框架”討論的基本問題在于:當法授權利確定之后,運用何種規則維護權利能夠有效控制污染的外部性并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在油污損害這一場合下,所謂“法授權利”是指石油企業擁有合理開采、使用石油資源并進行合法排污的權利;同時,可能受到油污侵害的不特定多數人享有生活在良好、適宜的環境中的權利。如前文所述,“卡-梅框架”包含財產規則、責任規則、不可讓渡規則三種規則類型。其中,財產規則代表了最少的國家干預,即污染者和受害者可以平等自愿地協商污染損害賠償金的數額,且國家不會對金額的確定進行干預;責任規則下損害賠償的價值由法律規定的國家機關或社會組織給予客觀、中立的評價,這些機構一般是受理油污侵權案件的人民法院,也可以是以啟動或支持環境公益訴訟的環保組織或檢察機關;不可讓渡規則中行政權的干預程度最強。一則表現為禁止污染者與受害者私自確定損害賠償金的數額(即對污染損害實行國家定價),二則對污染防治和權利保障的具體方式作出事先規定[6]。
(一)財產規則
財產規則又稱財產法則,指除非征得權利人授權,否則法律禁止他人侵犯權利人對財產進行合法處分的自由。財產規則包含三個特點:一是財產所有人對自己的財產享有排他性權利;二是保障雙方當事人的締約自由;三是賠償要與損害對等[7]。例如,為防止油污損害的發生,目前許多國家采取了環境保護協議的管理模式。即污染源所在地自治團體、居民或其他組織,因石油設施的處置與運營可能對生態環境造成損害的,可以就有關損害賠償、污染排放及其他有關環境保護事項自愿與石油企業達成協議[8]。這種由污染排放者與可能遭受油污損害的群眾自愿簽訂的環保協議就是財產規則的實際運用。
(二)責任規則
責任規則是指對侵權行為給予司法救濟。在油污生態損害案件中,因涉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環境公共利益,損害賠償的確定需要由法院這一國家機關作出客觀的價值判斷[9]。例如,2015年7月26日,青島海事法院受理原告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訴被告康菲石油、中海油海上污染損害責任糾紛一案,成為中國首個由社會組織提起并獲得受理的海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此案緣起于2011年6月發生在蓬萊“19-3油田”的突發環境事故(下文簡稱渤海溢油事故)。該事故造成蓬萊“19-3油田”周邊870平方公里海水受到嚴重污染(超第四類海水水質標準),海洋浮游生物種類和多樣性明顯降低。據《2014年中國海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渤海溢油事故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依然存在。鑒于當時事故的處理繞過了司法渠道(以利害關系人之間協商簽訂賠償、補償協議的方式了結),為修復渤海的生態環境、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環保組織就此事再次起訴。
(三)不可讓渡規則
在不可讓渡規則下,法律禁止某些特定權利在私主體之間進行,即使是自愿的轉讓或處分,因為這些權利的流轉會給第三方或社會施加某種外部成本。不可讓渡規則通常適用于人身權(如禁止人口買賣)和政治權利(如禁止買賣選票),有時也適用于某種特殊的財產權(如禁止出售淫穢書刊、毒品、武器)[10]。同理,石油資源的利用事關國家能源安全與環境公共利益,為規制石油利用的負外部性,石油資源的勘探、開采權需要通過行政許可和環境影響評價方可獲得,并且需要交納探礦權價款、采礦權價款以及資源稅等。這些稅費的征收既體現了礦產資源的國家所有權,又可廣泛用于環境治理和生態補償,其目的在于通過環境稅收手段將石油利用產生的外部成本內化為企業的生產成本。此外,不可讓渡規則還表現為對于違法排污行為科處的行政處罰。例如,《環境保護法》第59條規定的“按日計罰” [11]、《海洋環境保護法》第85條規定的最高20萬元的行政罰款,都是國家基于公益和外部性之考慮,為預防污染事件的發生而進行的事前定價。
三、規則選擇的取舍標準
同樣是油污損害事件,為什么有的場合會適用財產規則和責任規則,而有些情況則適用不可讓渡規則呢?這是因為“卡-梅框架”為解決外部性問題并實現效率最優,在規則選擇的過程中將經濟效率、正義觀念、道德風險、司法成本等問題納入考量因素。
(1)財產規則:“賠償=損害”?如前文所述,財產規則適用于由污染排放者與可能遭受油污損害的不特定多數人自愿簽訂環保協議。那么,這種為預防油污事件發生的約定,是否符合財產規則所要求的賠償需等于損害呢?由于環保協議的簽訂是在油污損害發生之前,屬于風險評估的范疇,相較于業已發生的損害,對于賠償范圍和環境損失的判斷很難與實際情況相吻合。再上升到一般情況,要認定油污的實際損害,需要分析污染物質排放量、污染物回收量、污染物質品質及揮發量、污染面積、清污劑使用量和使用后果以及污染前、后海洋環境的質量狀況與后續海洋生態恢復狀況等多種因素。在油污損害領域運用財產規則時,進行協商的當事人一般為石油企業與受到石油污染侵害的個人,雙方在舉證能力、專門知識、資金實力等方面存在非對等性和局限性,加之油污的實際損害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既包括生態損害,又包括涉及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財產損害),使得運用財產規則防治油污侵權難以實現“賠償=損害”的目標。
(2)不可讓渡規則:克服道德風險與外部性?前文提到,不可讓渡規則一般體現為由國家預先設定權利流轉的條件,如石油礦業權的授予或對石油勘探、開采行為征收一定的資源稅費。試想,如果通過不可讓渡規則就能完全排除石油污染的隱患,那么為何還需要只針對事后救濟的責任規則呢?可見這種假設太過理想與絕對。一方面,石油企業雖然獲得了國家主管部門的行政許可,但其內部實際的生產運營情況是否符合清潔生產和安全操作的規程,很難被外部監管機構完全掌握,此時便容易引發道德風險。例如,渤海溢油事故的發生,就是由于注水井井口壓力監控系統制度不完善、井鉆井設計部門沒有執行環評報告書、井鉆遇高壓層后應急處置不當等諸多內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12]。另一方面,由于中國油氣資源稅費的改革進程還在不斷推進,在成品油定價機制、資源稅率的設計、資源稅費的計征方式等方面還有諸多尚待完善之處[13],使得現行的資源稅費制度沒有充分體現資源的環境價值和社會價值,沒有實現不可讓渡規則試圖將外部性內化為企業生產成本的初衷。
(3)責任規則:司法救濟可否實現效率?承前所述,由雙方當事人通過財產規則對油污損害進行估價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是低效的;不可讓渡規則主要適用于油污損害的事前防患,但無法圓滿地克服道德風險和外部性問題。就以上兩點而言,責任規則因表現為由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社會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一則克服了當事人雙方訴訟能力上的失衡;二則由人民法院通過司法程序對生態損害給予客觀、公正的認定,有利于維護環境公益,符合法律的效率價值和正義價值;三則能夠對因道德風險而引發的油污事故進行司法評價,通過由違法企業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方式內化油污侵權的外部成本[14]。據此,理論上責任規則在解決油污損害問題上能夠實現有效率的權利保障。
然而,現實中油污損害的救濟往往面臨較高的司法成本,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污染事實難以認定。例如渤海溢油事故發生后,對海洋環境容量、海洋生態服務功能、海洋沉積物、潮灘生物環、浮游植物等方面都可能產生影響。按照客觀規律,有些損失是事發后立即出現的,而有些損失是在過渡期間逐步產生的,還有些損失則僅是可能產生的。因為溢油擴散的最終范圍、環境容量的恢復狀況具有不確定性,需要隨時間推移加以判斷,這就增加了油污生態損害鑒定評估的難度,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什么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案率與審結率遠低于侵權糾紛的實際發生率。
第二,缺乏對損害賠償范圍的細致分類。目前,中國加入的有關油污損害責任的國際公約主要有1969年的《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中國于1980年1月30日加入)、修正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的《1992年議定書》(2000年1月5日對中國生效,以下稱“1969年CLC公約92議定書”)、1971年關于設立《國際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國際公約》(該公約只適用于香港特別行政區)。上述三個公約創建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嚴格但有限的責任。此外,中國還加入了1982 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及《燃油公約》。“1969年CLC公約92議定書”規定過去已經發生和將來需要產生的合理修復費用都屬于環境損害賠償范疇;作為補充,《燃油公約》適用于船舶燃料艙燃油溢出所造成的污染損害。然而,上述公約都將石油鉆井平臺的溢油污染排除在外[15]。在中國國內法層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2011年)第9條中,進一步發展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所規定的船舶油污損害賠償范圍,包括采取預防措施所發生的費用、因環境損害所引起的收入損失以及采取合理恢復措施的費用。通過梳理可以看出,無論是中國加入的國際公約還是國內法,油污生態損害賠償范圍和計算方法都缺乏具有實踐操作性的規定,影響了油污環境侵權的審理效率。
第三,有關油污生態損害的訴訟程序還在探索之中。以馬耳他籍“塔斯曼海”號一案2004年12月24日和12月30日,天津海事法院對天津市海洋局、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以及約1 500名天津漁民和養殖戶等10組訴訟原告分別訴被告英費尼特航運有限公司(INFINITY SHIPPING CO., LTD.)、倫敦汽船船東互保協會(THE LONDON STEAM-SHIP OWNERS’MUTUAL INSUR-ANCE ASSOCIATION LTD.)“塔斯曼海”輪(Tasman Sea)船舶碰撞油污損害賠償系列案進行審理。為例,天津海事法院當時總共需要審理10個系列案件天津海事法院審理的10個系列案件如下:(1)天津市海洋局提起海洋生態資源損失(除漁業資源)索賠;(2)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提起漁業資源損失索賠;(3)天津市塘沽區大沽地區129名漁民提起捕撈損失;(4)河北省灤南縣879名漁民提起捕撈損失及15名養殖戶提起養殖損失;(5)天津市塘沽區北塘地區239名漁民提起捕撈損失;(6)天津市漢沽區6名養殖戶提起灘涂貝類養殖損失;(7)天津市漢沽區50名漁民提起捕撈損失及1名養殖戶提起灘涂貝類養殖損失;(8)天津市漢沽區121名漁民提起捕撈損失及2名養殖戶提起灘涂貝類養殖損失;(9)天津市漢沽區48名漁民提起捕撈損失及11名養殖戶提起灘涂貝類養殖損失;(10)天津市漢沽區9名漁民提起捕撈損失及2名養殖戶提起灘涂貝類養殖損失。其中,天津市海洋局和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系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的規定,代表國家提起的海洋環境污染生態損失公益訴訟,其余各地區漁民和養殖戶提起的捕撈、養殖損失系普通民事訴訟(私益訴訟)。 。為節約司法資源,法院成立“公共庭”,由所有利害關系方參與,將污染事實作為公共焦點進行審理。當年這一審理方式的創新,可稱之為現在環境資源審判庭實行的“四審合一”之前身。雖然這種綜合刑事、民事和行政訴訟程序的審理模式在理論和實際操作中存在諸多不解之惑,但足以說明:為油污生態索賠為代表的環境公益訴訟設計專門的訴訟程序,不論是從提高審理效率考慮,還是作為訴訟法的理論發展,都已是大勢所趨。
四、“卡-梅框架”在油污損害防治中的應用策略
如前所述,“卡-梅框架”進行規則選擇的邏輯在于追求最有效率的權利保障。無論是財產規則、責任規則還是不可讓渡規則,對于油污損害的防治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能根據實際情況科學地進行規則選擇,就可以提升油污損害防治的實踐效果。
第一,充分發揮財產規則、不可讓渡規則的事前激勵作用。在重大油污生態損害事件中,有些污染者承擔賠償的能力非常有限,若生態損害的總社會成本高于污染者的全部資產,此時單獨依靠責任規則進行救濟顯然不能填補實際造成的損害。從污染者的角度出發,為了防止生態損害這種小概率事件的發生,如果需要投入的最低預防成本高于其總資產,一個理性的經濟人往往會選擇不采取預防措施。也就是說,僅依靠責任規則進行事后救濟,顯然不能形成對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所以,需要引入財產規則、不可讓渡規則對污染者進行事前激勵,即通過簽訂環保協議、提高資源稅負和環境行政管理效率等手段,將生態損害的外部成本內化為排污企業的生產成本。一來能夠激勵排污者進行清潔生產,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損害發生,減少社會整體損失;二來可以為將來可能發生的損害積累救濟基金。
第二,不可讓渡規則與責任規則要雙管齊下。適用不可讓渡規則對油污生態損害進行救濟,是在環保領域賦予政府優先權的表現,是“預防為主”原則的實際運用。因此,為提高油污生態損害的救濟效率,應當綜合運用不可讓渡規則和責任規則。具體而言,在油污損害的防患階段,因為風險發生的概率和生態損害的實際情況具有不特定性,可以通過不可讓渡規則(如環境影響評價、行政許可、行政處罰、征收資源稅費)鼓勵和監督石油企業進行安全生產;當油污損害業已發生時,應當使責任規則充當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舵手”,并由責任規則對生態損害作出的客觀估價,彌補現行行政處罰和資源稅費所忽視的資源價值和外部成本。
第三,規則選擇要遵循法律的公平價值和效率價值。具體而言,對于環境違法行為可優先適用制裁程度較低的救濟規則,使行為人承擔的法律責任與造成的生態損害保持均衡。比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復原狀、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都是責任規則的具體運用。如果能夠通過判決被告以履行環境修復這一行為方式填補生態損害,那么在對法律責任進行設計時,可以考慮不再并用行政罰款這一不可讓渡規則;或者在作出并處決定罰款時,罰款數額應當扣除履行恢復措施的行為成本。權衡的關鍵在于,在采取恢復措施之后,責任人能否將生態環境修復到損害發生之前的狀態和功能。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0條為例,其中就規定履行環境修復義務和承擔修復費用這兩種責任形式可以擇一適用。
五、“卡-梅框架”對于提升油污損害防治效率的現實啟示
在前文關于規則選擇的取舍標準中,可以看出現行油污損害的防治規則存在賠償范圍太抽象、資源稅費不合理、訴訟程序待改進的實踐困境。因此,為實現“卡-梅框架”關于“最有效率的權利保障”這一終極目標,應當逐步完善現行法律中有關油污損害救濟的專項規定,切實提高油污損害防治效率。
第一,拓寬油污損害的適用范圍。通過前文的梳理可以看出,現有法律中油污損害范圍僅限于船舶溢油或海洋生態損害,沒有專門調整陸上或近岸鉆井平臺溢油造成損害的規范。比較而言,美國《1990 年油污法》將油污損害的適用范圍從船舶擴展到設施發生溢油污染或溢油污染危險
美國《1990 年油污法》第1001條第( 9) 款中關于“設施”的定義為: “‘設施’是指用于一個或多個下列用途任何的結構或結構 (而不是船舶) 的組合: 勘探、鉆井、生產、儲存、處理、傳輸、處理或運輸石油。這一詞包括任何汽車、機車車輛或管道用于一個或多個這些目的。” ,成為審理墨西哥灣漏油案的法律依據[16],對中國處理以渤海溢油事故為代表的鉆井平臺溢油事件具有借鑒價值。
第二,區分人身、財產損害與自然資源損害。人身、財產損害是指對特定民事主體的私益損害;而自然資源與民法上物的一般屬性不同,其具有經濟性和公共性。石油污染對環境的損害最初表現為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即減損了自然資源能夠為人類提供的經濟價值[17]。自然資源作為生態系統的物質基礎和基本要素,若遭重大破壞可能形成對生態環境的整體損害[18],侵害不特定多數人的環境公共利益。油污生態損害救濟旨在恢復受損的生態服務功能,其中的關鍵在于將生態系統的抽象損害轉化為自然資源生態價值的減損德國學者Lahnstein博士認為,“生態損害指對自然的物質性損傷,具體而言,即為對土壤、水、空氣、氣候和景觀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動植物和他們間相互作用的損害。也就是對生態系統及其組成部分的人為的顯著損傷。參見Lahnstein Christian,“A Market-Based Analysis of Financial Insurance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Taking Special Account of Germany, Austria, Italy and Spain”, in Faure Michael ed., Deterrence,Insur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i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Future Develop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Wien, 2003, p.307. 。同時,將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物權化,通過計算財產損失對生態損害進行估價。也就是說,明確油污生態損害賠償范圍的重點在于實現生態服務功能的資源化與物權化[19]。
第三,明確損害賠償的計算方法。當前關于油污生態損害賠償范圍的相關規定過于原則,即便將環境損害列為賠償對象,也沒有切實可行的計算方法與之對應。雖然國家海洋局2007年發布的《海洋溢油生態損害評估技術導則》列明了海洋溢油生態總損失的計算公式:HY=HYZJ+HYH+HYP+HYM(式中:HY——溢油海洋生態總損失;HYZJ——溢油造成的直接海洋生態損失;HYH——生境修復費;HYP——受損生物種群恢復費;HYM——進行損害評估的調查評估費),然而,該技術導則在性質上屬于行業規范,能否比照《合同法》第61條之規定成為法院判決的依據還存在爭議,尚需法律賦予其強制執行力。 因此,筆者建議,在遵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將環境損害司法鑒定納入統一登記管理范圍的通知》(2016年)和司法部、環保部聯合印發的《關于規范環境損害司法鑒定管理工作的通知》(2016年)的基礎上,通過委任性規則或準用性規則,對油污損害賠償的計算方法作出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使油污生態損害司法救濟有章可循[20]。
六、結語
“卡-梅框架”作為法經濟學領域分析侵權救濟規則的主導范式,將其運用于油污損害防治領域具有特殊意義。“卡-梅框架”將法律規則的“效果模式”作為分析問題的切入視角,突破了傳統法學慣用 “行為模式”的思維方式,引導我們從法的實效角度對現行油污損害防治法律規則進行檢視。此外,較之于其他法經濟學理論,“卡-梅框架”不僅將效率價值作為權利保護的重點,還特別關注外部性問題對于規則選擇的影響,而油污生態損害與其他傳統環境侵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外部性上。因此,“卡-梅框架”也提醒我們,油污損害防治領域的法律完善需要考慮外部性問題的解決方式,使法律規則的設計能夠充分體現資源的社會價值與環境價值,為有效率地維護環境公共利益提供法律指引。
參考文獻:
[1]帕特森.布萊克維爾哲學和法律理論指南[M].汪慶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15.
[2]WITTMAN D A.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M].Blackwell Publishing,2003:22-23.
[3]竺效.生態損害填補責任歸責原則的兩分法及其配套措施[J].政治與法律,2007(3):89-94.
[4]董正愛,王璐璐.邁向回應型環境風險法律規制的變革路徑——環境治理多元規范體系的法治重構[J].社會科學研究,2015(4):95-101.
[5]孟甜.環境糾紛解決機制的理論分析與實踐檢視[J].法學評論,2015(2):171-180.
[6] KRIER J, SCHWAB S.Property rules and liability rules: The cathedral in another light[C].70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5 :440.
[7]周林彬.物權法新論:一種法律經濟分析的觀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268.
[8]清華大學環境資源與能源法研究中心課題組.中國能源法(草案)專家建議稿與說明[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10.
[9]杜輝.環境司法的公共治理面向——基于“環境司法中國模式”的建構[J].法學評論,2015(4):168-176.
[10]沈海平.尋求有效率的懲罰:對犯罪刑罰問題的經濟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5.
[11]陳德敏,鄢德奎.我國“按日計罰”制度裁處程序的規范路徑[J].生態經濟,2016(2):202-207.
[12]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聯合調查組關于事故調查處理報告[EB/OL].[2012-06-21]. http://native.cnr.cn/news/201206/t20120621_509989271_4.html.
[13]代霞.中國能源消費總量:時序演變、影響因素與管控路徑[J].求索,2015(1):111-115.
[14]秦鵬.關于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實施的若干思考——基于國內首例跨省界環境公益訴訟案的分析[J].環境保護,2015(13):44-47.
[15]趙微,王慧.船舶溢油污染海洋的法律問責制研究[J].比較法研究,2012(6):122-133.
[16]羅南·佩里.深水地平線鉆井平臺溢油污染及其民事責任限制[C].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律評論(第86卷),2011.
[17]劉天齊.環境保護通論[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82.
[18]李偉芳.論我國海洋石油污染中環境損害的范圍認定[J].政治與法律,2010(12):117-123.
[19]鄧海峰.海洋環境容量的物權化及其權利構成[J].政法論壇,2013(2):131-137.
[20]郭楠.能源體制改革下油氣對外合作開采的規制失靈與規范路徑——以《對外合作開采海洋(陸上)石油資源條例》為研究[J].國際經貿探索,2016(3):10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