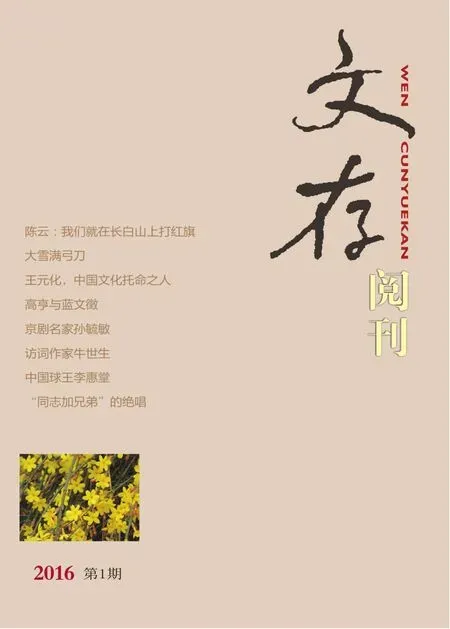大雪滿弓刀
□文煒
?
大雪滿弓刀
□文煒
劉建章,1910年3月出生于河北省景縣,1926年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學習時參加革命。1928年3月受中共黨組織派遣到延邊地區從事革命工作,歷任東滿特委(區委)委員、書記,延(吉)和(龍)中心縣委委員,琿春縣縣委書記。解放后,任鐵道部副部長、部長、黨組書記等職。本文記敘的就是他在極其艱苦和險惡的環境下,出生入死,為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幸福不屈不撓斗爭的故事。

十八歲書記的建黨大業
1928年3月,劉建章被組織上派往延邊,離開北平前,中共西郊區委的同志秘密約見了劉建章,先向他簡要介紹了延邊的形勢。
日本鬼子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在延邊設立了派出所、總領事館、分領事館,還開設了“東洋拓植會社”、“金融組合”等經濟機構,“三菱”“三井”這些大財團也在延邊設立分支機構投資做生意,牢牢把控了延邊的政治、經濟命脈。東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進入新階段,共產黨開始在各地建立黨團組織,雖然還不成氣候,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上級領導告訴劉建章,此去東北的任務就是給咱煽風點火的,就是給咱燎原的!領導還叮囑劉建章,到延邊之后先安頓下來,等當地黨組織與他聯系,聯系暗號“奉天朋友”。
抵達延吉后,劉建章被分到和龍縣稽查處(今龍井市三合鄉)小學。學校不大,一共也就四個班,學生幾乎都是朝鮮族。
對大城市來的老師,學生們充滿好奇,尤其是劉建章荒腔走板的河北版北京話常常招來孩子們善意的笑聲。這里與朝鮮的會寧僅八里之遙,兩處百姓常常渡過圖們江來往。這讓劉建章意識到無論是為了下一步的革命工作還是為了生活,他的第一要務都是解決語言問題。
劉建章的記憶力是驚人的,一個月后,他就能用朝鮮語和周圍人進行簡單對話了。在學生們眼里,大城市來的劉老師太有男神范了,他會踢足球、打籃球、打排球,他會唱歌、唱戲、耍大刀,他游泳還不是咱們的狗刨式而是蛙泳,最最重要的是他還濃眉大眼帥呆了!
不出幾天,學生們就都成了劉建章老師的粉絲。
劉建章趁機開始“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地向學生們灌輸愛國主義、馬列主義。偶像的力量是無窮的,劉建章幾乎沒費多少勁,就把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對軍閥統治的不滿種進了學生們小小的腦袋里。
4月的一天,劉建章接到一封信。信里寫到:“接到奉天朋友的信,知道你們已到延吉,十分高興,請抽空到龍井鎮《民聲報》一敘。
看到“奉天朋友”四個字,劉建章激動得熱淚盈眶,謝天謝地,組織上總算來找我了!
中午時分,劉建章已經出現在龍井鎮大街上。龍井鎮不大,劉建章沒費什么勁就找到了《民聲報》報館,見到了接頭對象周東郊。周東郊的公開身份是《民聲報》文藝版編輯。
周東郊向劉建章介紹了延吉黨的工作的開展情況,告訴他主要困難是人手太少,力量薄弱,許多事情力不從心,所以,對劉建章他們的到來,周東郊表示了由衷的歡迎。劉建章則把自己和其他十名黨員的情況向周東郊作了詳細匯報。
周東郊欣賞地看著劉建章,他發自內心地喜歡這個年輕人。激情、忠誠、思維縝密加上健康的體魄,這個年輕人具備了成為一名職業革命者所有必要條件,他需要的只是在戰斗實踐中淬火歷練。
1928年8月,經批準,中共延邊區委(后改名為特委)在龍井成立,周東郊任區委書記,劉建章任組織委員,這個在延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區委,在《民聲報》報館悄無聲息地成立了。
一個月后,延邊的共產黨基層組織放禮花般炸開,先后建立了十個黨支部,共有黨員二十二人。延邊區委組織委員劉建章能者多勞地兼任了和龍縣第一個黨支部——中共和龍縣三道溝黨支部書記。
黨支部剛建起來,上面就派下活兒了。中共滿洲省委提出了要在延邊四縣大力推廣國學啟蒙教育,以抵制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
這個任務,給大家出了一個難題,當時,各個小學使用的課本全部由張大帥的省教育廳統一編寫,統一使用。現在要編寫新課本,并且用新課本授課,教育廳肯定不會答應,怎么辦?
劉建章想起了自己曾經參加過的北京香山慈幼院的童子軍。童子軍是向孩子們傳遞正能量的一種絕佳方式。自己熟悉童子軍,建立一支童子軍手到擒來,更重要的是建立童子軍這樣的學生組織,無需教育部門批準,這就能繞過高壓線了。
劉建章的童子軍軍旗一豎起來,呼呼啦啦來了一堆報名的學生。幾天后,一支右臂統一佩戴紅色袖標的小小隊伍出現在學校操場上。紅色袖標上印著醒目的三個字:童子軍。
童子軍在校內有很高的威望,他們佩戴標識,手持棍棒在校門口站崗,阻止社會上的流氓、阿飛進校滋事,他們唱著“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真是威風凜凜,生龍活虎。
隨著人氣走高,劉建章對童子軍灌輸的思想開始縮小范圍,宣傳革命、抗日成為越來越精準的目標,不知不覺中,童子軍逐漸成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骨干隊伍。
劉建章開始帶領大家走出校門,開辦群眾夜校,走街串巷,深入農村和工廠演講,散發傳單,舉行秘密集會,喚起群眾覺醒。當年在香慈劉建章就辦過夜校,這個他有經驗,知道對癥下藥。他跟朝鮮族群眾講課時是這樣說的:
政府和日本人半拉眼角沒看上你們。而且你們現在納的稅比當年大清時多出三倍不止!
下面騷動了。
現在的政府比大清還不如,光知道朝我們要錢要糧,當我們是聚寶盆呢?收錢收糧也行,畢竟納皇糧是咱老百姓的本分,哪朝哪代也逃不掉,可你吃飽喝足了,日本鬼子來欺負我們,你又腦袋縮回王八殼不管我們死活,要你這樣的衙門有啥用?不如掫翻了重立一個!
劉建章還有一個陣地——《民聲報》。
人們發現,《民聲報》抨擊時事,影射政府,似乎越來越高調了,人們還發現,各版頭條的重要文章幾乎全部出自北平來的那些老師之手,尤其是署名劉建章的文章,更是文筆犀利,思想偏激,堅決跟政府唱反調。
當地由日本人創辦的《間島新報》疾呼:《民聲報》和從北平來的教師是延邊地區的兩大“魔影”,不除則必亂!
1928年10月,奉系軍閥政府把吉(林)會(朝鮮會寧)鐵路敦化—老頭溝段的修筑權,讓給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消息傳到和龍,劉建章帶領黨支部發動學生舉行集會,游行示威,抗議當局的賣國行徑。此舉提高了學生和工農群眾反侵略斗爭的覺悟,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民眾中的影響。此次活動,既得到了縣教育局局長關俊彥和六校校長周璣章等進步人士的多方支持和保護,也受到各族群眾的擁護,使黨的活動范圍進一步擴大。
一天,周東郊鄭重告訴劉建章:“據我方情報人員掌握的情況,當局和日本的特務機關已經擬定了一張跟蹤和調查的名單,而我不幸榜上有名。如果我有意外,你要接上,這件事已經過省委批準。”
劉建章沉吟半晌,問道:“你……怕嗎?”周東郊微微一笑,說出一句被現在影視劇用濫的臺詞:“怕死就不當共產黨了。”
跳躍的燭光放大了周東郊的微笑,放大了兩個人印在墻上的身影。“怕死不當共產黨!”劉建章永遠記住了這句話。他向周東郊發誓:“無論遇到什么困難和危險,我都會設法去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1929年1月18日凌晨,談話僅僅十幾天后,警察突襲《民聲報》,周東郊不幸被捕。十九歲的劉建章接替周東郊任中共延邊區委書記,繼續發動群眾開展斗爭,好像危險從來都不曾存在。
此時,另一位猛人正在趕來捧場的路上。此人姓陳名濤,是東北共產黨和中央的聯絡人。周東郊被捕,陳濤第一時間找到新任區委書記劉建章,商量對策。經過磋商,劉建章和陳濤決定走一步險棋:在和龍縣公開召開群眾大會,發動群眾,給縣政府施加壓力,爭取營救周東郊出獄。
陳濤的演講空前成功,老百姓炸了窩,廣場上群情激奮。當大批警察趕到時,陳濤早已被劉建章送上了開往大連的火車,警察毛都沒抓住一根,反而被參加集會的群眾團團圍住,罵了八輩兒祖宗。東北人暴脾氣不好惹,罵完了警察還不算,又圍住縣政府罵。
現在,周東郊被抓了、陳濤撤了,其他多名黨員也轉移了,劉建章陷入了孤立無助的境況,但工作不能停,必須讓延吉老百姓知道,共產黨還在,革命是不會終止的。劉建章召集黨員開會,制定了在延吉四縣同時貼出揭露蔣介石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罪行的傳單,以激勵民眾斗志的方案。
一個囚徒的偶像派生活
1929年2月9日,除夕,劉建章把一部分傳單分發給其他三名黨員,其余的全部裝進自己的包里,登上火車。他們要去各地分送傳單,第一站是龍井。
令人意外的是,車站上軍警林立,戒備森嚴,正對上下火車的旅客進行嚴格搜查和盤問。劉建章心里咯噔一下,心說壞了,估計沿途各站的情況都差不多,同志們帶著這些傳單誰也跑不掉。幾乎在瞬間,劉建章就做出了一個決定。他低聲對大家說:“把傳單都給我。”
大家還沒明白怎么回事,劉建章已經把大家的傳單全部塞進自己的挎包,起身向車門走去。臨走,撂下一句話:“誰也別跟著我下車,一會兒不論發生什么事,一定要沉著冷靜,趕緊回去向組織匯報。”
說話間,劉建章已經下了車。看著他大大方方向檢票口走去,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這是要吸引敵人的注意力,掩護大家安全撤退呀!
果然,在檢票口,劉建章攜帶的傳單被搜查出來。警察們如臨大敵,喊著“抓共產黨”,撲上來就把劉建章綁了個結實。火車啟動了,看著同志們安全離去,劉建章稍感安慰。
在龍井警察局,劉建章被鎖進一間候審室。這是一間很小的屋子,高高的墻上有一扇小小的窗戶,窗戶上裝著密密的鐵柵欄,顯然,這里插翅難飛。
過了三四個小時,審訊正式開始。主審是一名中年警官,在問過了姓名年齡職業這些基本情況后,警官話鋒一轉,突然問:“你是哪年參加共產黨的?”
劉建章一臉無辜:“我不是共產黨。”
警官冷笑:“不是共產黨?你身上帶那些傳單干什么?”
劉建章更加無辜:“哦,那些傳單呀?那是我在上車之前別人托我帶到龍井,說是有人來車站取。”
“是誰讓你帶的?”
劉建章一臉茫然:“我不認識。”
警官一拍桌子:“別耍滑頭,不認識,你為什么幫他的忙?”

劉建章在揮舞春秋大刀
“那人給了我五塊錢,而且我看那些傳單全是呼吁大家抗日愛國的,我覺得這應該不犯法吧。我是個教書的,我在課堂上也告訴學生要熱愛自己的國家,要保衛自己的國家,教育局關局長也是這么講的。你們不信可以去問問他。”
審訊暫告一個段落。
再說火車上那幾位安全脫險的黨員,他們一下車,急忙去教育局搬救兵。最有力的救兵當然是關俊彥局長。關局長一聽劉建章被抓,抄起電話就打到了警察局。接電話的恰巧是那個剛審訊完劉建章的中年警官黃澤孚,更恰巧的是黃警官曾經是關局長的學生,關局長向黃警官證明劉建章不僅確實是自己的下屬,而且是一位工作認真,為人正派的好教師。這樣的好人怎么會是亂黨呢?誤會了一定是誤會……
于是,黃警官在審訊結論上寫下了:疏忽致錯,嚴加教育。劉建章松了一口氣,以為很快就可以被釋放了。但由于抓住劉建章的事情已經上報,延吉鎮守使簽署命令把劉建章送到最高官署,繼續審訊。
第二次審訊開始了,這次的主審官是一位軍法處長,內容和第一次審訊基本相同。劉建章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產黨,就是個愛國青年。軍法處長顯然對這個案子對劉建章都沒什么興趣,草草走了一遍程序,呵斥劉建章說:“小小年紀懂什么?中國有一個國民黨就行了,還鬧什么共產黨,別跟著人家瞎起哄,到時候腦袋怎么掉的都不知道!”
劉建章假裝誠惶誠恐地直點頭:“是是是……長官教訓得極是。”
第二次審訊結束后,劉建章被押送到延吉監獄關押,等候最終判決。
因為劉建章跟“共匪”掛邊,典獄長怕跑了政治犯自己吃不了兜著走就對劉建章不僅給予“單間”待遇,而且贈送二十四小時佩戴腳鐐的VIP特殊服務。那個腳鐐少說也有五六十斤,堅硬粗糙,不出一天就把劉建章的腳踝磨得鮮血淋漓,到了晚上,因為戴著腳銬,沒法脫棉褲,只好和衣而睡,又冷又難受。
每天上午有十分鐘放風時間,別的犯人都在院子里溜達,就劉建章戴著腳鐐沒法走路,只能靠著墻根曬太陽。犯人們見劉建章又住單間又戴腳鐐,私底下議論紛紛,有人說他是飛檐走壁的江洋大盜,也有人說他是共產黨,總之,厲害角色!
劉建章呢,誰看他一眼,他都微笑點頭,親善又明星范兒,漸漸的,犯人們都在心里喜歡上了他。住在隔壁的犯人季國璋更是主動靠近,向他傳授“獄中生活實用手冊”,比如怎么把棉褲從褲襠到褲腳剪開,縫上諸多帶子,穿的時候系上帶子,脫的時候解開帶子,再比如怎么用棉布把腳踝厚厚纏起來,讓腳踝和腳鐐嚴絲合縫地融為一體,就不磨腳了。劉建章照著做,果然舒服多了。
判決書終于下來了。罪名:共黨嫌疑,刑期:一年。劉建章在心里長舒一口氣:沒有暴露身份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吧!漸漸地,他和犯人們也混熟了。有人問他:“聽說你是共產黨?”劉建章神秘地笑笑,沒有回答。那人又問:“聽說共產黨都是武藝高強的人?能飛檐走壁能百步穿楊還能刀槍不入?”這一問倒真是提醒了劉建章,我干嘛不給大家講講共產黨是什么人,這不也是宣傳鼓動嗎?劉建章說:“沒有你說的那么玄乎,共產黨也是人,跟你我一樣,有血有肉,有老婆有孩子,但可都是些能人,要跟政府干跟日本人干,沒點本事哪兒行?”
劉建章的話引得屋里的獄友都圍過來。他們好奇地問這問那,尤其對共產黨,充滿了好奇和模糊的認同感。
那個時代,監獄里根本沒有任何精神生活,劉建章就給大家講故事。當然,劉建章的故事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比如岳飛抗金、戚繼光抗倭等等,說的是古代的事,講的可是當下愛國抗日的理兒。漸漸的,劉建章像一塊吸鐵石般吸引了牢里的每一名犯人,連典獄長也忍不住來蹭聽他“故事會”。
典獄長姓涂,也是苦出身,雖然端了政府暴力機器的飯碗,但心地善良,對苦出身的犯人們管束并不嚴厲,對能講故事的劉建章尤其和善。典獄長還對他委以重任。監獄里設有教務主任,負責給犯人上課洗腦。這位教務主任因為體弱多病,班上得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偶爾上一課,永遠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邪歸正,重新做人”這些毫無創意的老套話,顛三倒四的說教搞得犯人們一聽課就打瞌睡。現在好了,有了劉建章這個會講故事的教書匠,不用白不用。監獄里,自己眼皮子底下,就算是共黨嫌疑犯,諒他也整不出啥妖蛾子。
就這么著,共黨嫌犯劉建章站上了張少帥大牢的政治課講臺,確實有點黑色幽默。
最初講課,典獄長還安排一名持槍獄警在一旁監聽,幾次之后,士兵來匯報:“劉建章講的都是歷史上的經典故事,反正都是保家衛國讓人學好的。”
典獄長問:“那犯人們呢?還睡覺不了?”
獄警說:“犯人們眼珠子瞪得溜圓,聽得入迷,課堂紀律超好。”
典獄長一聽,干脆讓監聽的士兵哪兒涼快哪兒稍息去了。這下,劉建章干脆拋開原教材,給犯人們講日本如何侵略中國,侵略朝鮮,欺壓凌辱中朝兩國人民,“二十一條”是賣國條約,號召大家團結起來,跟小鬼子對著干!跟軍閥對著干!跟天下所有地主老財老板工廠主對著干!
那個冬天,劉建章為延吉監獄所有牢房的犯人講了一遍課,典獄長又安排他去監獄的工廠講課,現在,犯人們都尊稱劉建章為“教師爺”。典獄長的勤務兵申守義,不可救藥地迷上了劉建章。申守義幾乎成了劉建章的影子,看他練拳,聽他講課,找他閑聊,跟他度過的每一分鐘都那么有趣那么快樂。
在接觸中,劉建章發現,申守義為人正直,思想進步,便產生了發展他入黨的念頭。如果申守義成為黨員,就可以通過他和外面的同志聯系上,當然,這件事同時也非常危險,萬一不慎暴露了自己共產黨區委書記的身份,后果將不堪設想。劉建章決定,進一步試探申守義。
有一天,申守義又來找劉建章聊天。劉建章向他描述了蘇聯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后,人民幸福生活的美景,告訴他那里沒有地主,沒有資本家,沒有剝削,人人平等……
申守義聽著,神往地說:“那多好啊,咱們什么時候才能像人家蘇聯那樣呢?”
劉建章拍著他的肩膀,肯定地告訴他:“只要有共產黨,有大家的力量,我們很快就可以實現。”
申守義激動了:“真的?如果這樣,我也愿意為共產黨做事!”
劉建章要申守義給接替他工作的趙志剛同志帶了一封沒有任何破綻的信,申守義帶回了趙志剛的復信。劉建章觀察了一段時間,一切正常。
不久,趙志剛和區委的王耿同志到監獄探望劉建章。劉建章跟他們講了申守義的情況,希望區委在外面做一些了解和考察。經過細致考察,組織上批準了申守義加入中國共產黨。
申守義的入黨儀式是在負責監視趙志剛探視劉建章的場合進行的,就這樣,劉建章愣是以一個囚犯的身份把典獄長的勤務兵發展成了共產黨員。在整個革命戰爭年代,劉建章就像一部宣言書,一個宣傳隊,一架播種機,走到哪里就把黨員發展到哪里,把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傳播到哪里,這種責任感使命感已經成為他的生活習慣。
屢敗屢戰
1930年初,劉建章服刑期滿。當監獄的大鐵門重重在身后關閉,劉建章抬頭望一眼干凈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氣,嘴角露出一個若隱若現的微笑。
出獄后,按照組織安排,劉建章留在延吉,公開身份是局子街北山小學教員,擔任一個班的班主任及全校的體育老師。這些,對劉建章而言,駕輕就熟,他開始了他的老本行: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揭露日本侵華暴行和國民政府的黑暗腐敗,激發學生對日本人的仇恨和對國民黨的不滿。
劉建章常常把《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這樣的禁書包上《啼笑因緣》一類的暢銷書封面,借給學生們看。在劉建章的煽乎下,北山小學進步學生越來越多,組織上認為時機已成熟,下達指示:在北山小學建立黨支部,由劉建章擔任支部書記。
劉建章入獄后,中共滿洲省委派其他人來東滿恢復黨組織的工作,建立了東滿特別支委,任命了新的特委書記。劉建章出獄后,甚至沒能成為東滿特支的領導成員。
這是有特殊原因的。作為一個成立時間不長的新生組織,共產黨多多少少存在著盲動和幼稚,在一些人眼里,為黨犧牲的英雄主義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最高境界,而被捕遠不如犧牲壯烈,尤其是被捕后又出獄就多少沾了嫌疑的邊兒,但是,在劉建章的一生中,無論被信任還是被猜忌,無論被重用還是被閑置,只要是來自組織的決定,他都毫無怨言地全盤接受,履行了十六歲那年,向黨的承諾:服從紀律,犧牲個人。
1930年,官越做越小的劉建章正心無芥蒂地帶領學生們參加延吉革命史上轟轟烈烈的“紅五月”暴動。
當時,中共滿洲省委給東滿特支下達了《全滿農民斗爭綱領》,要求盡快發動群眾舉行暴動,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境內修建鐵路,瓦解日本要發動的全面戰爭(這么大的口氣,確實夠盲動)。東滿特支為此進行了詳細的策劃,將時間定在五月,并取名為紅五月暴動。
劉建章帶領學生們到處張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沒收地主土地”、“不分民族人人分配”等口號的傳單。接著,全縣中小學全部罷課,學生娃娃不上課,全都上街游行,向政府示威。工人農民和市民們先是出來看熱鬧,看著看著,覺得學生們喊得有道理,就紛紛加入進來,游行的隊伍越來越長,喊聲越來越大,連“打倒國民黨軍閥”、“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這樣最敏感的口號都喊出來了。
5月25日,霹靂一聲震天響,全東北地區的第一個工農政權——藥水洞蘇維埃政府成立了。斗爭行動委員會鼓動工人、農民、學生和其他各行各業的民眾走上街頭,砸毀日本人開在延吉的商店、公司,襲擊和焚燒地主買辦的倉庫、住宅,平時最驕橫的土豪劣紳、有錢人聞風喪膽,四處奔逃,暴動持續了三天,政府機構陷于癱瘓。

1948年,劉建章和愛人劉淑清。

2004年8月,劉建章為新落成的大荒溝黨史教育基地揭牌講話。

2005年9月3日,胡錦濤為劉建章授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章并握手問候。
8月13日,中共延和中心縣委正式宣告成立,駐地設在龍井,劉建章是縣委委員,革命形勢一路高歌猛進,到9月初,黨員已發展到三百三十人之多。
“紅五月”暴動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人和東北軍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對藥水洞蘇維埃政權,他們的態度高度統一:堅決扼殺!
于是,昨天還相互戒備的日本鬼子和東北軍閥突然又穿上了連襠褲,出動大批軍隊、警察對共產黨及民眾進行了聯手絞殺。幾天功夫就有三千多人被捕,一百九十多名共產黨員壯烈犧牲,斗爭指揮者暴露,東滿特支被破壞,藥水洞蘇維埃政權遭到毀滅性打擊。
革命失敗了,這次失敗使從香慈來延邊的所有小學教員遭解聘,大家只好轉移到奉天或返回北平。在這次高調的暴動中,一直隱藏很好的劉建章也暴露了。
薄暮時分,校長帶著警察悄悄來抓劉建章,幸虧守大門的校工張東山冒著危險跑來通知他,他趕忙跳墻逃出了學校。
可是,警察的搜捕隊到處在抓共產黨,去哪里存身呢?一個大膽的想法蹦出來,對,去延吉監獄!最危險的地方往往最安全。
劉建章趁著夜色悄悄來到監獄,找到教務主任趙中相,打著哈哈說自己明天要去龍井辦事,路過此地,因帶的盤纏不多,想到老朋友這里借宿一晚。
這個不好好上班的趙主任從不關心政治,對劉建章這位“紅五月暴動”主要領導人的典型事跡竟全然不知,更不知道劉建章此刻的身份比坐牢那個共黨嫌犯還重口味:確鑿的共黨分子。他沒心沒肺地跟劉建章開著玩笑:“咋的,監獄沒住夠啊?”劉建章說:“只要你歡迎,我就來住,呵呵……”
就這樣,劉建章騙過了稀里糊涂的趙主任,在延吉監獄度過了一個安全的夜晚。那一夜,為了找到劉建章,警察們幾乎把小小的延吉縣翻了個遍,可他們想破腦袋也沒想到,此刻,劉建章正在監獄里睡大覺呢!
天蒙蒙亮時養足精神的劉建章溜出監獄,健步如飛離開了延吉縣城,經過帽兒山,來到龍井,敲響了曾經的獄友白道吉的家門。
白道吉親熱地把劉建章讓進家門。得知了劉建章當下的處境,白道吉拍著胸脯向自己崇拜的教師爺表示:“想住多久你就住多久,有我一口吃的就餓不著你。”
就這樣,白道吉不僅收留了劉建章,還成了劉建章與黨組織的聯絡員。為了麻痹敵人,組織上放出風來,稱劉建章已經跑到上海去了。警察得到這個消息,在黑名單上劃掉了劉建章的名字,心里總算落了停,難纏的共黨分子,禍害上海警察去吧!
史上最寒酸的縣委書記
一個月后,就在延吉警察局徹底放棄劉建章后,殺不光的共產黨在琿春組建了中共琿春縣委,劉建章化名劉春江,出任首任縣委書記。
這一次,給劉建章提供慷慨幫助的是另一名曾經的獄友——季國璋。對自己崇拜的教師爺,季國璋不僅包吃包住,還出謀劃策,幫劉建章選擇了一個安全的辦公地址:大荒溝。
第二天一大早,劉建章和季國璋、交通員上路了。他們很快就進了山。雖然才進10月,山里已經下了兩場大雪,厚厚的雪地上,雜亂地留下各種野獸的足跡,唯獨沒有人的腳印。路很難走,幸虧季國璋扛了一把鐵锨,一路鏟一路走,這樣走了約莫一個半天,終于來到一個較為平坦的山谷。
山谷里,幾間獵人廢棄的小木屋被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包圍著,季國璋撂下手里的鐵锨說:“就是這里了。夏天日頭曬不著,冬天白毛風吹不著,狗日的警察逮不著,怎么樣?”
劉建章哈哈大笑:“好地方!中共琿春縣縣委書記劉春江宣布:中共琿春縣縣委正式成立!哈哈哈……”
笑聲震落了樹枝上的積雪,震飛了鳥巢里的兩只小鳥。那是1930年10月,瑞金蘇維埃政權尚未成立,中共中央還掙扎在危局重重的大上海,中國工農紅軍也沒有集結,以游擊的形式艱難游離在南方最偏遠貧困的山區里,那時的中國革命處于絕對低潮期。劉建章內心深處也曾有過這樣的想法:也許,在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理想實現的那一天了。即便如此,劉建章從沒有過瞬間的動搖。他,是最虔誠的共產黨人。
幾間漏雨透風的破房、幾條生銹的破槍外加一些手榴彈,就是琿春縣委機關的全部家當了,首任縣委書記劉建章當仁不讓地成為中國共產黨史上最寒酸的縣委書記。
晚上睡覺,床鋪、被褥一概沒有,大家擠在稻草堆里,凍得牙齒直打架,劉書記發話了,沒錢沒槍沒關系,咱有堅定不移的信仰,有滿腔的熱血,還有一顆不怕砍的腦袋,還差啥?齊活兒!拉開架子干吧!
在劉建章的感染下,大家白天餓著肚子唱著《國際歌》刻鋼板,印傳單,晚上換上朝鮮族服裝,走街串巷搞宣傳鼓動。劉建章穿朝鮮族服,說朝鮮語,還學會了朝鮮歌舞,輾轉于清水洞、檳榔溝、三安、中崗子等村落開展工作。每到一戶,他盤坐在朝鮮族老鄉的大炕上,口上“阿媽尼”、“阿爸吉”不住聲地叫著,向群眾講岳飛抗金和義和團反帝的故事,教群眾唱岳飛《滿江紅》,講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講日本人和國民黨的統治壓迫……他在群眾心中播下信仰的種子,讓它們茁壯生長;他給被壓迫者點起了一盞燈,使他們看到了前進的路。
這個熱情膽大主意多的年輕人很快贏得了村民的擁戴,好幾次碰上警察的巡游隊進村,劉建章都是被村民藏到家里,搖身一變,成了村民的小舅子或二大爺家的三表弟,蒙混過關。
劉建章足跡所至的一個個村莊升起了革命的曙光,照亮了琿春黑暗的夜空。混沌沉睡的民眾從夢中醒來,他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投身于革命斗爭的洪流中。清水洞、中崗子、駱駝河子秋收起義吹響了反帝反封建斗爭的號角。
除了搞“反日會”、“農民協會”、“婦女會”、“兒童團”等這些慣常套路,琿春縣委還組建了飛行隊。當然,飛行隊配不起飛機,從鬼子、警察那兒繳獲(其實就是偷)的幾輛自行車是飛行隊的最高配置。
殺惡霸地主、在紅白喜事上演講、貼標語發傳單,飛行隊來無影去無蹤,搞得敵人頭疼無比。在國民黨縣政府的懇請下,日本情報部門業內資深人士親自出馬,伸出獵狗般的鼻子四處狂嗅,終于搜集到可靠情報:琿春,中共縣委負責人名劉光公(劉建章在龍井時的化名)領共黨若干,聚集大荒溝一帶……”另有情報:“風聞劉某者,新近從延吉過來,有共化行為,曾在哈達門村吳金魁家落腳……”敵人一直在跟蹤追捕他,但由于縣委機關隱蔽和群眾掩護,敵人的企圖沒能很快得逞。
1931年初,游巡隊集合了上百人,悄悄摸到大荒溝,意欲清剿中共琿春縣委,并活捉赤匪頭子劉建章。
危機關頭,劉建章碰巧出差了,機關其他同志也都出去公干,游巡隊跋山涉水忙活了半天,連共產黨的一根汗毛都沒撈到,氣得一把火燒了那幾間破房,回去的路上順手抓了曾經留宿過劉建章的季國璋的姐夫吳金奎,回去交差。
去東滿特委匯報工作的劉建章對家中變故全然不知。辦完公事,回到琿春,順便去季國璋家討口水喝。一進門,把季國璋嚇一跳:哎呦我的劉大膽,你還在這兒晃悠呢!警察天天來我家搜捕你,開出的賞金是“一兩金子一兩骨,一兩銀子一兩肉”,你萬萬不可停留,趕快走!
季國璋拉著劉建章就往外跑。邊跑邊說:“我知道一條小路可以直達圖們江,你趕緊過圖們江到朝鮮去,就安全了。”
季國璋送劉建章到村口,給劉建章指明了小路,就揮手讓他趕緊離開。走出好遠,劉建章回頭望去,季國璋還在岸邊揮手,示意他快走。劉建章最后望了一眼模糊在暮色中的季國璋,在心里說:“等著我,等到勝利的那天,我一定回來看你。
那個逃離的冬夜,東北大地千里冰封,劉建章踏著厚厚的冰碴碎雪,深一腳淺一腳跋涉前行,無數次地摔倒再爬起來,一口氣跑了幾十里,終于甩掉了警察的追捕,趕在天亮前渡過了圖們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