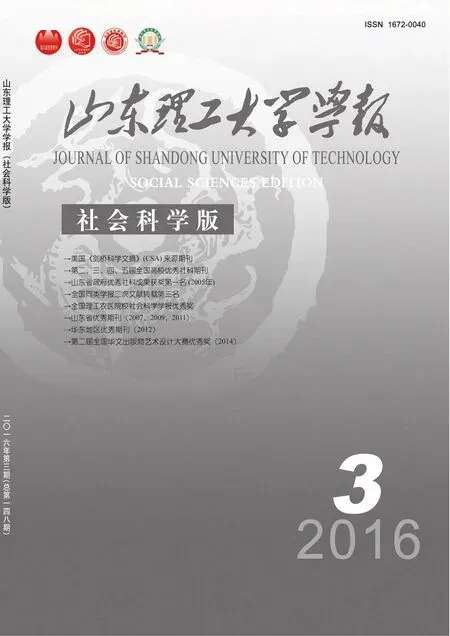重訪灰色地帶:策略實踐與文化政治
——從《雙城故事》看華萊塢電影書寫
洪 長 暉
(浙江傳媒學院文化創意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
重訪灰色地帶:策略實踐與文化政治
——從《雙城故事》看華萊塢電影書寫
洪長暉
(浙江傳媒學院文化創意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上海從孤島到完全淪陷,再到重回國民黨統治,抗戰時期共計八年,整個上海電影界呈現出錯綜復雜的面貌。這一時期的電影作品在傳統電影史書寫中被置于二元框架下的歸屬,因而處于一種消聲失語的狀態。傅葆石博士的研究專著《雙城故事》有助于我們重新讀解這段歷史。在那個復雜的場域里,借助電影剖解、闡發那個特殊語境下的社會生存狀況,電影人及其作品呈現出的策略實踐、反映出的文化政治,值得重新書寫。
《雙城故事》;電影文學;中國早期電影;華萊塢
20世紀早期的中國電影,不僅伴隨著坎坷的現代性進程,而且由于相伴相隨中華民族的抗爭歷史,從而額外具有突出的民族主義樣態。這種多變姿態和多元格局在抗日戰爭期間就顯得更為明顯,又反過來增加了讀解和品味這段歷史的難度。長期的回望實踐中,二元對立的框架被簡單化地定型為認知圖式,英雄與漢奸、“自由中國”與淪陷區、抗爭與附逆,一系列的標簽,既構建了整個電影世界的政治分野,也推演成對不同區域生產的電影作品的質量判斷。而顯然地,這樣的認知一方面顯示了當時的社會語境下權力的分配,一方面則意味著大量的模糊地帶被忽視,存沒于其間的人和事則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且無力發聲的犧牲者。
傅葆石博士的《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劉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簡稱《雙城故事》)就試圖再現流動于上海和香港兩座城市間的“灰色地帶”,描摹出中國電影在當時特定的國家政治環境中騰挪閃躲、左支右絀的姿態。
一、如何理解淪陷區電影?
中國電影事業的起步與發展都和西方尤其是好萊塢電影緊密勾連,而作為十里洋場的上海則是這種聯系和紐帶的見證及體現,即使是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1938年上海淪陷之后,這種聯系也沒有中斷。于是乎,當我們審視淪陷區電影時,也就沒有理由忽視這層關系所帶來的深層影響,甚至于,因為淪陷區的獨特地位,以及因之而來的復雜糾葛,這層關系就更為微妙、多元和動態,考察它則更見闡釋者的想象力與洞察力。
傅葆石博士所瞄準的就是淪陷區電影在動態的歷史進程中所呈現出的復雜面貌。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經提出“同情之理解”,以求從詮釋者的自我心性休養為基礎,對詮釋對象(文本)視之為人的生命表達方式,從而達致內在共通*關于“同情之理解”可以參看周可真的《中國哲學詮釋方法——“通情之理解”的源流及其限制》一文。該文見《河南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5至9頁。陳先生原話為“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傅葆石的研究在這里就可以印證了陳寅恪先生的警語。
《雙城故事》中特別剖解了淪陷區電影的諸般樣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本文提到的“淪陷區電影”并不是一個嚴謹的時空概念,它既包括孤島時期(1937-1941)的租界區域,也包括上海完全淪陷的時期(1941-1945)。而之所以不做這樣嚴格區分,是因為在筆者看來,這些時空區域里的電影作品與實踐都具有相當一致的策略性,處于這些時空中的電影人(和其他普通知識分子)均普遍地在心靈上被動割裂了與“自由中國”的聯系,并且由此而來產生極大的愧疚、糾結乃至幻滅。盡管在程度和方式上不同個體會存在各種區別及變體,不過并沒有給研究者的觀照造成根本性障礙。
那這種策略究竟如何?傅葆石用了一段略顯拗口的話,精準地涵括了其內在精神:無關政治的娛樂通過有意地非政治化具備了重要的政治意義(apolitical entertainment that was deliberately depoliticized became significantly political)。對這句話的理解可以從兩個層面上來看,首先,作為一種現代大眾媒介,電影本身就是“充滿這戲劇化的感性和思想的濃湯”,從其誕生之初就更多地是扮演著娛樂大眾的角色,這樣的功能定位在戰前中國尤甚。李歐梵先生在《上海摩登》一書里就已經指出,早在上海淪陷前,電影院已經成為充滿現代因素的公共場所,而電影文化——無論是看電影,還是翻閱影院裝潢雜志和影迷刊物——已經是現代生活的點點滴滴了[1]118。另一方面,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一層,刻意地將電影作為娛樂,并限定于此,既是淪陷區電影的生存策略,也是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態。傅葆石在書中講得非常透徹,“淪陷電影并不完全是相對于自由中國的國民黨官方電影的漢奸文化工具,相反,它建立了一種新的公共空間,讓淪陷區的民眾在這個空間內參與構建一種娛樂文化話語,逃避日本帝國主義操縱和建立的‘大東亞’侵略文化”[2]163。
眾所周知,在淪陷后的上海,由于日偽合作提出所謂的“國策電影”運作方式,強行要求電影人進入中華電影股份公司(簡稱“華影”),否則就面臨生存危機。因而以非此即彼的“忠奸”二元模式(即殺生成仁的“英雄”與為虎作倀的“漢奸”)來看待淪陷區電影人及其實踐,顯然是不合適的。在傅葆石看來,“淪陷電影提倡中國的民族傳統和民眾的欲望和想法,而淪陷區的統治者則視這種形態的電影為庸俗不堪和毫無價值:也就是說,這僅僅是娛樂!換句話說,淪陷電影一方面和日本人妥協,一方面又抵抗了他們的文化統治”[2]163。
質言之,每一個處于淪陷區的人都是鮮活的個體,他們各自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承受戰爭帶來的苦難或沖擊。這種回應的途徑紛繁多樣、五花八門,而其指向又殊途同歸,意圖在逼仄的現實空間里尋求生存乃至生活,所差者或為尊嚴、或為物質,雖說求仁得仁,但總體上則組成一個規模可觀的“灰色地帶”。
二、淪陷區電影對誰重要?
十里洋場的上海無疑是民國時期最具現代性的中國都市,這種“現代性”識別甚至在內地和東南亞都具有超高的影響力,“外地人一有機會到上海,就會迫不及待地去看好萊塢電影或到南京路購物,尋找融入大都市的感覺”[2]41。而在20世紀20~40年代的中國電影版圖中,上海電影一方面形成與“以北京為中心的非商業化的政治教化電影或稱京派電影”相對應的“海派電影”,這“海派電影”既指一種“與特定文化形態密切相關的電影流派,同時也指中國電影發展的一個階段”[3]7,它是以現代大眾商業文化為基本特征的。另一方面,上海電影還在商業驅動力作用之下,向外拓展,從而在香港乃至東南亞一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然,這種作用是一種雙向的過程,在時事格局變動之下,香港以后來居上的態勢最終取代了上海成為亞洲電影的又一中心。這也正是傅葆石在其論著中所著力勾勒出的演變圖景。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上海電影在整個抗戰時期的位置不僅沒有由于戰爭而削弱,反而成為各方角力和爭奪的舞臺。換言之,上海電影的重要性越發突出,這也就很好理解為何日方開始時試圖建立像“滿映”那樣以生產殖民電影為目的的“宣傳機器”,后來雖然放棄這一企圖,但仍然整合中國電影生產機構成立中華電影公司(1939年于南京成立)、中國聯合制片廠股份公司(1942年上海川喜多長政主事,張善琨等參與其中),在后期更是直接以控制膠片等資源的方式嘗試掌控和導引上海電影的方向。而一旦這一目標未能完全實現,日方則會大加指責,認為“中聯”電影既沒有教導淪陷的人們“新東亞秩序”,也沒有教育人們去認識“大東亞戰爭”的本質[2]174。
日方的這些不滿與指責恰恰提供了從另一視角審視淪陷區電影的可能。可以稍顯化約地說,日方控制電影生產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要為其殖民政策服務,強化的是電影的政治宣導功能,因而絕不滿足于“讓人們沉浸在娛樂傳統”中;而對于淪陷區的電影人來說,電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這也是他們為什么沒能丟開電影(這是他們的生計所系)前往“自由中國”的最重要原因,由此,如何在這樣的日常生活實踐中,既能夠巧妙地傳遞出他們的無奈與不甘,以求化解或沖淡他們不能“堅決抵抗”的道德焦慮,又不至于挑戰殖民者的底線導致生存可能的湮滅,就成了電影人的策略應對。
法國社會學家德賽圖就非常明確地指出,日常生活就是“透過以無數可能的方式利用外來的資源來發明自身”,他將日常生活看成一個在全面監控之下的宰制與抵抗的斗爭場域,職是之故,人們的日常生活并沒有在技術專家政治的規訓網絡之中趨于同質化,人們亦非毫無抵抗能力[4]182。無獨有偶,詹姆斯·斯科特也在對東南亞農民的“怠工”研究中提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這樣的概念,盡管斯科特分析的對象是農民在面對生產壓力時所做的各種隱性抵抗,但是顯然,它也同樣適用于對淪陷區上海各色人等的生存策略和文化政治的分析。也只有充分考慮這些日常的潛行于生活中的抵抗,才能夠避免薩義德所批評的那種“抽離歷史時空的文本世界”,回到淪陷區電影的“灰色地帶”,因為正如斯科特所說,在侵略強權下的空間中,“不公開的異議”是能夠被安全的表達出來的[5]4。
正因為借助電影的“表達”,上海電影人不僅使生產電影或從事與電影有關的工作變成個人維持生計之道,而且還成為他們承擔和減少(看似矛盾,其實恰是合二為一)身處殖民統治的焦慮與愧疚的一種自我宣稱。亦即是說,與作為殖民者的日方將電影看做殖民宣導的工具不同,上海電影人不僅將電影視為物質意義上的,更是文化政治意義上的,而如其宣稱,之所以選擇了娛樂化的表達,其實只是特定殖民情境下的策略實踐,一種煞費苦心的策略實踐。
“娛樂不僅僅是娛樂”。但是處在“自由中國”的國統區人則不會這么認為,毫無疑問,國統區也非常看重電影,尤其是看重電影的戰斗動員價值。不過,也正由于戰爭的緣故,國民黨失去了對上海這一“東方好萊塢”的控制,而后方薄弱的產業基礎、貧乏的物質條件、短缺的資金供給,都直接制約了高品質的抗戰電影的生產可能,于是乎,寄望于“孤島”時期的上海電影自是應有之義,而面對滔滔的娛樂電影又自然是“恨鐵不成鋼”——因為,對于戰爭動員,電影太重要。
三、個案重審:《木蘭從軍》“遭焚”事件
如上所示,淪陷區電影成為一個多方力量角力的場域。而1939年由新華公司(張善琨所有)拍攝的《木蘭從軍》上映前后的遭遇則恰恰是一個極佳的分析案例。
張善琨成立的新華公司可以說是淞滬抗戰結束后,上海電影迅速恢復的一個標志。在個人影響力、與日方曖昧關系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新華公司很快成為上海電影界最大的公司。數據顯示,1939年新華公司共生產了24部電影,超過當年全上海電影總產量的一半,而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由陳云裳主演的《木蘭從軍》(卜萬蒼導演,歐陽予倩編劇)。
《木蘭從軍》是一個典型的借用中國傳統故事編排的電影,在當時的特定語境下,木蘭替父從軍的傳奇就成為一個充滿隱喻的象征,影射著空前的民族危機,木蘭本身也演化為一個洋溢著愛國激情的英雄符號。正如當時劇作家阿英的評論所言,“在民族危亡之際,所有的人都必須團結起來,奮戰救國,這是男人和婦女都應該做的”[6]33。這樣一個絕佳的電影選題,再加上張善琨高超的運作技巧,將木蘭的扮演者陳云裳塑造成一個既有現代觀念又有傳統美德的女性形象。這樣的形象一方面迎合了上海市民的欣賞需求,一方面又淡化了陳云裳外來者(陳云裳來自香港)的反差,使陳云裳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巨星。而電影也同時取得史無前例的成功,自首映之日起,《木蘭從軍》連映83天,打破了上海電影的一切票房紀錄,也正因為《木蘭從軍》的成功,進一步奠定了張善琨在上海電影業的不可撼動的霸主地位。
對于這樣一部古裝劇,上海評論界一片溢美之詞,如有評論就這么寫道,“《木蘭從軍》告訴我們,對外國入侵我們應該如何回答,怎樣回答”。與此同時,該片還引發了一波古裝片風潮,根據胡菊彬的研究,1938~1940年間發行的影片中有一半都是歷史古裝片,而1939~1940年更是被稱為“古裝年”,此類影片遠超50%[2]163。以講述古代故事來書寫當下,幾乎成了上海電影業的一種套路,而此間的電影人也以此作為自己不忘國仇家恨的佐證,他們自述為“電影的話語資源、框架、剪輯和舞臺布置都越來越和敘事目的相融合”[7]120。可以說,《木蘭從軍》的拍攝如果不是讓上海影人重新站到民族大義的制高點的話,至少也蕩滌了他們心頭的屈辱感與愧疚感。
可惜這恐怕是一廂情愿的自我感覺良好。因為在國統區的人看來,并不存在可以茍延殘喘的“灰色地帶”(在忠奸二元的對立格局中,他們是不可能承認有這樣的可變空間的),抗日文藝是整個社會主流的思想,只要不是為抗日服務的,那就是投敵的,所差者間接與直接、程度深淺而已。盡管整個抗戰時期,“自由中國”生產的電影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乏善可陳,重慶在七年間僅僅生產了20部故事片和63部記錄片(顯然與上海不在同一量級),可是這并不妨礙他們能憤怒地聲討上海電影界,當時的中央電影制片廠廠長羅學濂有一段話很有代表性:“電影從業員除了部分優秀的投奔內地,和部分投機的赴港掘金或躲避外,留在上海畢竟還是少數……孤島的極少數電影人落水,有少數的蟲豸蜷伏在黑暗的角落里投機買賣,更聰明的則攝制意義相異兩種拷貝,甚至巧立名目的影片,在變相的出賣靈魂……穆時英、劉吶鷗之流已被‘誅伏’……中央政府還會有更多的制裁。簡單說,上海電影正處在忠貞無恥的生死斗爭時刻。”[8]431
在這樣的憤怒聲浪中,上海電影界的驕傲《木蘭從軍》就在內地遭遇了“焚禁事件”。1940年1月,經歷了重重波折和關卡之后,《木蘭從軍》在重慶公映,引起轟動的同時也帶來各種非議,當月27日下午場放映該片時,有人爬上舞臺叫喊,指出該片導演卜萬蒼是上海偽市委黨部執委,因此該片是一部用愛國主義的名義去替日本人宣傳的漢奸電影,強烈要求燒毀該片,群情激奮之下不僅將該片膠片焚燒,還引發現場一片混亂,不得不靠軍警維持秩序。
盡管事后調查發現這是一起暗中精心策劃的事件,可是恰恰也折射出重慶方面的文化人對忠奸分隔的敏感——事實上,他們對《木蘭從軍》的聲討也聚焦于導演制作人、公司等的背景,而不是電影內容本身。焚燒《木蘭從軍》,可以看做是“自由中國”對那些身處上海的電影人的一次敲打和警告,而包括張善琨在內的上海影人都深感屈辱,他們再次意識到沒有旗幟鮮明地向日本人抵抗、宣示,就不可能被民族主義陣營所容納和接受。這種屈辱感既讓上海電影人越發謹小慎微,又不得不游走在“灰色地帶”,等候黎明到來。
四、華萊塢影史書寫——另一種可能?
時經七十余年,當下的中國電影正面臨著一個全新的發展契機。如果讓當年的民族主義者看到這一切,不知當作何感想。歷史不能假設,但卻需要不斷地書寫。自國內傳播學者邵培仁先生提出“華萊塢”的學理概念以來,有關的論述就成為一個熱點話題。其中討論較為突出的是“華萊塢”的概念界定與內涵指向(關于此,筆者也有自己的淺見,在此不再展開),不過,有一點邵培仁先生已經講得非常清楚,提出“華萊塢”概念不是要向“好萊塢”宣戰,而是一種“競合多元”的關系。
事實上,當我們回顧中國電影史的時候,就可以發現好萊塢一直是中國電影的對話對象。這也是一個顯見的事實,只是另一個史實卻容易被忽視了。那就是,好萊塢作為一種電影力量幾乎從未停止過對中國電影的影響,可在這層影響之下還有其他的力量曾經作用于中國電影——如果說這些其他的力量沒有改變中國電影的進程,至少也曲折地形塑了中國電影的風貌。換言之,華萊塢電影無疑要回溯過去,在時空中成就現在與未來;而在這種回溯的過程中,或許要發掘出潛藏著的“灰色地帶”,析出曾經曲折影響中國電影的日本力量(也許還有之后的蘇聯、東歐力量)。
傅葆石先生的著作顯然沒有從這個層面上來討論,他自己也說得很明確,《雙城故事》不應當被視為一部電影史作品,而是借助電影剖解、闡發那個特殊語境下的社會生存狀況,作為“人”如何應對外來力量形成自己的策略實踐,而這種策略實踐又該被做出怎樣的文化解讀。但是,正因為傅葆石對“灰色地帶”的描摹,我們可以看到歷史脈絡中的華萊塢電影在抗戰語境中的多元光譜,忠奸背離下的“灰色上海”。華萊塢電影史的寫作除了關注那些影響深遠的電影事件之外,還需要在一種日常生活觀照的范式中,去審察那些一個個的鮮活個體在各種作用力的沖擊之下如何騰挪閃躲,他們又有著怎樣復雜的心態?這樣的華萊塢電影史書寫將是豐富、細膩和動人的。
[1]Leo Ou-fan Lee.Shanghai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J].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傅葆石. 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M].劉輝,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3]盤劍.選擇、互動與整合:海派文化語境中的電影及其與文學的關系[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4]吳飛.“空間實踐”與詩意的抵抗——解讀米歇爾·德塞圖的日常生活實踐理論[J].社會學研究, 2009,(2).
[5]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M].張霖,譯.劉輝,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6]阿英.關于木蘭從軍[J].文獻雜志,1939,(6).
[7]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8]重慶市文化局電影處. 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電影[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責任編輯楊爽)
Revisiting the Grey Zone: Tactics Practice and Cultural Politics——Huallywood Film Narrative fromStoriesofTwoCities:CulturalPoliticsofEarlyChineseMovies
Hong Changhui
(SchoolofCulturalCreativity,ZhejiangUniversityofMediaandCommunications,Hangzhou310018,China)
From being isolated to being totally occupied and to being under the reign of Kuo-Min-Tang, the city of Shanghai underwent complex changes together with its filmdom during the 8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movie products of that period of time were subjected to dual frames of attribution in traditional film narrative, and thus stay silent and invisible.StoriesofTwoCitiesby Fu Baoshi serves as an effective way for people to re-interpret that period of history. Confined to such a complex situation, film-makers depicted and interpreted the social existence situation in that special context, and the tactics practice presented in their works, the cultural politics reflected by the works all deserve reconsideration.
StoriesofTwoCities; movie literature; early Chinese movies; Huallywood
2016-01-29
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中國夢影視的創作與傳播策略研究”(15ZD01);浙江傳媒學院新聞傳播研究院重點項目“民族現代性的歷史影像呈現與國家認同研究”(Z431Y16516)。
洪長暉,男,安徽績溪人,浙江傳媒學院文化創意學院副教授,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后,傳播學博士。
J905
A
1672-0040(2016)03-00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