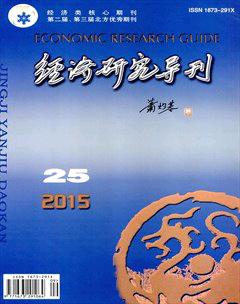論新時期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
周麟欣
摘 要: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能夠保障人民文化生活的基本需求,有利于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厘清現代社會的復雜與多元,對構建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至關重要。中國鄉村有其本身的特點,在中國鄉村地區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科學的理論與正確的實踐缺一不可。
關鍵詞: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5-0030-02
一、公民文化權利與公共文化服務
公民文化權利包括多個層面的內涵:享受文化成果的權利、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開展文化創造的權利以及對個人進行文化藝術創造產生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利益享受保護。文化權利同其他權利一樣,是一種道德權利、普遍權利和反抗權利,它是人類歷史活動的產物,它的出現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體現[1]。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顯得尤為重要。作為實現公民文化基本權利的重要途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是實現公民文化權利自覺和自為的制度性平臺。即公民文化權利的良好實現,離不開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務,而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務必須建立在一個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之上。其次,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文化產業作為新的國民經濟發展重點與增長點,是時代與歷史的必然要求。歷史經驗表明,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與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務對文化產業的繁榮與發展起著支撐、促進作用,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文化基礎。最后,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對提升國民素質,提升國民生活幸福感,促進社會和諧有著重要作用,是國家影響國民意識形態的重要手段。
二、當下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存在的問題
(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缺乏理性態度
公共文化服務在于尋求民眾總體的公共利益,然而公共利益并不因為公共以及群眾的概念等同與人人相等的利益,過分強調公共利益有時反而不能獲得利益最大化。犧牲小部分人的利益來滿足大部分的需求,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普遍做法。但如果當小部分人的利益獲得滿足時能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那么追求公共利益便不是利益的最大化,或是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過程中放棄了長遠效益的考量,就與公共利益本身的價值與目標背道而馳。公共文化服務的提供者與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明晰公共利益的真正內涵,防止在追尋公共利益過程中對公共利益本身造成損害,避免落入“公共利益等同人人利益”的陷阱。保持一種清醒、批判、尊重的態度來面對和處理公共問題,是作為一名文化人必須持有的素質。公共同民主一樣,本身不具有任何立場與屬性,其相應的色彩乃是認為在時間過程中添加與賦予的。西方國家就曾利用民主針對前蘇聯進行了“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表面名為實現人權自由,實質是對國家利益進行的分化瓦解。而西方也有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名言,保持清醒、批判、尊重的態度,以人民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來面對公共相關問題,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群氓”的惡劣后果,也能避免所謂精英的“納粹”。
(二)文化碎片化對公共文化服務的消極影響
1.消費區隔加劇文化碎片化。就目前的社會現象來說,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受“碎片化”趨勢影響,也逐步碎片化。當下,受大眾文化消費的影響,使得客體價值、矛盾多元化。例如“大眾之俗”與“精英之雅”,表現為大眾文化消費追求的娛樂性和“精英”所追求的藝術性,對于二者來說都是愉悅且快樂的,他們都從各自的追求中達到了滿足自身的目的。借用古典美學的觀點,康德和黑格爾對于藝術和美的探討得出無論大眾還是精英對于美的追求都不存在分歧。其美是理性的感性顯現,表現在事物上,便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這種統一反應在古典哲學中,就是和諧自由,均衡統一。大眾與精英二者間產生文化消費與文化需求矛盾的一大原因便是消費這一重要因素。消費不僅僅區隔了群體,人為地給各個群體貼上標簽,強化了各個群體之間本已存在的差別,甚至創造差別,更為重要的是消費伴隨著商品而商品背后便是資本,資本的介入以營利為目的,刻意進行了消費方式的引導,在加劇了群體間分化的同時,也催生了群體間的矛盾。消費所帶來的矛盾,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使得人無法獲得感受事物的自由,因此也就達不到對于美和藝術的純粹追求,也就使得大眾之俗和精英之雅爭論不休,加劇了文化的碎片化。
2.文化碎片化倒逼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的興起伴隨著信息的爆炸,信息的爆炸使得所謂的“知識”不斷膨脹,歷史上人們對于知識的獲取和追尋從未有過像今天這般廣泛、易取。科技的進步壓縮了時間和空間,文化產業的興起豐富了對于“知識”的解讀,二者結合在一起也使得知識呈現了一種扁平化與碎片化。由此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廣泛的知識獲取擴張了人們的視野;另一方面,扁平化與碎片的知識(微信、微博)使得人們對于世界的認識呈現塊狀與帶狀。廣泛的知識獲取在拓寬了人們視野的同時,也使得人們對于現實生活的思考更加寬泛,與之相對的卻是當下生活的單一、單向。而對世界的認識呈現塊狀與帶狀,在經個人主觀的聯想與臆斷,便表現出了一種與事實截然相反的推斷。
人們對于“理想生活與當下生活相矛盾”的解決辦法,往往采取旅游、懷舊、叛逆來進行調和。以上三種行為的實質其實都是人們對當下生活矛盾的改良。在知識借助“自媒體”不斷泛化同文化產業的不斷發展的情境下,這種改良的方式和方法也會不斷豐富,與之相應的是對改良的解讀也不斷多元。但又因生活的單向和資本綁架所帶來的刻意引導,最終人們呈現的卻是異常的單向。兩組矛盾帶來了如今人們文化生活中離奇的一幕:人們在做出改良當下文化生活的同時,卻又在質疑反思改良的行為;有著豐富的選擇卻最終呈現了一種單一。這離奇的一幕無疑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務的標準與要求,加大了公共文化服務的難度,也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增加了難度。在反思公共文化服務碎片化的趨勢時,人自身的理性與現代生活的客觀事實,知識的泛化與文化產業的發展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
三、新農村建設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
“新農村建設”背后隱含著一個更大的民族及國家的歷史時代訴求:中國廣大鄉村社會的現代建構,其中最為關鍵之處在于能否在廣大農村地區建設現代意義上的“鄉村社區”[2]。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是“新農村建設”中重要的一環,沒有相應的文化作為保障是不會長久的。
(一)構建鄉村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本動力
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本動力。臺灣傳統農村的社會結構同空間構造以及變遷過程,同中國傳統農村有著極其相似的一面。所不同的是,臺灣農村在與外界壓力同一系列社會運動的過程中,以“地方認同”的“共同體”意識為基礎的社區營造扮演了重要角色。從臺灣的社區營造身上,學界承認通過社區營造帶來社會轉變的可能性,同時也發現,依附于社區運動的“政治的、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與空間的改變與創新。臺灣地區較為成功的社區營造可以成為中國建設新農村的良好借鑒。社區營造是過去二十年臺灣重要的社會改造運動,并逐漸深化成為一種共同的社會經驗。這種共同的社會經驗成為了社區營造與公共利益的銜接點,即社區營造是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其目的是最大化實現公共利益。
(二)整體性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臺灣的社區營造對于當下新農村建設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的另一個重要啟發是,整體性的社區營造對于社會結構轉變的影響。社區營造并不是一個單純片面的文化運動,政治運動,而是一個全方面整合的社會運動。臺灣學者翁玲玲的報告中得知,臺灣的社區營造,往往是建立在一個地方性產業的基礎上,以地方性產業為核心而進行的系統性、整體性的建設活動。一定是在有一定經濟支持的條件下,以提高地方的公共利益為目的才得以建設并實現的。這再一次表明,在商品經濟的年代,經濟因素仍然是影響公眾利益的最大因素,所謂的文化依然側身于經濟之后。但我國目前在鄉村地區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部分項目與服務存在盲目地拔高農村地區的文化自覺程度;以學者的想象與愿景來取代地方民眾的實際需求;隨意地將鄉村地區的特色文化標簽化。這些行為都缺乏一種對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認識,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與現實割裂,片面強化其與地方文化經濟的聯系都會導致公共利益的被分割,加劇了文化、利益的碎片化,不利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在中國鄉村構建現代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定要重視社會環境與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之間的適配性,整體性、全方位地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三)重視中國鄉村社會結構與人際關聯
中國鄉村社會結構經歷了從傳統鄉村社會的封閉性、內聚性,到現代商品經濟活動打破了村落的封閉性,國家政權建設破壞鄉村共同體的內聚性,改革開放后鄉村受行政權約束減弱的歷史進程。中國鄉村社會的歷史進程決定了,雖然新農村的建設是打造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但并不等于憑空造樓,而是需要在舊有的基礎上有所傳承、批判與創新。
文化是屬人的,而人際關聯是社會結構的基礎,社會結構也決定著人際關聯模式。了解中國鄉村社會結構,便于了解中國鄉村人際關聯,了解中國鄉村人際關聯,便于利用人際關聯,將公共文化服務的效用與質量大幅提升。關于中國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人際關聯,費孝通先生著名的“差序格局”和“團體格局”廣為學界接受,將人際關聯定位親疏遠近,并區分了中西方人際格局特點[3]。
總之,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一個社會性的公共工程與社會運動。歷史經驗表明,政府與民眾在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必須保有一定的理性精神與批判態度。從本質上說,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代表著廣大人民利益的實現,因此在構建過程中應該更科學、更合理,切勿淪為經濟發展的催化劑與地方政績的假面子。
參考文獻:
[1] 藝衡,任琚,楊立青.文化權利:回溯與解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2.
[2]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118.
[3]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9-32.
[責任編輯 吳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