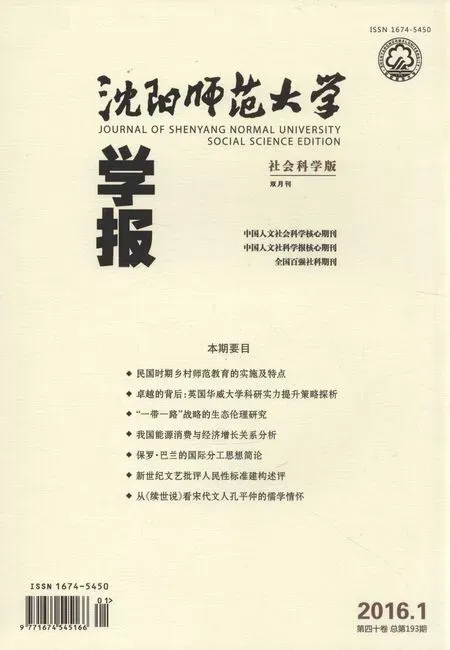走出迷宮的另一條小徑
——由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的讀法達至其隱喻的實質(zhì)
徐可超
(遼寧大學(xué)文學(xué)院,遼寧沈陽110036)
走出迷宮的另一條小徑
——由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的讀法達至其隱喻的實質(zhì)
徐可超
(遼寧大學(xué)文學(xué)院,遼寧沈陽110036)
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這篇創(chuàng)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而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為背景的小說,并非試圖利用“時間”建立一種“宇宙主義”的圖式,也并非一篇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作品,而是采用隱喻、反諷等一系列藝術(shù)手段,傳達了作者對于當(dāng)時社會歷史的反思:一方面精煉地呈現(xiàn)了那段真實的歷史,并探究了造成這種歷史的政治、種族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以對真實歷史的呈現(xiàn),諷刺、揭露和批判了某些脫離現(xiàn)實的文化史的虛假與悖謬。
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隱喻;反諷;歷史
譯成中文之后只不過7 000余字的這樣一篇小說,本來應(yīng)該相當(dāng)簡單,但又確實令人迷惑。之所以會令人迷惑,也許只不過是因為它恰如其名,是“小徑分岔的花園”,而我們一直跟隨著其中的敘述者走上了其中的一條岔路,從來沒有去到另外一條岔路上嘗試一下。
一、文本的一種特殊讀法
博爾赫斯的這篇小說我們已經(jīng)讀了不止一遍,那么這一遍不妨從這里開始:
“設(shè)一個謎底是‘棋’的謎語時,謎面唯一不準(zhǔn)用的字是什么?”我想一會兒后說:
“‘棋’字。”
“一點不錯,”艾伯特說。“小徑分岔的花園是一個龐大的謎語,或者是寓言故事,謎底是時間;這一隱秘的原因不允許手稿中出現(xiàn)‘時間’這個詞。自始至終刪掉一個詞,采用笨拙的隱喻、明顯的迂回,也許是挑明謎語的最好辦法。……”
二、文本的第一敘述層次
首先,我們對《小徑》的結(jié)構(gòu)做一“整體觀”,小說家佛斯特“從繪畫中借一個用語稱之為‘圖式’”[1]。這篇小說分成三個敘述層次,因此其“圖式”就像一顆蛋之有殼、清與黃。蛋殼薄硬,小說最外那個敘述層次亦如之,簡短而干脆:某位“隱蔽的敘述者”直截了當(dāng)?shù)刭|(zhì)疑“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zhàn)爭史》”對一次歷史事件的解釋不當(dāng),其依據(jù)是“青島大學(xué)前英語教師余準(zhǔn)博士的證言”,旋即列出證言,而小說切入到下一個敘述層次。就像吃蛋時剝掉蛋殼那樣,我們對小說的第一個敘述層次不會留意,以為它在作品中的功用不過是引出故事以及造成某種“真實的幻覺”。而且它采用的是科學(xué)化、邏輯化的語言,這種語言被小說家馬原稱為“通過式的”[2],也就是說,我們會迅速理解并通過這種語言而不會駐留于其中。然而,如果我們假定《小徑》“采用笨拙的隱喻、明顯的迂回”,就不該輕易放過這個層次,因為我們輕易放過的地方,可能正是“小說家的狡獪”所在。
實際上,《小徑》的第一個敘述層次關(guān)涉著人類社會的一種至關(guān)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即歷史與歷史的書寫。歷史的書寫并非總是對歷史準(zhǔn)確、如實的記錄,往往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觀點、解釋,而這種觀點、解釋又總是由于主觀或客觀的原因而與實際的歷史不相符合,正如利德爾·哈特上尉不知有意還是無意地遺漏了一條關(guān)鍵的“證言”,因此把造成“十三個英國師(有一千四百門大炮支援)對塞爾—蒙托邦防線的進攻原定于1916年7月24日發(fā)動,后來推遲到29日上午”的原因,解釋為一場“滂沱大雨”。然而那條證言就完全真實可靠嗎?也未盡然,因為不僅“證言記錄缺了前兩頁”,而且雖“由本人簽名核實”,卻經(jīng)過“記錄、復(fù)述”,還被加上了“原編者注”,所以它與其說是“本人”的“證言”,毋寧說是對“證言”的某種觀點、解釋。
三、文本的第二敘述層次
《小徑》第二個敘述層次的“明顯”特征,就是它好似一篇懸疑小說。這又容易使得我們過于關(guān)注它的形式,而忘記了這篇小說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以及我們研究文學(xué)作品時所習(xí)慣采用的社會歷史方法。尤其這一層次的敘述者與主人公是一位本該疏離于故事背景之外的中國人,這更會加重我們對于作品之為“玄幻”的想象。然而,如果我們意識到小說“采用笨拙的隱喻、明顯的迂回”這一點,就不該忘掉它寫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講述的又是與之相隔不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發(fā)生的一個插曲。
作為一篇懸疑小說,《小徑》著實處處顯得相當(dāng)“笨拙”。比如,小說寫到余準(zhǔn)的“計劃已考慮成熟。電話號碼簿給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報傳出去”,這個計劃是什么?這個人的名字是什么?其實對于一篇余準(zhǔn)被捕后的供詞來說,已經(jīng)是不必保守的秘密,然而作者卻又固執(zhí)地在這里替他保守著秘密。也就是說,作者“非法”地扣押了一些信息,沒有把本該公之于眾的情況公之于眾,制造出一個欺騙讀者的“假的懸念”,而這種“假的懸念”是一般懸疑小說家都不屑為之的。如果我們熟識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就有理由把《小徑》當(dāng)成一篇非常業(yè)余的懸疑小說。然而恰是這類“笨拙”在時時提示我們,作者之意不在“懸疑”,而在乎“隱喻”之間也。對于隱喻,我們?nèi)菀追赶碌囊粋€錯誤,就是以為在其背后應(yīng)當(dāng)是某種玄奧的哲理,豈不知它的對象也可以是社會的現(xiàn)實。
然而,余準(zhǔn)的行為似乎處處不合邏輯。他是“青島大學(xué)前英語教師”,卻在英國為德國做間諜工作。作為一名間諜,他非常業(yè)余,這從他臨事之際會“可笑地鎖上門”“胡思亂想”“又恨又怕”“毫無必要地悄悄起來”“不由自主地檢查一下口袋里的物品,也許僅僅是為了證實自己毫無辦法”,一封信“看后決定立即銷毀但是沒有銷毀”“可笑地拿起槍,在手里掂掂,替自己壯膽”等種種表現(xiàn),可以看得出來。職業(yè)間諜如余準(zhǔn)的對立方馬登上校,“作為一個聽命于英國的愛爾蘭人,他有辦事不熱心甚至叛賣的嫌疑”,而余準(zhǔn)這名業(yè)余間諜卻對自己的工作十分負責(zé)和投入,為了把他掌握的“準(zhǔn)備轟擊昂克萊的英國炮隊所在地的名字”傳達到德國,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來冒險。難道他并不珍視自己的生命?并非如此,他在被捕后的證言中說:
這一天既無預(yù)感又無征兆,成了我大劫難逃的死日,簡直難以置信。雖然我父親已經(jīng)去世,雖然我小時候在海豐一個對稱的花園里待過,難道我現(xiàn)在也得死去?隨后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頭上了。多少年來平平靜靜,現(xiàn)在卻出了事;天空、陸地和海洋人數(shù)千千萬萬,真出事的時候出在我頭上……
這表明當(dāng)時他千思萬慮也找不出死亡會落到自己頭上的理由,也就是說,他認(rèn)為自己還不該去死,也并不情愿去死。但是,在他打電話給同伙魯納伯格卻是馬登接了電話時,就已經(jīng)知道:
這意味著我們的全部辛勞付諸東流,我們的生命也到了盡頭——但是這一點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來如此。
這表明在他看來,他從事的工作更為重要,相對來說生命就成了次要的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了使得他們的全部辛勞不至付諸東流,他甘愿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挽救。一個中國人,不遠萬里來到英國,把德國的戰(zhàn)爭成敗當(dāng)作他自己的事業(yè),這是什么精神?其中緣由,也就是余準(zhǔn)行為的動機、邏輯,卻被“原編者”或者小說第一層次的“隱蔽的敘述者”用兩三串省略號就給刪除了。然而在歷史當(dāng)中畢竟還會留存一些無法被人刪除的東西,可以作為我們探明真相的線索:余準(zhǔn)是一個聽命于德國的中國人,無獨有偶,其對手馬登是“一個聽命于英國的愛爾蘭人”,這就不難使我們注意到“種族”與“國家”這兩個既相區(qū)別又相聯(lián)系的概念,進而發(fā)現(xiàn),余準(zhǔn)的行為不只是一種個人的行為,也是某種種族的、國家的行為,也就是說,在余準(zhǔn)的個人行為背后又隱伏著種族性、國家性的原因。
從“我是個怯懦的人”開始,小說的被敘述時間出現(xiàn)了很大幅度的跳躍,也就是從余準(zhǔn)的計劃一形成,跳至這個計劃實施之后。這個時候,余準(zhǔn)之“后我”反觀“前我”,對自己的行為有了較為清楚的認(rèn)識。所謂的“怯懦”不僅是余準(zhǔn)的個人性格使然,也是出于他的種族自卑感。他又說:“我認(rèn)識一個英國人”,這個人就是“中國通”艾伯特,他對艾伯特的評價是“一個謙遜的人”,因為在他看來,英國人艾伯特“并不低于歌德”“就像歌德”——這里的“歌德”當(dāng)然不是實際的歌德,而是他所仰視的德國種族的象征——但是艾伯特不像他的德國頭頭那樣“瞧不起我這個種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匯集的無數(shù)先輩”。事后的余準(zhǔn)意識到:“我才不關(guān)心一個使我墮落成為間諜的野蠻的國家呢”,但卻已經(jīng)為這個野蠻的“國家”完成了一件“窮兇極惡的事情”,目的不過是為了要向他的頭頭“證明一個黃種人能夠拯救他的軍隊”。由此可見,一種非理性的種族自卑情緒是如何被卑視它的種族情緒及其國家機器所煽動和利用的。其實,那種卑視其他種族的情緒又何嘗不是出于一種種族自卑情緒呢?這種種族自卑情緒一旦被某種國家機器所煽動與利用——就像納粹主義所主張的那樣:國家是實現(xiàn)種族意志的工具——就會成為極其可怕的勢力。這種勢力既然把余準(zhǔn)這樣一個其外圍的、反動的人裹挾進去,其內(nèi)部的、順動的人更是可想而知,不難想見這種勢力在當(dāng)時德國之強大,而戰(zhàn)爭必然由此而起。
余準(zhǔn)這個“怯懦的人”,卻能完成一項鋌而走險的計劃,貌似純屬“僥幸”:他恰好登上了八點五十分的列車,馬登又恰好在已經(jīng)發(fā)車時才趕到車站,而下一趟火車要等九點半才會發(fā)車,這樣就為他贏得了四十分鐘“時間”。然而在這種偶然性中又包含著必然性,因為承載和推動他的計劃的其實是一種業(yè)已形成的勢力,他登上的那列火車就是這種勢力的象征:
我在幾個車廂看看:有幾個農(nóng)民,一個服喪的婦女,一個專心致志在看塔西佗的《編年史》的青年,一個顯得很高興的士兵。
哲學(xué)家、心理學(xué)家艾瑞克·弗羅姆有一種觀點,大概可以用作這列火車的注腳:“父親和母親兩原則之間有一個適當(dāng)?shù)钠胶馐且粋€民族神經(jīng)健全的先決條件。有些民族夸大了父親原則,于是變成了好斗、不寬容和跋扈專權(quán)。相反,卑躬屈節(jié)地篤信母親原則則使一個民族變成孤立主義的、地方主義的和過分‘愛國的’,這種民族變得在他們所居住的土地上生了根,并象個人自愛一樣發(fā)展了孤芳自賞的傾向。結(jié)果是成為一種表現(xiàn)為種族中心主義和排外的可笑的民族主義。納粹黨人‘血與土地’的沙文主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3]“幾個農(nóng)民”是否“在他們所居住的土地上生了根”?“一個服喪的婦女”是否代表失衡的“母親原則”?“塔西佗的《編年史》”是否就像“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zhàn)爭史》”?那個“士兵”又為什么“顯得很高興”?所以說車上的這些乘客恐怕并非作者隨意的幾筆點染,而如讖語一般透露了余準(zhǔn)的命運。如果說這樣的解釋過于牽強附會的話,那么我們也可以只把它看成對戰(zhàn)時景況的一幅速寫。在這種景況當(dāng)中,余準(zhǔn)也必然可以達到他的目的,所以他才會把自己的計劃看成“一個誰都不會說是冒險的計劃”,并且說“我怯懦的順利證明我能完成冒險事業(yè)。我從怯懦中汲取了在關(guān)鍵時刻沒有拋棄我的力量”。最終,他通過自己的行為看到了那個時代涌動著的一股惡流,這一惡流把他的命運卷入了歷史的漩渦。
一路左傾,就好像在一個漩渦當(dāng)中,余準(zhǔn)走向了自己的目標(biāo)。
四、文本的第三敘述層次
余準(zhǔn)踏上那條不歸路后,從腳下的路聯(lián)想到“迷宮”,小說開始延伸向下一個敘述層次,即一個“元虛構(gòu)”的故事:
如果我們把余準(zhǔn)的這段敘述與后來艾伯特的“重復(fù)性敘述”加以比較,就會嗅出小說中的那股反諷味道:余準(zhǔn)這位為了“身上匯集的無數(shù)先輩”可以去做可怕事情的人,其實還遠不如一個英國人了解他的祖先;他說“我對迷宮有所了解”,其實卻一無所知。正因為他的無知——作為一位“博士”的無知,對他來說何處不是迷宮呢?
我在英國的樹下思索著那個失落的迷宮:我想象它在一個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動,被稻田埋沒或者淹在水下,我想象它廣闊無比,不僅是一些八角涼亭和通幽曲徑,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國組成……我想象出一個由迷宮組成的迷宮,一個錯綜復(fù)雜、生生不息的迷宮,包羅過去和將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牽涉到別的星球。
的確,如果不了解生活、歷史、宇宙,那么生活中、歷史上、宇宙間到處都是迷宮,而且是“走不出來的迷宮”。
我沉浸在這種虛幻的想象中,忘掉了自己被追捕的處境。在一段不明確的時間里,我覺得自己抽象地領(lǐng)悟了這個世界。
余準(zhǔn)覺得自己領(lǐng)悟了這個世界,其實正好相反,因為他丟開了自己現(xiàn)實的處境,企圖在“虛幻的想象中”“抽象地”把握世界,那么世界對于他就會益發(fā)抽象、虛幻而不可知。
對于余準(zhǔn)這位“土博士”,作者顯然采取了反諷的態(tài)度,對于艾伯特這位“洋博士”,也同樣并未筆下留情。當(dāng)余準(zhǔn)站在冷落寂寞的“一扇生銹的大鐵門前”正不知如何進退,恰逢一似得道高人的艾伯特出來迎接貴客。盡管來者并非艾伯特所期待的中國領(lǐng)事,但卻是花園原主彭的曾孫,恐怕不會過減他的逸興壯思。艾伯特原說請客人參觀“花園”,卻把他帶到了自己的“書房”。書房里的各種擺設(shè)似乎顯示出主人博通古今、融貫中西的造詣,但偏是那個不倫不類的“留聲機上的唱片還在旋轉(zhuǎn)”,可以讓余準(zhǔn)知道他到大門前時聽見的“像火花迸濺似的樂聲”,并非這位高人手揮五弦的“高山流水”。余準(zhǔn)原來或許不明何以“樂聲沒有停止”“然而”一位高人卻手提燈籠飄然而至,此物可以讓他狐疑盡消,卻又引起我們狐疑于“從未付印的明朝第三個皇帝下詔編纂的《永樂大典》的逸卷”的“用黃絹裝訂的手抄本”,以及其他文物的來路與真?zhèn)危骸耙恢磺嚆~鳳凰……一只紅瓷花瓶,還有一只早幾百年的藍瓷,那是我們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帶著這種狐疑,我們也就認(rèn)明了這位“神情有點像神甫,又有點像水手”的艾伯特的本來面目。
后來他告訴我,“在想當(dāng)漢學(xué)家之前”,他在天津當(dāng)過傳教士。
此處非常別扭的是“在想當(dāng)漢學(xué)家之前”句上用了引號,是直接引語,然而緊接的“他在天津當(dāng)過傳教士”句上沒有引號,又是間接引語。直接引語表明引述者真實地照搬了艾伯特的原話;間接引語經(jīng)過了引述者的過濾和揣測,不一定符合艾伯特的原話。更為別扭的是前面又加上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預(yù)敘:“后來他告訴我”。我們知道,馬上艾伯特就會向余準(zhǔn)解釋“迷宮”,接著余準(zhǔn)就會殺掉艾伯特,那么這個“后來”又會在什么時間呢?顯然,作者采取了“字詞反諷”手法,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也就一并增加了這位“贗品”與“舶來品”大師的虛實。在書房里,艾伯特“微笑著打量著”余準(zhǔn),余準(zhǔn)也打量著他:
我剛才說過,他身材很高,輪廓分明,灰眼睛,灰胡子。
然而余準(zhǔn)剛才說過的卻是:“由于光線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臉。”所以說,“灰眼睛,灰胡子”又是一個“笨拙的隱喻”,表明艾伯特對于余準(zhǔn)來說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因此剛才艾伯特引他走向書房的“潮濕的小徑”才會使他覺得同“兒時的記憶一樣”。其實何止對于余準(zhǔn),即便對于我們來說,艾伯特不同樣也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嗎?也就是說,艾伯特是文化領(lǐng)域中的一種“典型”。
我們已經(jīng)假定《小徑》是一則謎語,那么按照“謎語學(xué)”的邏輯來推測,這部名義上的“小說”,實質(zhì)上肯定不是小說,而是形而上的“哲學(xué)”。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形而上的哲學(xué),才能像彭的小說那樣是“無限”的,才能容納比《紅樓夢》更多的人物,才能涵蓋“許多不同的后世,許多不同的時間,衍生不已,枝葉紛披”。在現(xiàn)實中及模仿現(xiàn)實的“所有的虛構(gòu)小說中,每逢一個人面臨幾個不同的選擇時,總是選擇一種可能,排除其他”,只有形而上學(xué)的辯證法,才能“選擇了所有的可能性”。“小說的矛盾就由此而起”,這其實是以“小說”笨拙的隱喻“哲學(xué)”而產(chǎn)生的矛盾。但是似乎作者還是唯恐過于聰明的讀者反而看不出其隱喻的笨拙,所以又借艾伯特之口提示讀者:
這無疑又在“小說”和“哲學(xué)”之間畫了一個彎曲的約等號。如果說艾伯特的科研成就之一是指出迷宮和小說實為一物,那么之二就是指出這部小說“最關(guān)心、最專注的問題”是“深不可測的時間問題”。這種“時間”不同于“牛頓、叔本華”即物理、哲學(xué)意義上的時間范疇,它“沒有同一性和絕對性”,“有無數(shù)系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復(fù)雜的網(wǎng)。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wǎng)絡(luò)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時間里,我們并不存在;在某些時間,有你而沒有我;在另一些時間,有我而沒有你;再有一些時間,你我都存在。”對于這則謎語,除非“歷史”,恐怕我們再也找不出更為合適的謎底。
這個“歷史”也不單是一系列符號、象征、觀念即文化學(xué)意義上的歷史,而是在現(xiàn)實中已經(jīng)發(fā)生、正在發(fā)生及將要發(fā)生的歷史。人們用符號、象征為之命名的歷史圖像和秩序,盡管可以被看做真實的歷史的反映,但它反映的絕非歷史的真實。原因有二:一是歷史由于人的觀念的滲透與操縱而改變了意義;二是歷史經(jīng)過一再抽象而僅剩概念,正如海登·懷特所說,歷史就像小說一樣經(jīng)過了話語的虛構(gòu)。人類歷史的規(guī)律,被彭抽象為“小徑分岔的花園”,又被艾伯特闡釋為“時間”,而在他們的概括與闡釋中,以偽裝的形式出現(xiàn)而掩飾了其血腥的,其實卻是一種鼓動仇殺與戰(zhàn)爭的“英雄主義”觀念:
比如說,方君有個秘密;一個陌生人找上門來;方君決心殺掉他。很自然,有幾個可能的結(jié)局:方君可能殺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殺死,兩人可能都安然無恙,也可能都死,等等。
其一,一支軍隊翻越荒山投入戰(zhàn)斗;困苦萬狀的山地行軍使他們不惜生命,因而輕而易舉地打了勝仗;其二,同一支軍隊穿過一座正在歡宴的宮殿,興高采烈的戰(zhàn)斗像是宴會的繼續(xù),他們也奪得了勝利。
五、結(jié)語
博爾赫斯在其《虛構(gòu)集》的序言中說,《小徑》“是偵探小說;讀者看到一樁罪行的實施過程和全部準(zhǔn)備工作,在最后一段之前,對作案的目的也許有所覺察,但不一定理解。”然而這篇偵探小說與一般偵探小說大不同的是,其中沒有偵探,而且罪犯及其整個犯罪過程也被從頭到尾一覽無余地呈現(xiàn)出來。那么作者的言外之意,也許就是期望讀者自己去做其中的偵探,偵探的任務(wù)不是去發(fā)現(xiàn)誰是罪犯及其犯罪的目的,而是去理解這樁罪行背后的社會歷史原因。博爾赫斯曾把他的天堂設(shè)想為圖書館的模樣,也曾自嘲地說:“……不幸,世界是現(xiàn)實的;而我,不幸地卻是博爾赫斯。”[4]他沉迷于文化這座迷宮花園,深諳其中的奧秘,也始終關(guān)注外邊的現(xiàn)實,具有鮮明而堅定的民主主義政治立場。他把讀者引入一座花園,目的卻是把他們帶出這座迷宮。
[1]佛斯特.小說面面觀[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125-128.
[2]馬原.虛構(gòu)之刀[M].沈陽:春風(fēng)文藝出版社,2001:85.
[3]愛·麥·伯恩斯.當(dāng)代世界政治理論[M]//曾炳鈞,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3:378.
[4]林一安.走近本真的博爾赫斯:總序[M].博爾赫斯全集·小說卷.王永年,陳泉,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6:11.
Another Path Out of the Labyrinth:Guid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Xu Kech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036)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by Jorge Luis Borges,a short story on the background of World War I and written during World War II was not trying to use time to establish a pattern of the theory of the universe,or just a detective story,but applied a series of artistic strategies like metaphor and irony to convey the author’s reflection to social history:on the one hand it presented the real history of that time and explored the political causes of history;on the other hand it conveyed the satire and criticism about the hypocrisy and paradox of certain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eality.
Jorge Luis Borges;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metaphor;irony;history
I106.5
A
1674-5450(2016)01-0107-05
【責(zé)任編輯 楊抱樸】
2015-08-13
遼寧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立項課題(2015lslktwx-27)
徐可超,男,遼寧大連人,遼寧大學(xué)副教授,文學(xué)博士,主要從事文藝學(xué)與中國古代文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