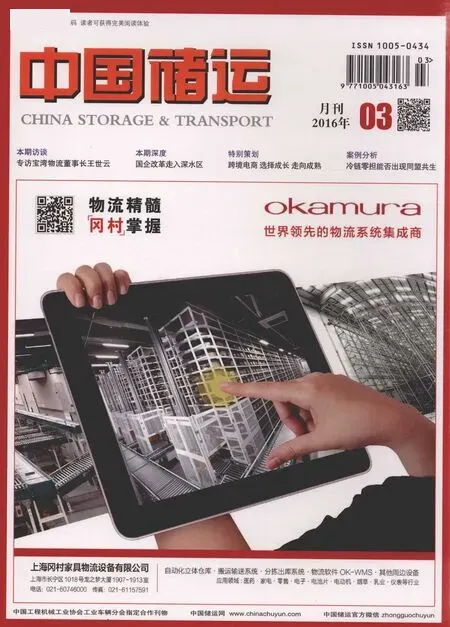自由、民主、文化共享則有光
文/李煒光
?
自由、民主、文化共享則有光
文/李煒光
今年是周有光先生誕辰111周年,上周我有幸到周有光先生的母校去了一趟。先生的母校在上海,民國時代叫“圣約翰大學”,現在的名字叫“華東政法大學”。
圣約翰歷史悠久,建校130多年了,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教會大學之一。先生回憶自己的母校時曾說:“圣約翰大學雖然是教會辦的,但并不強迫學生信教,很民主,圖書館里什么書都有。”可能是這個原因,這所大學培養出眾多的優秀人才,顧維鈞、宋子文、鄒韜奮,林語堂、張愛玲、貝聿銘、吳宓、榮毅仁等,都是這個學校畢業的。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該校的英文校訓:Light and True,意為“光和真理”。說來也巧,說要有光,這所學校就出了個學生叫周有光。《舊約·創世紀》上說:“神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亞里士多德認為這句話是智慧的象征,因為神創造天地時是默默無語的,他的行動是在黑暗中進行,于是意識到“光”是事物存在本質之一。
只有憑借光的照耀,才能看得見創造的進行。沒有光明,人類就不可能感知物質、事物、世界,就不可能發展社會,發展自己。沒有靈魂和信仰亦被視為暗夜,人類就處于危險之中,而光是用來照亮人心的。
光的存在需要一個光源,它照耀著我們前行的道路。一個人擁有思想和智慧,就像這個光源,影響著他身邊的每一個人。周有光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光源,一生向往光明,把自己感知的光明播撒于世界。
讀過先生的部分文字,我有三個體會:
第一是自由則有光。自由產生于公共權力和個人權利的張力,是站在個人的角度對公共權力的限制和抵抗。它存在的價值,就是為國家權力劃定界限。
先生珍視自由,他說,羅斯福說人類社會有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予貧困和免予恐懼的自由,“現在是五大自由,第五個就是網絡自由,網絡不應該被控制”。先生問道:“全球化時代是透明化的,蘇聯經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們難道害怕透明嗎?”
現代社會中,自由可促進人類社會的創新,是一種基于人性的基本的善,是發展的首要價值,人類須臾不可失去自由。沒有互聯網自由,謊言就可能成為集體意志,野蠻就可能被賦予合法性。先生英明。
第二個體會是民主則有光。先生把民主看作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從專制到民主是自然的發展,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誰也不能違背這個規律。”先生說,凡是專制都會阻礙社會發展,在民主問題上,中國是一個落后的國家,一點也不先進。
先生是對的。目前世界上接受民主的國家越來越多,國家領導人經自由的、競爭性的差額選舉方式產生的國家已達到三分之二以上。只有民主才能代表文明,專制統治必將被民主政治所代替。中國不能背向文明而行。
第三點是共享文化則有光。先生反對把文化分為東方和西方兩部分,認為“文化一定是多種文化的混合。單元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就不能繼續發展了,要有外面的文化來嫁接。現在世界上各個地域和地區的全球化加速融合,文化也在相互融通,“大致從18世紀開始,不知不覺發展成為不分地區的國際現代公共文化,由世界各國共創、共有、共享”。
先生批評了季羨林提出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之論,說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傳到中國來了。先生表示不參加這些討論,他說文化流動不是忽東忽西、輪流做莊,而是高處流向低處、落后追趕先進的關系。“河東河西”論是由“自卑綜錯”變成“自尊綜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壯膽”。有研究認為,人確實是被制造出來的。如果真是這樣,周有光先生一定是其中制作最精良的一個,他長壽至今111歲證明了這一點。
資中筠先生說,人老了一定要退出舞臺,年輕人才是創造這個社會的主力,我不完全同意。中國的現狀是老人家們還不能把啟蒙的重擔卸下去,因為欺騙和謊言還占據著人們的心靈,中青年的知識分子們出于種種顧慮,還承擔不起這個社會責任。
記得年輕時讀過高爾基的《伊席吉爾婆婆》,里面有一個名叫丹珂的英雄帶領人們穿過幽暗森林來到美麗草原的故事。先生們,你們就像高舉火把的丹珂那樣走在前面,后面黑壓壓的一大群人跟隨在你們身后。如果你們的火把熄滅了,我們將不知道走向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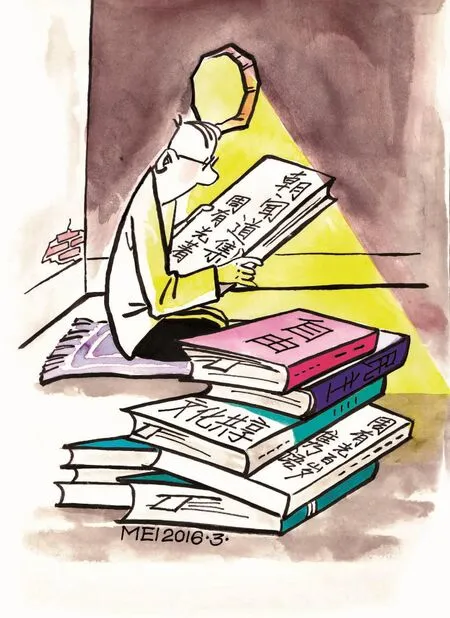
鑿壁借光勤讀書 暗境育出心明人 梅逢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