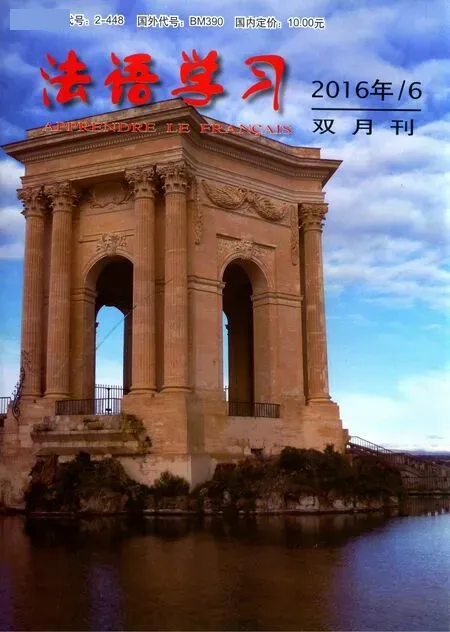從《安德烈·瓦爾特筆記》看《圣經》對紀德寫作的影響
● 西安外國語大學 曹文波
從《安德烈·瓦爾特筆記》看《圣經》對紀德寫作的影響
● 西安外國語大學 曹文波
本文通過介紹法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宗教背景,對安德烈·紀德的宗教態度與特征進行梳理和總結,并通過閱讀《安德烈·瓦爾特筆記》,分析《圣經》對紀德寫作風格的影響。
安德烈·瓦爾特筆記,圣經,紀德
安德烈·紀德,這位20世紀初法國文壇的精神領袖,以其作品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人格的復雜性以及所處的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在文學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作為公眾人物的紀德,與19、20世紀之交的許多重要文學思潮和社會活動都有過密切的關系;而作為藝術家,紀德幾十年中在文學園地上辛勤耕耘,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縱觀紀德的作品,我們可以注意到,從最初的《安德烈·瓦爾特筆記》到最終的《忒修斯》,紀德的創作有兩個重要的源泉,一是異教文化,主要是古希臘羅馬神話;二是基督教文化,主要是《圣經》新舊約全書,這兩種看似互不相容的文化在紀德的生命中各自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家庭的影響和所受的教育,基督教問題幾乎貫穿了紀德的一生。在濃厚的新教氛圍中長大的紀德有很重的宗教情結。在本文中,我們將透過《安德烈·瓦爾特筆記》對《圣經》及基督教文化在紀德藝術生命中的重要地位進行梳理和歸納。
一、時代與個人:紀德宗教情結的產生和初步發展
安德烈·紀德出生在一個富有的資產者家庭里,父母親都是新教徒,但母親祖上曾經是天主教徒。紀德常常強調雙重的家庭、地域乃至宗教背景在自己看似充滿矛盾和沖突的思想體系中的決定性作用,他是兩種血緣、兩種地域、兩種信仰的結晶,但這雙重的宗教背景只有在家族歷史溯源時才存在。實際上,紀德的外祖父一代已經從天主教改宗,到了紀德,家庭中已經充滿純粹的新教氣氛了。父親早逝后,他被虔誠的母親悉心培育,受到了嚴格的宗教訓練,包括對《圣經》文本的學習和對各種清規戒律的領受。這種濃厚的新教氛圍決定了后來紀德對《圣經》、尤其是對四福音書文本終生不倦的偏愛。耶穌基督的形象很早就在紀德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圣經》的故事和文字也成為他后來在作品中最愛援引的來源之一。
《安德烈·瓦爾特筆記》是紀德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也是他所受新教教育的第一次集中體現。作品從安德烈·瓦爾特的視角出發,通過主人公在愛情面前的苦悶和彷徨,探討了靈魂與肉體的分離、精神至上、對上帝的虔誠信仰等一系列問題。全書以安德烈·瓦爾特對表姐艾瑪紐埃爾無望的愛情為主線,既反映了紀德本人的情感危機,又體現了作者對愛情、信仰甚至寫作本身的思考,作品中傾注了強烈的個人感情,不乏神秘主義的呼號與感嘆,想要通過與上帝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來傳達內心的祈禱,他在其作品中呼求:“主啊,饒恕我,我還是個孩子,一個迷失在背信路上的小孩:哦,主!我不要瘋狂!”(紀德,2014:47)再如“上帝啊!我向你尋求庇護,我從來不會迷失自己!但是你啊,我的上帝!直到何時?你丟下我要到何時?征戰的路上感受不到你在我身邊要到何時?……然后呢?……該如何結束,這戰爭?……”(紀德,2014:80)
作為紀德初涉文壇的作品,《安德烈·瓦爾特筆記》可以看作是作者充滿焦慮的青年時代的寫照。紀德對這部處女作并不是很滿意,在1930年的再版前言中,他甚至說:“總之,我再次翻開《安德烈·瓦爾特筆記》時總感到痛苦,甚至屈辱。”(紀德,2014:1)但是在寫作這本書時,他是懷著一種虔誠信念的,認為自己在同兩個最可恨的敵人作斗爭,兩個敵人分別是肉欲和批判精神。盡管紀德告訴讀者那時不會寫作:“那個年紀,我還不懂寫作,更確切地說,或許是因為我感到自身有一些新鮮事兒需要一吐為快,我便摸索上路。”(紀德,2014:1)這部宗教氣氛濃烈的抒情作品還是起到了宣泄、凈化的作用:紀德通過描寫自己的焦慮而擺脫了這種焦慮。這種通過內心情感的外化和具象化來超越自身的方法,從此成為紀德創作的一個重要原則。
二、《安德烈·瓦爾特筆記》:內心世界的真實表達
紀德母親的生長環境培養了她清教徒式的資產階級道德觀,在她的觀念里,性就是魔鬼,這種觀念時刻存在,體現在講話所用的每一個詞、無意識的手勢、無意識的動作及書籍中,特別是書中。朱莉葉認為,在詩歌美好詞語的外衣下,隱藏著不可告人的淫穢糟粕。紀德受到這種禁欲主義思想影響,反映在其生活和文學創作中。
1882年底,紀德去舅舅埃米爾·隆多家時對表姐瑪德萊娜·隆多萌生愛意,并為她寫下《安德烈·瓦爾特筆記》。“每晚,我的靈魂飛到你身邊,飛到它愛著的你身邊。我的靈魂像輕盈的小鳥,落到你的唇上。在柔美的顫栗中,你的雙唇含笑而啟。一聲飽含肉欲的叫喊,我的靈魂呼喚著你的靈魂。我們的靈魂如同兩片燃燒的火焰攪在一起,合為一體,撲閃著翅膀,伴著迸發的激情飛向和諧的遠方。”(紀德,2014:51)禁欲主義的道德方式讓紀德飽受折磨,他既要捍衛自己的信仰,對肉欲加以控制,又要經受肉欲的反抗,內心感受到對自由的需要。面對這種矛盾的局面,紀德開始懷疑導致如此結果的基督教的道德,但并未因此懷疑上帝的存在。他認為出現謬誤的是人,如其母親所曲解的基督教道德,他始終相信上帝是提倡人類享受快樂和自由的,而基督教的道德卻使人經受痛苦,這與《圣經》真理是背道而馳的。
19世紀后期西方工業文明日益發達,在給人們帶來豐富的物質產品的同時,也給他們造成精神家園的缺失。曾經以理性和自制為特征的社會制度和道德規范已不再適應現代人的生活狀況,而個體的差異性感受和價值偏好則成為這種公共倫理極力壓制的對象。西方人從幾個世紀前就開始爭取人權和個性解放,然而,人們在最大限度地享受到物質文明成果之際,卻又漸漸感受到精神的空虛和孤獨,感受到靈魂無所歸依的痛苦。世紀之交,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劇烈角逐給人們的心靈帶來強烈的震撼。傳統文化講究秩序,而現代文化則弘揚自我,注重情感,它們的發展不平衡的狀態給人們造成精神的困惑。人的內心世界成為這兩種文化角逐的戰場,反映在社會生活中,就是人們感到理想遙不可及,前途迷茫,退亦憂,進亦憂,即使作出很大犧牲,也不能將傳統與現代統一起來。人們不能離開追求高尚精神的終極關懷,也不能沒有靈魂的港灣和精神的棲息地。基督教指引著對上帝和天國的信仰,使西方人在漫長歲月中找到人生的最高目標,相信只有恪守基督教信條,用高尚的道德觀念約束自己,無條件地奉獻身心于上帝,才能救贖自己的靈魂,重返無比美好的天國世界。新世紀開始后,雖然上帝在一些人心目中退隱了,這卻不能阻止一批有責任心的作家在作品中重塑上帝的形象和精神的信仰,以求找到人類靈魂的家園。紀德也不例外,正是在對道德規范的質疑中開始了尋找自我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創作實踐。
然而,無論紀德的經歷如何,他仍在努力尋找和追求美麗豐富的精神家園。靈魂與肉欲的斗爭之美,不勝猶然。無望之戰最為壯美,勝利之滋味已享受于英勇無畏嘗試之時。靈魂必須反抗外物的束縛,將肉體所受的傷害置之度外,因為雖然肉體受辱而靈魂卻可以得勝。肉體淺唱低吟,但他終將被精神的火焰所征服。紀德此番斗爭的勇氣和力量來自《圣經》,如同雅各與天使征戰,在意志與行為的征戰中,意志已經占得上風,因為獨肉體有一死,而靈魂之樹常青。
三、《圣經》:生活與藝術的橋梁
張若名曾經這樣評價紀德:“紀德的作品是他生活體驗的戲劇性象征,撇開他的生活,就將會失去完整的意義。它雖是一種純象征,也一點都不會描述所過的生活;更確切地說,它再現了紀德的內在人格,這樣的內在人格由他的經歷結晶而成。”(張若名,1997:72)
《圣經》一直伴隨著紀德的成長,然而母親嚴厲的教育及紀德身體內部的本能沖動時時沖撞他的思想,因此紀德的心靈常常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母親對紀德進行的資產階級新教教育時時頑強地反映出來,另一方面,紀德通過反抗母親的要求來保持自己的天性。因此,寫作逐漸成了紀德發自內心深處的根本性需要。一方面,紀德需要用寫作來調整自己心中兩種精神力量之間的平衡,另一方面,寫作這個平臺給紀德開拓了更加廣闊的思維空間。同時,寫作還是紀德對自己往事的一種藝術記憶,這種記憶“對于個體而言,記憶的救贖力量并不在于將記憶的內容轉移到某個外在對象上,而在于記憶由于以上帝之國為基礎,它在一方面是屬于個體的,但另一方面又對個體有著一種‘越出’的屬性。”(莫運平, 2007:46)
豐富而獨特的生活經驗為紀德提供了寫作的精神動力,《圣經》則架起了紀德生活與藝術之間的橋梁。紀德閱讀《圣經》是為了尋找活著的理由和意義,寫作則是他表達思想的一種生活方式,旅行又是他一生不斷追求自我的一種途徑,特別是北部非洲的大自然,既賦予了他快樂和自由的秉性,又為他的創作提供了靈感。可以說,閱讀《圣經》和寫作既是他的一種生活狀態和方式,又是對自我靈魂進行拯救的方式。張若名又說:“二十歲時,紀德創建了藝術的宗教,……除信仰外,雖然憂慮和自豪也能激起他的熱忱,卻不能滿足他創建永生的欲望。唯獨他的信仰中充滿了對崇高的膜拜,會迫使他走上永生的道路,如果他不甘心蔑視自我的話,因為他的宗教情感變成了一種藝術情感。”(張若名,1997:16)
紀德在閱讀《圣經》的過程中“獲得的激情不單單是宗教方面的,也不像《伊利亞特》和《悲劇三部曲》賦予我的激情那樣,純粹是文學方面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我思想上藝術和宗教是虔誠地結合在一起的。二者如此和諧地融合一起,令我非常著迷”。(紀德,2005:139)可見,《圣經》對紀德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宗教方面,更重要的是紀德將藝術和宗教虔誠地結合在一起,建立了一種他所需要的和諧關系,并且領略到了迷狂至極的滋味。
紀德把自己從《圣經》中學到的信、望、愛用藝術的方式堅持了一生。當紀德把寫作變成終生的主宰和一種生活目標時,紀德的生活方式就深深影響了他創作的取材方法,取材的方法又決定了他在作品中的敘寫風格和主題表達。生活、宗教、寫作這三個方面的表現,被紀德隱藏在心里的《圣經》情結所統轄。在紀德那里,《圣經》與生存互為需要,寫作與《圣經》互為動力,紀德一生的創作都離不開《圣經》,他時而引用《圣經》原文,時而從《圣經》中取材,時而從《圣經》中汲取思想營養。但“至于作者為什么要采取一種態度去寫某一部小說,他自己也不能完全自由。因為他的個性與他的過去經驗,早已指示給他一種觀看人生的態度。而他的使命,即在承認這種看法,而且能自圓其說,找到許多合理的條件,使他所看見的人生表現在作品里,變得更為真切,更為堅固合理。”(張若名,1997:111)紀德總是在《圣經》中尋找自己所要的東西,來創作自己的作品,然后再冷靜地退出,慢慢地去體驗和享受自己創作出來的那種理想的生活狀態。由此可見,《圣經》不僅是紀德創作的思想和題材來源,而且是他彌補自己生活中不足的一種方式。紀德把自己對自由與愛情、靈與肉、同性戀、人與上帝、人與社會、倫理與道德等問題與《圣經》緊密地聯系起來,通過改革和改良,把對生活的熱情變為藝術的熱情,并最終變成了自己對“人與人性”和“人與上帝”關系的思考。
結語
呂西安·戈德曼在《隱蔽的上帝》中曾說:“一個作者的著作實際上不過是他的行為的一部分,而一個作者總是由一種極其復雜的生理和心理結構來決定,在一個人的一生中,這種結構遠遠不是始終如一和恒定不變的。”(戈德曼,1998:10)紀德閱讀《福音書》,不是為了宣揚信仰,而是從基督教教義中找到他一直尋覓的東西:不帶宗教的基督教理想,沒有教條的倫理。他寫作只是為了傳播一種自由和本真的存在,而不是消滅矛盾。他的作品所追求的是在正視人類本性的前提下,在自身內部力量的矛盾與平衡中找回自身的法則。紀德創立了自己的宗教和《圣經》,并且不斷地改變自己,隨時更新它們。朱靜曾于《紀德傳》中這樣說道:“紀德孜孜不倦地追求細膩的、富于想象力的、不斷更新的文學創作,他的作品與嘩眾取寵的暢銷書不能同日而語……紀德不善于模仿別人,別人也模仿不了紀德。紀德從不媚俗,他要走自己的路,也許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寫作態度,造就了后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朱靜,1997:73)紀德的一生和全部作品,不啻為人在尋覓自我的過程中一場不間斷的對話。
?
安德烈·紀德[法],《安德烈·瓦爾特筆記》[M](宋敏生、姜俊欽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
安德烈·紀德[法],《如果種子不死》[M](羅國林譯),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2005.
呂西安·戈德曼[法],《隱蔽的上帝》[M](蔡鴻濱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莫運平,《基督教文化與西方文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張若名,《紀德的態度》[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朱靜,《紀德傳》[M],臺北:臺灣業強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