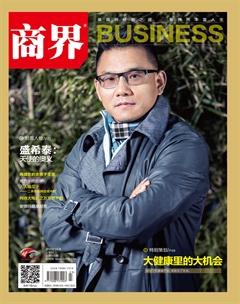為什么中國人收入差距會持續擴大?
新型產業、金融行業跟傳統農業和工業的收入差距,并非因其貪婪,更多的是由于這些現代產業具有全新特征。以騰訊公司為例,2015年其營業收入超過900億元,按照騰訊2.5萬名員工計算,人均創收達360萬元。相比之下,2015年中國農業總產值約為6萬億元,按3億農民來看,人均創收僅有2萬元。這樣一來,農民收入遠低于騰訊員工就不足為奇了。
為什么騰訊的創收能力超過農業這么多?關鍵原因在于:農業跟騰訊的經濟特征完全不同,兩者的產出函數不一樣。
農業的產出與投入之間有極強的線性關系,這限制了農民的創收空間。如果種一畝地需要花100小時勞動、200元種子和肥料成本,最終產出100千克糧食,那么,要生產1 000千克糧食,就需要種10畝地,投入1 000小時勞動、2 000元種子和肥料錢;為了生產1萬千克糧食,就需要種100畝地、花1萬小時。不能因為這畝地種好了,下一畝地就可以少花勞動時間或肥料成本。每畝地所需要的勞動和成本投入是相互獨立的,這也使得農業生產難有規模效應。
而騰訊的產出和投入之間的關系不僅是非線性的,甚至沒有太大關系。在QQ空間里,一頂虛擬帽子的設計可能要幾個設計師與程序員花幾天時間,可一旦設計好了,一頂帽子賣一塊錢,賣100萬頂就創收100萬元。由于虛擬帽子的銷售是電子記賬,每賣一頂并不需要重新制造。所以,騰訊賣一億頂虛擬帽子跟賣一萬頂在成本上幾乎沒有差別,但收入卻有天壤之別。以此類推,騰訊的虛擬衣服、虛擬裝飾、虛擬家具等都是如此。
金融服務業、基金管理行業的產出與投入關系跟騰訊也有類似特點。一家對沖基金或者私人股權基金公司可能只有15~20人,卻可以管理2億美元或者20億美元基金。因為,他們一旦決定投一只股票,投10萬美元還是投1 000萬美元對他們來說需要做的工作、花的時間完全一樣,運營成本也基本接近,利潤卻能相差十倍甚至更多。
實際上,產出是投入的線性函數不只是農業的特征,許多傳統行業也是如此。制造業企業的收入和投入之間不是純線性關系,因為它們可以通過新技術提高生產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占比,也可以利用規模優勢迫使供應商降價。但是,制造業最終離不開每件產品都需要部件、配件、人工成本投入的事實。以汽車制造為例,雖然制造商可以壓低發動機、車身、剎車、輪胎等部件的進貨價格,但每一輛汽車都必須用上這些部件,其邊際成本不可能降到零。
也就是說,雖然汽車制造商可以通過技術革新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但每輛汽車的邊際成本降低到一定水平后,制造商的收入和投入之間依然會趨向于一種線性關系,增長就受到新的約束。因此,他們的收入水平難以跟新型產業相提并論。
姚明退役之前,平均每場球賽的收入約為25萬美元,這相當于5個美國家庭的年收入、近30個中國家庭的年收入。對于習慣于用勞動價值論的人來說,打一場籃球賽賺25萬美元,怎么也難以從勞動時間和強度來解釋。
今天姚明打一場球,跟70年前的籃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時間、消耗的能量、力氣應該差不多,即使有差別也不會是數量級的。但在收入方面,姚明可能是70年前球星的數百倍,甚至一兩千倍。
——最大的差別在于:70年前,一場籃球賽只有現場觀眾享受,即使門票貴到200美元一張,有1萬名觀眾,主辦方也只能得到200萬美元收入,除此之外主辦方并沒有其他收入;可是,今天的籃球賽與其說是給現場球迷打的,不如說是給場外數以億計的全世界觀眾打的——這些觀眾既可以通過電視、互聯網觀看實況,也可以在比賽之后通過互聯網下載觀看。
電視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經濟、體育打破了國界,產生了受眾數量級的巨大變化,導致同樣一場球賽、同樣多的勞動付出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價值。換言之,現代技術和全球化使“贏者通吃”更上一層樓。
唱片、錄音帶、影碟的出現也使歌星、影星一下子全球化了。粉絲買唱片只買全國明星、世界明星的,看電影也只看國際大片。有了互聯網之后,演藝界的“贏者通吃”局面更被推到全新高度,世界級明星和普通明星之間的機會鴻溝、收入鴻溝被大大拓寬了。
交通技術、媒體技術改變了人類生活,不僅豐富了我們的所見所聞,拓展了人生閱歷,而且大大提升了生產速度和效率。新型交通使“日理萬機”不再是夸張比喻,而是我們每天的真實生活。但也造成“贏者通吃”被不斷延伸,先是地區內的“贏者通吃”,后是省市范圍內的“贏者通吃”,最后是全國范圍乃至全球范圍的“贏者通吃”。與之相應的是,贏者與非贏者間的收入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在鐵路、汽車、飛機、電話出現之前,各村、各鎮基本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場,無法出現像沃爾瑪這樣的連鎖集團。任何家電和日用品生產、運輸、銷售都不可能實現規模化。人工運貨的距離也許可達二三十千米,更遠則體力難以支撐;即使馬車可使運輸距離增加,但由于沒有現今寬闊的公路網,馬車運輸的有限容量和高額成本還是極大地限制了生產規模與市場范圍的擴張。
因此,張三在張家鎮、李四在李家鎮可各辦一家雜貨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辦得太大,張家鎮和李家鎮甚至還可容納多家雜貨店。正因為每家雜貨店規模都小、需要的創業資本也不多,所以只要有創業意愿和能力,多數人都有機會籌集到所需資金、進入“企業家”階層。而且這種致富機會人人平等,對于任何良序社會都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培育并維持一個足夠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階級”的必要條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于太離譜的重要前提。一旦中產階級占多數,社會穩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產者有恒心,穩定是他們的自然偏好。

在這個意義上,正因為以前開飯館、開理發店的選擇空間比較大,創業機會總體比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沒有現在大。當年的地主也許真的富有,但沒有幾家的收入會是普通百姓的幾千倍乃至幾萬倍。
然而,隨著交通運輸與信息技術的變遷,商業和餐飲業也在經歷公司化、規模化的發展過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規模化零售公司出現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費者能以更低的價格、更方便地買到物品,消費者和創業者達到雙贏。
這也給社會帶來挑戰,規模化公司在全國范圍內統一采購,利用現代物流低成本運往各地,由于它們采購量很大,掌握進貨的定價權,能把進貨價壓到最低,進而可以大打價格戰。相比之下,夫妻雜貨店的規模小,只能被動地接受廠商給的價格。所以,規模化公司有極強競爭優勢,夫妻雜貨店卻很難生存。于是,今天人們做小本生意的機會越來越少,中產階級難以擴大。
餐飲行業也大致如此。肯德基、麥當勞、永和大王等連鎖餐飲公司,因其規模優勢,能把各類食物原料的進貨價壓到最低,夫妻餐飲店卻不能。這勢必造成傳統夫妻店被淘汰出局,逐漸被連鎖餐飲公司取而代之。
在許多小規模創業機會不復存在后,張三、李四們當然可以挖掘其他創業機會,也可選擇成為國美、華聯、沃爾瑪、如家等連鎖公司的職員:只要這些連鎖公司的收入在增長,張三、李四們的工資也能水漲船高,只是他們不再擁有經營性產權,沒有財產性收入,生活方式跟自己做老板也大不一樣。
總之,零售業、餐飲業、酒店業、手工業這些傳統夫妻店行業,已經經歷或正在經歷“去夫妻店化”的洗禮。社會因此失去了眾多中等收入機會,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階層,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出現更為嚴重的分化。
在沒有資本市場的社會里,說“張三很有錢”,意思是“張三過去賺了很多錢,并且積攢下來沒花掉”。不管他是美國的比爾·蓋茨,還是中國的李彥宏、馬化騰,都需要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著收獲創業果實。因此,過去個人財富、家庭財富最多以“萬兩銀子”計算,而不會以“億兩銀子”計算。
可是,股市的到來改變了財富數量級。股市給上市公司股票的定價,本質上是對未來的定價,是對企業未來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定價。于是,微軟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值可以達到2 000億美元。比爾·蓋茨20多歲時就成了億萬美元富翁,李彥宏和馬化騰也都在30多歲成為數十億美元富翁。股市讓他們不需要等幾十年或者幾代人時間,現在就能把未來變現。
假如騰訊沒有在香港上市,馬化騰的個人財富只能通過過去的收入體現,絕不會有今天1 170億元的個人財富。
雖然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企業與個人都有未來收入預期,但以前沒有資本市場,沒辦法對未來收入預期做定價,也沒辦法把未來收入轉變成今天就能算數、就能花的財富。因此,過去即使張三創業成功,有很好的未來收入預期,人們也不一定認為他是百萬富翁、億萬富翁。
由此可見,今天出現那么多億萬富翁,部分是資本市場所致,因資本市場對未來做定價而來,而不是企業家、資本家更貪婪或更剝削的結果。
收入差距、財富差距在惡化,這是現實,也是過去“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大致背景。惡化的起因很多,其中,交通運輸技術、信息技術、互聯網為全球化提供了基礎,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贏者通吃”的地理范圍不斷擴大,有能力的群體成為世界佼佼者,享受前所未有的收入,手握大量財富;而規模化商業模式一方面造就了新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面將許多傳統夫妻店擠出,讓眾多資產階級加入工薪大軍。這些因素使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往兩個極端分化。
但這些因素跟貪婪、剝削沒關系,政府要做的顯然不是禁止技術革新,更不是去阻擋“全球化”。因為抑制革新的動力、降低“全球化”的激勵都會逆轉人類社會的進程。
各國政府要做的是為社會底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給那些在競爭中不幸運或天生人力資本不足的人擁有體面生活的機會。激勵上升通道、保障底層才是上策。除此之外,強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會的人力資本,來應對現代經濟現實。
人力資本的價值高于任何時代,在國家層面如此,在個人層面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