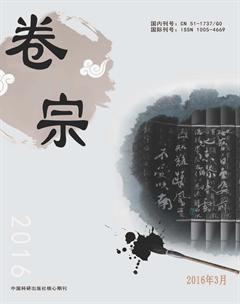淺論明朝的海權思想
項夢顯
摘 要:儒家思想的內涵是豐富而復雜的,推崇大一統是其基本精神之一,也是其一以貫之的思想主張。明朝仍以儒家文化立國,也以實現大一統為目標。明朝海權思想的核心是大一統思想,而能突出代表明朝海權思想的事例就是從永樂三年開始的鄭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由于時代的局限,明朝海權思想也不可避免的帶有局限性。
關鍵詞:明朝;大一統; 海權思想;鄭和下西洋
1 明朝海權思想的內涵
“海權”(sea power)一詞出自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馬漢的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以鄭和下西洋所體現的海權思想無疑比馬漢早得多,但現代世界提及“海權”一詞,必然會提及馬漢,而少有人想到鄭和,確實是個缺憾。鄭和作為傳播明朝海權思想的積極推行者,其歷史功績與作用不應忽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而此時馬漢的“海權論”大行其道,風靡全球,列強紛紛加強海軍建設,極力擴張海權。梁啟超注意到了世界的局勢,在他的《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中說“西紀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歐沿岸諸民族,各以航海業相競。……自是新舊兩陸、東西洋,交通大開,全球比鄰,備哉燦爛。……而我泰東大帝國,與彼并時而興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1]梁啟超之所以極力贊揚鄭和,突出他在航海史上的地位,就是為激發國人海權意識,重振國家海權,抵御外敵。要理解明朝海權思想的內涵,首先必須明晰15世紀中國歷史的環境和背景。公元十五世紀,人類的活動舞臺更多地從大陸移向海洋,在西方掀起了一股航海熱,在中國以鄭和為代表的海權思想也在西方轉型社會和中國歷史交叉口上開始形成,它是中國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段的必然。明初,國家統一,經濟富庶,軍事實力雄厚,這使明朝向海外發展成為可能。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舉措客觀上適應了對外開放的新形勢,這不僅是對海洋的一種探索,也是渴望將強大的國力展示和運用于海外的表現。
儒家思想極力推崇“大一統”,“大一統”是中國歷代皇帝治國理念,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每一個成員孜孜追求的目標。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歷朝歷代都竭力創建或維系大一統國家,鄭和下西洋行動的背后也包含著這層戰略意圖。鄭和下西洋與明皇朝封建的"大一統"思想一致,所有行動本質上都是在實踐明廷的對外戰略。明政府對海外諸國的一系列外交方針,決定了鄭和下西洋的性質、目的以及任務,同樣,正是整個明王朝致力于“大一統”的目標,決定了鄭和下西洋所體現的海權思想內涵。
明成祖對海外諸國,通過大力開展和平外交活動,以德服人,以理感召。永樂七年,成祖朱棣第三次派鄭和下西洋,行前交待:“敕諭四方海外諸番王及頭目人等,……祗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庶幾共享太平之福。”[2]鄭和下西洋自始自終實踐著朱棣“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在航海途中,極力維護和建立朝貢關系,通過強大的軍事實力,肅清海盜,安邦撫民,這種海權思想的奉行,無非是服務于“大一統”這個終極目標。
鄭和作為杰出的航海家,在長達28年的航海生涯中,深知海洋對于國家的重要性。維護海權,有利于實踐大一統理念;海權失去,大一統的實現必然只是空想。所以當新繼位的仁宗高熾下詔:“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出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于內府該庫交收。”[3]鄭和痛心疾首,力諫“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之于海,危險亦來自于海……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伏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4]鄭和已經意識到海洋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認識到海洋與國家富強、國防安全的緊密聯系,頗有現代世界海洋戰略方針的味道。可惜這次力諫并未改變明王朝逐漸閉關自守的趨勢,說明朝廷盡管渴求大一統,但對如何運用海權實現這個目標并未有真正深刻透徹的認識。
2 明初海權思想的表現
在鄭和28年航海活動中,圍繞其海權思想核心所形成的一系列行為主要體現在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
(一)政治上致力于確立并維護朝貢關系
明朝初年,四海統一,國力強盛,這讓永樂帝具備了積極致力于建立以大明王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條件。這正是明朝海權思想在對外關系方面的突出體現。可以說“鄭和遠航展示了明朝鼎盛時期在對外關系上致力于建構一個以明帝國為中心、海外諸國稱臣納貢的朝貢體系的努力與實踐”,[5]也是踐行自古以來,帝王無不以建立強有力的宗藩隸屬關系以顯示國家強盛的理念。追求構建“諸侯朝聘”“四夷朝貢”的禮制體系,雄才大略的明成祖也不例外。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明成祖在即位之初,就放寬了對朝貢者的限制,對禮部大臣作諭示:“太祖高皇帝時,諸藩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者聽。” [6]明成祖在此欲實現帝王居中,萬國來朝的目的表現的十分明顯。太祖派遣鄭和率領浩浩蕩蕩的船隊下西洋,目的之一就是“以懷遠人”,建構起以大明帝國為中心的盛大朝貢體系。作為永樂帝國家理念的實踐者,鄭和重視海洋,開發海洋,維護海洋利益,無論是前來朝貢的國家數量還是朝貢總次數,永樂一朝達到了鼎盛時期。鄭和下西洋期間建立了更多的朝貢關系,體現了明朝海權思想的內核——“大一統”思想,而這里的大一統已超越了傳統的九州范圍。請看朱棣對禮部臣屬的一番話:“帝王居中,撫馭萬國,當如天地之大,無不覆載。遠人來歸者,悉撫綏之,俾各遂所欲。近西洋回回哈只等在暹羅間,朝使至即隨來朝。遠夷知尊中國亦可嘉也。”[7]由此可見,是時海權思想的內涵及行為是相輔相成的,即一方面建立“大一統”的國家,但又絕不靠武力征服他國,另一方面運用強大的威望與更多的國家建立朝貢關系并和平相處,維護和增進自己的海權。
(二)軍事上肅清海盜、平定騷亂
明初南洋海盜猖獗,倭寇侵擾,肅清海盜,平定騷亂,這是鄭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也是明朝海權思想在軍事上的突出體現。“海權”一詞在這里雖與軍事實力相關,但與西方國家奉為圭臬的“海權”首要不是維護自身合法的海洋權益,而是利用軍事實力主動進攻,進行武力征服,從而掠奪資源,建立殖民地,甚至稱霸世界有著本質的區別。
明初南洋域內海盜經常“私自下番,交通外國”,劫掠往來貢使,嚴重影響了明朝對外發展友好關系。鄭和在出使中以肅清海盜、平定騷亂,確保朝貢貿易的順利進行,發展和平外交關系為已任,在下西洋途中為確保航道安全以以下三次戰斗為代表。第一次在永樂五年(1407)鄭和航行至舊港(今印度尼西亞), “遇祖義等,遣人招諭之。祖義等詐降,而潛謀要劫官軍。和等覺之,整兵提備。祖義率眾來劫,和出兵與戰,祖義大敗,殺賊黨五千余人,燒賊船十艘,獲其七艘及偽銅印兩顆,生擒祖義等三人。既至京,并悉斬之”。[8]經此一役,盤踞舊港的海盜首領陳祖義被清除。
第二次發生在永樂七年(1409年),即第三次下西洋途中,鄭和出使諸番國,“至錫蘭山,亞烈苦奈爾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覺而去……及和歸,復經錫蘭山,遂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言,索金銀珠寶,不與,潛發番兵五萬余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使不得相援,和等覺之……乃潛令人由他道至船,俾官軍盡死力拒之,而躬率所領兵兩千余,由間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亞烈苦奈爾并家屬、頭目……。” [9]錫蘭山戰役后,錫蘭山國入貢不絕50余年。
第三次是在永樂十三年(1415年),即第四次下西洋返航時,蘇門答臘島蘇幹剌見鄭和到其國未對自己進行頒賞,勃然大怒,遂起兵襲擊鄭和船隊。《明成祖實錄》記載:“永樂十三年九月壬寅,蘇門達剌國王宰奴里阿必丁遣王子剌查加那等貢方物。太監鄭和獻所俘蘇門達剌賊首蘇幹剌等。初,和奉使至蘇門達剌,賜其王宰奴里阿必丁彩幣等物。蘇幹剌乃前偽王弟,方謀弒宰奴里阿必丁以奪其位,且怒使臣賜不及己,領兵數萬邀殺官兵。和率眾及其國兵與戰,蘇幹剌敗走,追至南渤利國,并其妻子俘以歸”。 [10]鄭和將蘇幹剌等俘獲大大有利于蘇門答剌的和平穩定,蘇門答剌使者不斷入貢中國。
鄭和英勇作戰,參與的這些軍事紛爭純系自衛反擊,給當地人民鏟除匪患,帶來了福祉。鄭和在海外恩威并施,運用海權、維護海權,構建了和諧的對外關系。鄭和以自己的外交、軍事才智,保持了海上航道的暢通,受到各國稱贊,便利了中外友好交往,出現了“自和后,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 [11]的局面。
3 明朝海權思想簡評
明統治者提倡大一統,派鄭和七下西洋是想通過和平的外交行為達到這個目標。訪洋各國途中,鄭和積極傳播華夏文明,結好與國。對中國人來說,華夏文明是一種向心力、回歸力,更是大一統的凝聚力。特別是,明朝海權思想的運用并不局限于中國這個國家范圍,所以它并非具有狹隘的民族意識。但明朝的海權思想自始至終都體現了和平相處的外交理念,而非吞并和傲視小邦的大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這也是和馬漢海權思想的根本區別所在。
明朝的海權思想仍有現實意義,尤其是通過和平實踐背后所體現的大一統思想,仍值得去弘揚。歷史上大一統思想對于維護完整的主權以及多民族的團結與融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現今中國的統一實質是中國自身領土的統一,與明朝大一統所表現的超越于中國領土之外渴望建立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含義也是不同的。但二者為實現目標有一個共通點:都是運用和平手段,求同存異,解決分歧矛盾,形成和平相處的局面。而這一共通點正是實現統一的關鍵。隨著時代背景的不同,“大一統”地理概念和精神內涵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在經濟全球化, “大一統”更多的是在強調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
由于時代的局限,明朝海權思想又不可避免的帶有局限性。鄭和下西洋時進行的朝貢貿易,本身是一種政治行為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行為,因為這種貿易的前提是違反經濟原理的不等價交換。維護海洋權益,有效使用海權統轄海域,僅以維護朝貢關系是無法長久維持的。強大的海軍力量也必然是在自身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不考慮經濟因素的海權終將會喪失。在政治上鄭和時代的軍事實力固然強大,但想通過單一的軍事力量去維護自身的海權優勢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馬漢所說:“這種海上軍事力量貌似強大,而實際上像一種沒有根的浮草一樣,很快會干枯”。[12] 另外,盡管鄭和個人已經看到了海權與發展經濟的關系,但他背后的明朝統治者仍舊死抱“重陸輕海”的觀念,無法從根本上踐行發展海洋貿易的理念,這也造成了其海權思想的根本局限所在。鄭和下西洋后,明政府也無力向海洋進發,更別說經略海洋,至此中國的對外關系發展由盛轉衰,在下坡道上滑行。
4 結語
明代的海權思想至今閃耀著光芒,尤其是以鄭和下西洋代表的“大一統”思想以及自始自終實踐“輯睦鄰國,無相侵越”的理念現在仍值得宣揚。但中國必須首先拋棄明朝重陸輕海的觀念,以合理的步伐進行海軍建設、經略海洋。更重要的是,必須著力提升開發海洋資源的科技水平,在政治、軍事、經濟各個層面協調發展,確保對海權的可持續擁有。
參考文獻
[1]梁啟超.梁啟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545—1550
[2]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史料匯編[M].濟南:齊魯書社,1980:99
[3]《明仁宗實錄》卷1。
[4]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北京[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1):442
[5]李慶新.瀕海之地:南海貿易與中外關系史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10:174
[6]《明太宗實錄》卷12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條。
[7]《明太宗實錄》卷24,“永樂元年十月辛亥”條。
[8]《明成祖實錄》卷52。
[9]《明成祖實錄》卷77。
[10]《明成祖實錄》卷97。
[11]《明史》卷304《宦官一·鄭和傳》。
[12](美)A·T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