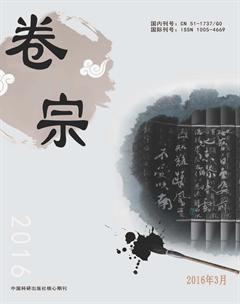海德格爾技術工具論批判思想的評價初探
摘 要:海德格爾批判技術,但其批判角度并非社會學、倫理學、生態(tài)學的視角,而是存在論的角度。基于存在論,海德格爾區(qū)分了存在和存在者,存在不是存在者,進而他區(qū)分了技術的本質和技術,技術的本質不是技術,其中技術的本質相關于存在而技術相關于存在者。現(xiàn)代技術的本質是“座架”,它同樣是“解蔽”,但其方式區(qū)分于自然和技藝,其方式是強求和限定。“座架”將世界和人設置為“持存物”,此“持存物”區(qū)分于主體的對象,這在于人首先被設置為“持存物”。“座架”的“解蔽”方式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座架遮蔽存在自身和真理,而另一方面“座架”遮蔽自身。在此,人并非主體而技術也并非單純的工具,技術是世界的構造。
關鍵詞:技術工具論;海德格爾;技術批判思想;座架
海德格爾批判現(xiàn)代技術是深刻的,但僅從“座架”來看又是極端的,這表現(xiàn)在過分強調技術的負效應而忽視技術的正效應。由于人類具有自身生存的局限性,技術和人相伴而生,技術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技術也是人性光輝的體現(xiàn)。因此,對待技術既要看到它的自然屬性也要看到它的社會屬性。
1 座架的批判
由于“座架”自身的強求性和限定性,從而它對社會的發(fā)展以及人的命運具有決定性,相反,社會和人對“座架”毫無影響,從而“座架”是技術決定論的也是技術悲觀主義的,但由于海德格爾的思想是“林中空地”中光和影的游戲,從而世界、萬物、人和座架都顯示自身,并為處于無家可歸狀態(tài)的人類尋找到家園,那么海德格爾的技術思想并非是技術決定論和技術悲觀主義的。
1.座架與技術決定論
海德格爾的“座架”通常被認為是技術決定論的,那么,什么是技術決定論?《自然辯證法百科全書》中認為,所謂技術決定論“通常指強調技術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認為技術能直接主宰社會命運的一種思想。技術決定論把技術看成是人類無法控制的力量,技術的狀況和作用不會因為其他社會因素的制約而變更;相反,社會制度的性質、社會活動的秩序和人類生活的質量,都單向地、惟一地決定于技術的發(fā)展,受技術的制約”[1]。技術決定論是研究技術與社會的關系所形成的理論,它突出技術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忽視人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并強調技術是社會中的一股獨立的力量,并且這股力量決定著社會的發(fā)展,相反,社會對技術的影響或者沒有或者比較小,從而在性質上即強弱上可分為強技術決定論和弱技術決定論,“(1)強技術決定論認為,技術是最重要的、唯一的左右和決定社會發(fā)展的因素,而嚴重低估以致否認社會對技術發(fā)展的制約和影響,即否認社會對技術的影響。(2)溫和的技術決定論,既承認技術決定社會的發(fā)展,又承認社會的諸方面對技術有一定的制約作用”[2]。除了性質上的劃分,技術決定論在形態(tài)上還可以劃分為,技術自主論、技術媒介論和技術統(tǒng)治論,“(1)技術自主論主要是把技術作為一個社會子系統(tǒng),或者一個社會領域來看待的,并由此賦予這個系統(tǒng)以自主性,具有一種決定其他社會領域的主導作用。(2)在媒介研究領域,人們常常把媒介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放在一起來討論……媒介決定論是技術決定論的一個子集(subset),著眼于媒介對社會的影響。(3)技術統(tǒng)治論一般來講是指在這種政治制度中,決定性的影響屬于行政部門和經濟部門中的技術人員”[3],其中技術統(tǒng)治論中所指的技術既不是器具也不是設備系統(tǒng)而是意識形態(tài)。根據上面對技術決定論的討論,這里將分析“座架”本身是否符合技術決定論的。
從強調技術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來看,一方面,“座架”不屬于社會也不屬于人,也就是說無論是社會還是人都不是“座架”的主人,那么社會和人無法對“座架”進行號令,無論是社會還是人無法對“座架”進行有效的控制;而另一方面,雖然社會和人也不屬于“座架”,這在于“座架”并非埃呂爾的技術環(huán)境,技術構建了技術社會而人在其中生存成為技術系統(tǒng)的一部分或是附庸,但“座架”對于社會和人的建構具有規(guī)定性,并且“座架”將世界和人強求和限定為持存物,從而“座架”是世界和人的形而上學根據。另外,基于“座架”的兩重性,“常人”是無法認識“座架”自身,而沉浸在主體性的美夢中,“座架”顯出一定神秘性。因此,從自主性和獨立性來看,“座架”具有有自主性也具有獨立性,從而“座架”具有技術決定論的特征。
從“林中空地”角度來看,“座架”不是技術的東西,而是技術的本質,從而“座架”是技術成其所是的根據。“座架”是一種解蔽方式,它相關于真理,在“林中空地”呈現(xiàn)自身。由于有了“林中空地”才有光射入“密林”中從而事物得以顯現(xiàn),所以“座架”是相關于作為根據的理性而存在,從而“座架”也是光,同時“座架”的方式是強求和限定,所以“座架”具有雙重性,即“座架”一方面照亮事物使其顯現(xiàn),另一方面由于顯示的方式是單一的,從而在顯現(xiàn)的同時還有遮蔽,并且遮蔽是本源性的。由于“座架”相關于存在和真理,從而“座架”是無法對象化的,盡管“座架”可以表現(xiàn)為信息。這意味著“座架”是不屬于人的,人不表現(xiàn)為主體性,并且“座架”和人都在“林中空地”中顯現(xiàn)自身,在“林中空地”中“座架”和人是其所是且成其所是。可以說“座架”和人歸屬于“林中空地”,這意味著“林中空地”規(guī)定“座架”和人。因此,海德格爾的技術思想并非技術決定或者說無關于技術決定論。
2.座架與技術悲觀主義
對“座架”的另外一個與技術決定論相關的評價是技術悲觀論。盡管技術決定論使得社會和人被技術所規(guī)定,但卻出現(xiàn)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即技術樂觀主義和技術悲觀主義。其中在《自然辯證法百科全書》中認為,所謂技術悲觀主義“指認為技術的發(fā)展直接主宰社會命運,并必然給人類帶來災難的一種觀點,又稱反技術主義。它是技術決定論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它懷疑、否定技術的積極作用,主張技術必須停止乃至向后退”[4]。基于技術決定論在倫理學、社會學以及生態(tài)學等領域的效用,可以將技術悲觀主義劃分為三種類型即道德型、社會型和生態(tài)型。它們分別表現(xiàn)為,道德型“是技術悲觀主義最早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它主要是從道德、倫理角度來否定技術、貶斥文明。中國古代的老莊學派和近代西方以盧梭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學派是其突出代”,社會型是“現(xiàn)代西方人本主義學派和一些技術哲學家、社會學家從社會學、文化學角度對現(xiàn)代技術進步進行哲學反思,在揭示技術與社會的相互關系中所表現(xiàn)出的技術悲觀主義傾向”,生態(tài)型是“以‘羅馬俱樂部為主要代表,包括‘綠黨、綠色和平組織、環(huán)境保護主義組織等,生態(tài)學、全球學角度對加速發(fā)展的技術所產生的日趨惡化的人類環(huán)境提出質疑,通過大量調查數(shù)據向人們發(fā)出了帶有悲觀色彩的忠告,以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和綠黨的‘綠色政治論最具代表性”[5]。根據已有對技術決定論的研究,這里將分析“座架”自身是否符合技術悲觀主義的。
由于“座架”是技術決定論的,從而可以說“座架”主宰著社會和人的發(fā)展,這種主宰表現(xiàn)為科學的控制論,“座架”通過科學控制論主宰世界。從人的主體性出發(fā),人在“座架”下已經失去了主體性,從而淪為“座架”的奴隸,世界在“座架”下被技術化為技術世界,從而世界在“座架”的操控下,那么世界和人處于危險之中而且是最高的危險。但由于人以“常人”表現(xiàn)自身,通常無法經驗到此最高的危險,因此“座架”從技術決定論出發(fā)是技術悲觀主義的。
如果“座架”是技術悲觀主義的,并且“座架”成為人的“命運”,但此“命運”并非宿命論之命運也非厄運,因為此“命運”乃是“危機”,所謂“危機”意味著既有危險也有轉機,正如海德格爾引用荷爾德林的詩句“但哪里有危險,哪里也生救渡”[6]。由于“座架”自身既是顯現(xiàn)的又是遮蔽的,從而想要轉機必須經驗到此危險,這就需要經驗到“座架”,但“座架”的經驗需要經驗到“林中空地”,它是區(qū)別于形而上學的另一個開端,即它是在哲學終結處的思想的開端。因此,海德格爾的技術思想并非是技術悲觀主義的或者說無關與技術悲觀主義。
2 技術與存在的直接觸碰
盡管通常認為作為技術本性的“座架”是具有技術決定論和技術悲觀主義色彩的,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作為工具的技術對人們的好處。技術是人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是人性光輝的體現(xiàn)。
1.技術是人的生活方式
在這個技術物俯拾皆是的時代,技術成為人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技術已經成為人們的生活的主要方式。盡管人類在應用技術時會產生很多方面的負效應,比如人們?yōu)榱双@得更多的資源,從而破壞自然生態(tài);人們?yōu)榱颂岣呱a效率,從而使得工人被捆綁于機器上;為了達到政治的控制,從使而技術成為政治的幫兇;為了打擊敵人,從而才有大規(guī)模殺傷性的武器等等,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忽視技術的正效應。在人的具體生活中,技術可以滿足人們的日常需要。
通常,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吃、穿、住、行,而技術不僅能滿足這些需求而且還可以讓人生活的更好。可見,技術的發(fā)展對于我們的生活有著非常大的影響,技術已經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當然,技術對我們的影響不只是上面這些方面,當然也包括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
2.技術在終極意義上是人性的光輝
人可有固定的本質屬性?人沒有固定的本質屬性,人的本性乃是自由,那么人通過自己來建構自己,人以自身為根據,“人沒有自己的本質。并不存在一個永恒不變的人性,這是人的基本的悖論: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沒有本性。人文學科的目的就在于喚醒人們身上的這個最原始的本性,即回歸‘無的本性。人的無本質包含著兩層意思:第一,它沒有固定的本質——人是一種未完成的存在,一直處在流動變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質的構成是一種向著‘無的、受著‘無的規(guī)定的構成,這里的‘無是‘無它,即它是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7]。人性自由,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可以擁有自由,這是說“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種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8]。
技術是人的生存方式,而且人類通過技術來構造人的本性。人的屬性包括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基于此技術表現(xiàn)為身體技術和社會技術。所謂身體技術是與人的生物性相關的技術,它表現(xiàn)為身體的各種功能,比如眼睛的看、耳朵的聽、四肢的活動等等。基于這些生物性的技術,人們對它們的延伸又發(fā)明了很多其他技術,比如望遠鏡是眼睛的看的延伸,電話是耳朵的聽的延伸,生產用具、代步工具可以認為是四肢活動的延伸等等。所謂社會技術表現(xiàn)為各種社會制度,比如各種規(guī)章制度、各項法律法規(guī)等等。
可見,從語言的生物性和物理性上以及工具性,人和動物并無本質的區(qū)分,那么人是相關于怎樣的語言才使得人與動物區(qū)分?是智慧性的語言即真理性的語言。首先,什么是智慧?博德爾認為,智慧是關于人的規(guī)定的知識。智慧是知識,但不是一般的知識,比如物理學知識或是生活方面的知識。作為知識形態(tài)的智慧相關于人的存在。智慧表明“人是什么”以及“人不是什么”,它指引人區(qū)分存在與虛無、真理與謬誤、是與非等等,進而要求人選擇真理之路放棄意見之路。智慧性的語言相關于真理,從而照亮人的本性。其次,與工具性的語言相比,智慧性的語言有何不同?通常,語言是人的某種能力,從而語言是屬人的,人是語言的主人。在此,語言的工具性表現(xiàn)為語言表達人的思想,人可以使用各種形式的語言來表達思想,從而語言是人隨意使用和丟棄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語言與其他用具沒有任何區(qū)別。
在此,人不僅區(qū)分于動物,而且區(qū)分于自身,在此人的自身區(qū)分才是本質的區(qū)分。總之,智慧語言引導人知道什么是“應該”以及什么是“不該”。人存在于此智慧的語言中,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語言是家園”。
參考文獻
[1]王建社.“技術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互斥還是互補?[J].科技哲學,2006(06):63-68.
[2]許良著.技術哲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111.
[3]王茵.技術決定論研究綜述[J].理論月刊,2004(11):67-68.
[4]趙建軍.追問技術悲觀主義[J].自然辯證法,2000(04):23-26.
[5]趙建軍.技術悲觀主義思潮辨析[J].華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03):64-70.
[6][德]馬丁·海德格爾著.演講與論文集[M].孫周興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上海分店,2011:28.
[7]吳國盛.技術與人文[J].北京社會科學,2010(02):90-97.
作者簡介
銀根,碩士研究生,新疆阿勒泰地委黨校,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