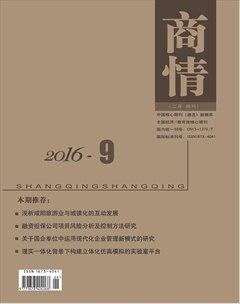淺析經濟全球化對福利政策的影響
周躍敏
【摘要】當今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大趨勢,這使很多資源實現有效合理配置的同時,對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福利政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本文對國外的一些文獻編譯整理后,總結了一些相關的理論,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全球化對福利的影響提供了支持。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福利政策,現代化,影響
1.國際主流觀點分析
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許多福利國家的各種福利建構,源自于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意識形態,在若干層面上都面臨相同的壓力,包括科技變遷減少了工作機會,特別是對低技術勞動者而言,制造業的衰退與服務業的擴張是整體趨勢,因而也對福利國家帶來一些問題。首先,制造業就業的下滑往往導致更高的失業率,或者周旋于低薪且不穩定的服務業中的所謂“低技術作業”;而人口結構的改變,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的趨勢隱憂,年輕工作者的數量減少,分享退休金資源的高齡老年人日益增多,增加了潛在成本;加上新的家庭型態,伴隨著女性對性別平等與薪資工作的平權要求,促進了人們在工作和家務照顧責任上更多性別平衡的改變,從而擴大了人民對國家福利供給的需求。但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政府對于運用進出口、金融、資本與匯率面的控制進行對總體經濟調節的能力卻被削弱,并更深化福利政策必須被用于提升經濟競爭力的壓力。
簡而言之,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所建構的以生產與經濟競爭為導向的生產福利體制,秉持的是一種社會福利建制與經濟發展的零合對立觀。這樣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發展意識形態從工業發達國家開始,以其優勢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科技力量,也引領著許多發展中國家奉為典范,而東亞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起飛過程,更是二戰后經常被舉例的發展典型。但這樣的觀點所反映出來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與現代化都依賴于先采取工業先進國家個人主義的價值體系,為了成就現代化轉型,發展中國家有些不得不先西化,而其中就會有問題,新自由主義論者認為:市場力量的完善與科技的持續發展終能解決一切,政府所應該做的就是不要干預,如此,所有的國家都可以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獲利進步,最終擠身于發達國家之列。但是以戰后半個世紀的發展經驗來看,全球化發展固然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帶來了若干程度上的經濟成長,卻也帶來許多的社會問題,有待社會政策加以適當的處理。而這其中源自全球化所對勞動者與社會福利所造成的沖擊,可以分成以下三類:一,全球化使社會伙伴關系瓦解:全球化發展下,資本快速地流動所造成的國際競爭壓力下,勞資雙方的伙伴關系逐漸瓦解,而必須重新建立新的經濟與社會伙伴關系。新的社會契約強調的便是提升生產力與競爭力,并以競爭式組合取代傳統組合。二、對就業的沖擊:科技與產業技術的發達,意味著大量機器取代人力工作,低技術含量的工作最后將被機器取代,全球化促使技術快速革新與競爭力提升,也使得失業問題日益嚴重,充分就業目標難以達成。三,全球化所帶來工作條件與環境惡化:全球化下的勞動市場普遍存在短期,臨時,部分工時,低薪的不穩定工作環境,低技術性或傳統產業勞動者被迫經常彈性更換工作,實質薪資收入也逐漸減低。
泰勒-顧柏認為在全球化外部因素的影響下,與塑造政府福利論述主流思想型態的新發展,彼此相互影響,因而產生了一些重要的福利國家論述轉移。首先,單從形式層次來看,主張以國家干預達成促進經濟成長與充分就業的約翰·凱恩斯主義已經失效,經濟全球化已經改變了福利政策制定背后的基本假設,之前認定政府在自己國內的政策享有完全自主權的預設,已遭到徹底推翻,甚至使得多數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黨轉向接受競爭力的必要性,必須超越傳統上對“再分配的關懷”的說法,十足自由主義的思潮成為政策制定大體方向的基礎。這意味著一種結合機會的平等、對工作倫理的強調、僅對那些無工作能力者給予適當的福利、并設法透過社會支出增進其生產力。
顯著的例子是鮑德溫透過中產階級角色與勞動階級利益之觀點,分析福利國家的成長,在全球化競爭中取得優勢的資本與中產階級,在福利供給取得方面同樣有優勢,并開始撤回對以政府為主的福利供給的支持,這樣的狀況又以一些典型政府福利供給較少、不平等程度又較高之國家中發生為多。換言之,典型新自由主義的福利政策觀點認為,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國家的稅收越來越少,已沒有能力維持國家原有的福利政策,國家的公共支出必須進行削減,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取代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體現出了國家主權在社會資源再分配領域所受到的限制。以上的三種轉變,在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公積金制福利中,都可以看到全球化對社會政策影響的特點,所得的逆分配、階級的差異、顯性勞動者的獨厚,和顯著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政策觀,賦予社會福利政策積極生產價值與競爭力強調的意義。而這樣的全球化發展趨勢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是否就如同文獻探討中新自由主義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福利意識型態的終結?從很多表現結果來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2.全球化的影響以及問題分析
首先,全球化是否真的導致福利國家的資本出走?這樣的觀點假設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各國無法再對資本流動進行嚴格的管制,資本基本上來說已經可以在世界各國之間進行自由流動。在這種條件底下,各國為了吸引外來投資,增強經濟競爭力,將會在各方面迎合資金的需求,國家之間為了爭取資本投入將進行激烈的競爭。其次,資本的自由流動使得企業可以在世界各地進行生產,企業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就會離開稅收高、工資水準高、福利負擔高的國家,轉向低稅收、低工資、低福利的發展中國家或轉型國家。因此,對企業獲利征收高稅率及社會支出的國家,將會面臨資本外撤到秉持友善投資態度國家的困境,從而會降低國內的就業與投資水準[1]。在這種狀況下,福利國家就會面臨許多困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稅收減少、失業人數增加。資本和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強化了跨國公司等利用轉移生產成本或者其他逃避稅收方式的效果,因而全球化再這個意義上就削弱了國家提供福利保障和社會服務的能力。因為福利國家的稅收是保證各種福利政策能夠實施的支柱。財政稅收的下降將會導致福利的資金來源縮水。政府削減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的支出就成為一個理所當然、也是必須的選擇。在資本的流動可以輕易跨越國家邊界的情況下,國家的高比例再分配性稅收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各國政府的決策者不但需要考量自身國內的各種狀況,也必須考慮其他國家對待投資的各種政策措施。由于各國政策相互之間難以協調,從而使得各國決策者處于囚徒困境之中。
為了獲得資本投資的青睞,各國政府會競相降低稅收、調降工資并削減勞動保障水準等。這樣的競爭將會導致稅收、工資與勞動保障降低到一個最低的標準。因此,全球化的市場競爭與資金流動強化了資本的結構性權力,資本家在與政府或勞工談判中擁有了強大后盾和選擇空間,福利國家在這個發展邏輯之下將會逐漸轉變為競爭型國家。但以上基本上是新自由主義關于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觀點,相當程度上只能說是理論上的推理,實際上與福利國家的真實狀況有多大程度上的相符合還是一個問題。從理論上來看,新自由主義的這種觀點是把吸引投資的因素僅僅局限在稅收和工資水準上,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響,特別是把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和公共服務視為負擔。如此則存在著幾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第一,影響國家的經濟競爭力的因素僅僅取決于工資和稅收水準嗎?第二,與第一個問題相連的根本問題是,社會福利發展必然與國家的經濟競爭力相沖突嗎?第三,福利國家面對全球化的政策選擇是否一致?除了英國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福利模式之外,還有哪些其他福利模式可供選擇?假設新自由主義對福利國家的觀點是可靠的,那么就一定會出現有國家為了獲得投資而降低稅率,或者反過來說,將會有實行普遍福利的國家出現經濟競爭力大幅衰退的問題出現。然而,這樣的證據在當代21世紀的福利國家當中卻是不如預期的,其實從總體上來看,歐洲的高福利國家并沒有出現大量資本外逃的情況,相反,國際上很大一部分投資是在這些國家之間進行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新自由主義關于福利國家走向瓦解,以及國家必須削減福利以適應全球化的這個命題,其實是充滿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
即使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非國家行為體(例如跨國企業)的重要性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實際上,國家在領土之內卻對于這些非國家行為體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即使是一個最貧窮的國家,政府對于經濟和政治的控制仍能帶給跨國公司最嚴重的損失,政府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并非無關緊要,相反地,跨國公司反倒經常要求助于國家來鞏固自身的市場實力和地位。
3.結論
目前更加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歐洲福利國家在面對全球化的相似壓力時,有出現所謂的全面趨同“福利向下競爭”,不同類型的福利國家體制仍然保有其明顯的特性。顯然,有關政府福利角色的論述與福利體制的典型轉移,正朝向一個新的方向調整。大體上來說,當傳統國家面對到向全球化發展趨勢這樣的全面挑戰時,過去那種以福特式工廠為基本模型的政治經濟環境中,透過支持男性養家模式的增強男性勞工階級利益,強調國家、社會與福利之間的團結角色,過去所秉持的干預式經濟發展策略,隨著全球化的開放競爭與資金快速流動跨越疆界,已經逐漸無法收效,取而代之的是朝向因應全球化市場競爭為主的福利體系演變,包括推動積極的就業促進方案,工作福利路線,以及更加強調其經濟效益的福利支出。以需求出發所維持的傳統特定對象殘補式福利,自然無法再滿足公眾的普及福利需求,在經濟發展之中透過福利促進生產的積極性,并需兼顧社會公義平等的基礎與價值,保障公民身份的社會契約權利才是開源之策。
參考文獻:
[1]Mishra Ramesh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General Information. 2016, 35(2002):213–239.
[2]Vic George , Paul Wilding.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Welfare. The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2015(30):17.
[3]Peter Taylor-Gooby . Choice and public policy : the limits to welfare markets, Macmillan , St. Martin's Press. 1998.
[4]Baldwin P.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olidarity: Class Bases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1875-19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5]任丙強. 全球化、國家主權與公共政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