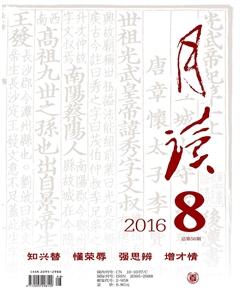并蓄兼容的益處
歐陽瑩之
人民是國家的基本。我們所研究的時期之始,中國或意大利的人口不多,但種類繁雜、風俗紛亂。經過長久的沖突交會,他們終于在秦漢皇朝或羅馬帝國的統一政權下,融合為一個主體民族:后稱漢人的華夏族,或以羅馬為名的意大利人。民族形成的過程艱難,體現了華夏族和羅馬人較為開通的性格。
一位現代史家說:“古意大利的居民,原有百端異樣的種族成分、社會經濟、政治組織、宗教言語、物質文化。這是我們極難明白的。”古中國的情勢更難明白,因為它更龐大復雜。從遠處看,今天的中國人顯得單純,92%是漢族,其余的分為55個少數民族。近看即使漢族之間也大有差別。“漢人”在漢朝之后才成為民族之稱。在有名稱之前的悠久歷程中,漢人融合了遠比意大利原居民龐雜的無數民族。
軍事征伐、政治組合、移民共處、血緣混融、文化熏染,種種影響把繁雜的民眾陶鑄成一個整體民族。這漫長的過程殊不容易。華夏和羅馬人作為中國或意大利的主體民族,時常驕橫偏執、自私好斗。然而以美國的種族歧視為尺度,他們的偏見遠離1860年代內戰之前的程度,近于1960年代民權運動之后的情形。他們有能力適應、改造或吸收同化其他種族,從而擴大自己的實力。要認識華夏族和羅馬人的相對容忍量,最好把他們與別的民族對照。與他們同時的希臘人便是個好例子。
當羅馬人開始聚居建城時,約700個希臘城邦已經散布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哲人柏拉圖喻之為池塘邊聒叫的青蛙。它們大多數很弱小,平均居民不過數千;龐然巨物如雅典和科林斯是個別例外。希臘城邦的公民享受重大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權益。誰有資格作公民?當時的哲人亞里士多德解釋:“一般實際規律,公民的雙親都必須是公民,單單父親或母親是公民不能合格。有時這規格更推溯到二、三或更多代祖先。”一旦發現外婚,子孫幾代都有被開除公民籍的危險。現代學者形容民主的雅典如何嚴格執行公民內婚的規律:“令人有一種圍城的感覺,猶如公民們堅守城壘,不斷地抵御外面壓力。”
意大利和中國的習俗與希臘相反。在那兩地,與外族通婚的損失不太大。羅馬逐漸授公民籍及其權益予征服過來的意大利人。周人有同姓不婚的禁忌,阻礙諸侯貴族相互通婚,因為他們大多數是周王的親屬,同姓姬。外婚常逼使他們求偶于庶人土著,甚至蠻夷異族。皇朝中國沒有公民制度,然而從秦朝開始,一貫把絕大部分居民,不論來源,都納入編戶齊民,給予同等義務和權益,也不禁對外通婚。
誰有資格進入政府擔任官職?這是政治社會的重要性質之一。在排外的希臘人間,亞歷山大大帝獨樹一幟。據希羅傳記家普魯塔克說:“亞里士多德教亞歷山大做希臘人的領袖、野蠻人的主子,愛護前者如朋友親屬,對待后者如野獸草木……亞歷山大不聽,他對所有人都一樣。”可是亞歷山大才咽氣,他的繼承者們就恢復傳統,把他任用的波斯人等土著,席卷踢出政府。在龐大的希臘化世界里,希臘和馬其頓人構成一個優等民族。極少土著能進入他們的封閉圈子,想成功的必須耐心等待,并通過困難的洗禮把自己變成文化上的希臘人。希臘人慣于在運動場脫光衣服,但在許多東方社會,當眾裸體卻是最大的羞恥。類似的苛刻條件使承繼亞歷山大的希臘化王國不能得益于土著人才。羅馬和中國就開通得多。自前1世紀開始,意大利和各省土著相續涌入元老院。后來,不少羅馬皇帝來自非洲、亞洲。秦始皇廢封建后,用人憑能力品德,不論種族親疏,成為一個中國理想。丞相大臣來自全國各地。漢武帝遺詔,為8歲的少主指定4個輔政,其中一個是匈奴人金日磾。
強烈的排外性使希臘城邦難于擴張、合并或統一。多數始終微小,而且經常與鄰近城邦爭執抵觸。饒它帶領抵抗波斯的大功,雅典的帝國維持了不過50年。與雅典和希臘化王國相比,秦漢皇朝和羅馬帝國就成功長壽得多。華夏族和羅馬人有歧視,但主要基于行為道德、文化政治,不基于種族出身,從他們的事例,可見并蓄兼容有助帝國擴張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