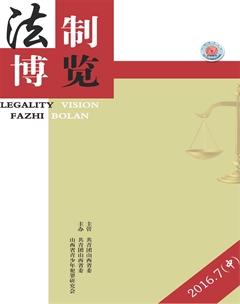論轉化型搶劫罪的認定
摘要:轉化型搶劫罪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屬于多發的且形式多樣的犯罪。由于刑法對普通搶劫罪與轉化型搶劫罪均以條文明確地規定下來,導致學者對本罪的構成要件的認識存在不同觀點,加上司法工作人員在適用本罪中有偏差和錯誤,因而需要對本罪進行準確地認定。本文分析本罪的前提條件與幾個關鍵要素,以期對實踐活動提供有益的思考。
關鍵詞:轉化型搶劫罪;數額限制;當場;認定
中圖分類號:D924.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6)20-0209-02
作者簡介:陳文,男,漢族,福建福州人,吉林財經大學,法律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刑法、理論法學。
我國刑法通說把刑法第269條的規定稱為轉化型搶劫罪,其與刑法第263條規定的普通搶劫罪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刑事司法實踐中,搶劫類型犯罪多發,形式多樣,加上實務中有的司法工作人員未能正確地把握刑法第269條所規定的構成要件中的要素,導致實務中轉化型搶劫罪認定出現偏差和錯誤。因此,有必要對刑法第269條所規定的條文進行要素分析,本文基于刑法條文的表述,結合普通搶劫罪與轉化型搶劫罪的聯系、區別,對相關要素進行司法認定,以期為司法實踐提供有益思考。
一、對犯盜竊、詐騙、搶奪罪要素的分析與認定
刑法理論認為規定轉化型犯罪是基于普通犯罪與特定犯罪之間的相似性而作出的法律擬制,換言之,刑法第263條規定的普通搶劫罪與刑法第269條規定的轉化型搶劫罪是表面上有不同之處,二者的本質是相似的,立法者因此在經濟、便利、避免無必要的重復的原則下規定了轉化型搶劫罪。在轉化型搶劫罪條文的前提條件進行分析時,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準確認定。第一,刑法條文的表述是構成三種犯罪,而不是僅僅是所謂的違法行為的情況,應當注意這個明顯的區別。眾所周知,刑法中所規定的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除了極個別對數額沒有限制外,一般要求達到刑法中數額較大的規定,因此如果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無需由刑法對其進行否定評價,只需根據行為人的具體的違法情形給予其他法律足以懲罰,這時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由于行為人不具備構成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條件,不應該適用該罪對行為人科處刑罰,只在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情況下給予相應的行政處罰即可。當然,行為人在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時構成其他犯罪的,應當依據相關罪名追究其刑事責任。第二,如上所述,刑法中對構成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一般有數額上的要求,那么作為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條件,能否也要求達到數額上的限制?可以這么說行為人實施的三種行為而構成犯罪的情況下,當然適用轉化型搶劫罪對行為人科處刑罰。但是假如行為人在實施本罪三種前提犯罪時,實際上無法取得數額較大的財物而行為人主觀上認為能取得的情況下,可以成立刑法第269條所規定的犯罪。這與上述的內容是不存在矛盾的。因為該罪的刑法條文所表述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并不要求作為前提條件的三種罪,必須達到既遂狀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行為人如果實施了前提條件的三種罪而并未發生刑法的法益侵害的結果,采取構成本罪所要求的一定時間和空間內的為刑法所禁止的行為的,依然符合刑法的規定;如果將前提限定為前三種罪名必須是既遂,那么由可能行為人不符合構成要件或進構成罪輕的犯罪,這難以為人所理解和接受。
第三,我國刑法規定了普通的盜竊罪、詐騙罪和搶奪罪,還針對侵犯法益所指向的對象的不同規定了一些特別的盜竊罪、詐騙罪和搶奪罪。例如搶奪國有機關印章罪,行為人實施了該罪所禁止的行為,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應當指出的是,由于該罪所禁止的行為所指向的對象僅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意義,在未符合其他條件而形成重大價值的情況下,其只是價值極小的東西,與一本普通的書籍的價值相似,均不可認定為構成搶奪罪,進而適用轉化型搶劫罪。這種處理方法實際上貫徹了罪刑法定原則中只有侵犯刑法值得保護的法益才能科處刑罰的要求,同時也可避免至多僅需治安處罰即可處理的情形認定為犯罪的濫用刑法的情況出現,損害國民的可預測性。最后,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釋中將嚴重的侵害法益結果的發生作為滿足一定條件的未成年人對轉化型搶劫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的情況,但是應當采取謹慎的觀點,因為這種規定實質上將普通搶劫罪與轉化型搶劫罪認定為兩種完全不同的犯罪,這與刑法通說中認為基于行為的相似性而規定轉化型搶劫罪是相沖突、相違背的。因此,筆者認為,應當明確地指出滿足一定條件的未成年人既然觸犯普通搶劫罪在刑法中明確要求要受到刑事責任的追究,那么犯轉化型搶劫罪當然也必須對其科處刑罰。
二、對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要素的分析與認定
首先,當場這個要素的理解、解釋是司法實務中準確認定轉化型搶劫罪的關鍵,既要防止片面狹窄地、不當地縮小認定范圍,又要反對任意地解釋致使適用轉化型搶劫罪范圍的擴大。有的學者和司法工作人員片面地將其限定在行為的發生地,這樣容易人為地漏掉一些值得處罰的情形。有的學者和司法工作人員采取擴大解釋的方法,將本罪的條文表述分割為前后兩個獨立的行為,認為只有后一行為才是成立本罪的場所。這樣導致在當下的行為發生地可能沒有人能夠及時采取救濟措施,在經過幾天甚至更長的時間后才被發現,這時行為人再實施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的行為才可以構成轉化型搶劫罪。毫無疑問,這種解釋存在令人無法接受的邏輯,將會使得司法實務中將數個行為隨意結合,濫用該罪。因此,綜合以上兩種情況,實務中應當反對片面限制當場的范圍,也要堅決制止任意擴大范圍。筆者認為,對“當場”這個要素的解釋應包括以下幾種情形。最常見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本罪中實現行為人的行為發生地;或者是行為人實施了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正要離開時被人發現,可以認定為現場;或者說實踐中較常發生的行為人實施了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后,立刻在現場被人發現而逃跑,此時被人追趕的過程,可以認定為當場;或者說行為人完成了盜竊、詐騙、搶奪行為,離開行為實行地很短的時間內即被發現,此時可以認定為當場,當然,與這種情形相類似的,即在離開行為實行地后又主動折回來的情形或在離行為實行地有很長距離才被發現的,就不宜認定為當場。依本文所述,可以認為這幾種情形,均是在空間與時間上存在密切聯系的情形,才可以認定為轉化型搶劫罪的當場。
其次,行為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究竟要達到什么樣的程度才是可以適用轉化型搶劫罪的情形也應該進行認真分析和認定。應當指出的是,認定這個要素時應采取與認定“當場”要素相同的解釋方向和思維,既不能不當地限制縮小程度,又不宜肆意地擴大暴力程度。參考普通搶劫罪等相關犯罪的多年司法實務的認定標準和刑法理論的通說觀點,適用本罪的程度標準應該是使他人主觀上害怕或者擔憂其他與其利益相關人受到傷害等而不得不放棄反抗,才可適用轉化型搶劫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當然這種判斷也應當符合社會一般人的觀念。此外,行為人適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人應當是特定范圍內的人,不能將任何人均認定為其所指向的對象。本文認為,這個特定的范圍不僅有犯罪行為的受害人和執行職務行為的公安人員,也應包含自發地在發現行為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后參與追趕等行動的人。實務中只要使這些人不得不放棄反抗的情況出現即可適用本文中所論述的罪名。
綜上所述,在司法實踐中對轉化型搶劫罪的認定,應當準確把握刑法第269條的規定的幾個關鍵要素。對本罪的前提條件的分析時,不能將只需行政處罰的違法行為認定為刑法中的犯罪行為,也要把握即使沒有達到既遂,也可以認定構成本罪。同時,正確解釋當場與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這兩個要素,作出符合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對認定轉化型搶劫罪和對行為人準確追究刑事責任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鄭澤善.轉化型搶劫罪新探[J].當代法學,2013(1).
[2]張明楷.行盜竊罪的新課題[J].政治與法律,2011(8).
[3]李希慧,徐光華.論轉化型搶劫罪的主體[J].法學雜志,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