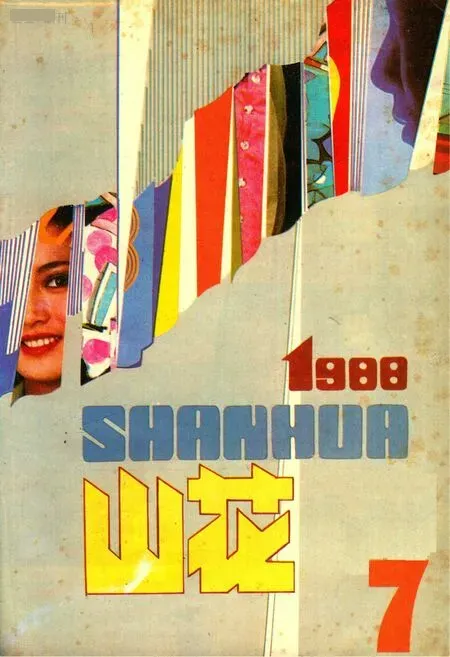睜開自己的眼睛
王林
Ⅰ.瞬間的真實性
盡管印象派的大師們想以自然光、條件色和戶外作畫的方式來顯現對象“瞬間的真實性”,但對繪畫而言,這是不可能的。繪畫所凝固的瞬間,是為理解所組織的場景,而理解所依賴的知識塑構和藝術規范決定了繪畫的所謂真實。所以對繪畫而言,真實是一個文化概念,不同時代有不同文化的真實性。攝影顯然和繪畫不同,當快門以百分之一秒或千分之一秒抓住對象時,其影像正是瞬間的真實。但應該指出,它只能是局部的。局部的瞬間的影像能否代表對象的真實姑且勿論。問題在于對局部和瞬間的擇定乃是人為的結果,這樣影響的危險即是用真實世界的類像去取代人與真實世界的直接聯系。
陳啟基先生深諳攝影的本質,他從不用虛假的記實性迷惑人,即使是對象具體的人像攝影,或者是運用道具使之具有舞臺性,矯飾感,或者是附著物品使之呈現異樣感、荒誕性,或者通過繪畫處理和拼貼添加以造成殘缺、破碎、割裂和分解,其目的無非是要把觀者的感受引離對象的真實,導向內心的體驗。
陳啟基手中的鏡頭是不平靜的。經常運用閃忽、裂變的影響來提示精神的壓抑和緊張,具有突出的表現主義傾向,其作品有一種特殊的影響效果。一方面是強烈的黑白關系,借中國水墨“計白為黑”、“無之以為用”的手法,但更沖突、更放縱、更大膽,也更刺激。另一方面則是強調感動勢,不管是表現音樂和呼吸的抽象形式,還是表現書法和肌體的合成作品,都是以線條的急速運動來捕捉不是凝固的瞬間,而是運動的瞬間。
在瞬間與運動發生關系時,也就是影像和心理相通的時候。人的內心世界,無論是意識還是潛意識,無論是幻想還是夢境,用柏格森的話說,乃是綿延不斷的“生命在于運動”的另一種解釋,即是生命在于精神、心理、情感。以及內心沖動的不斷發生,永不平息。影像的瞬間,如果有意義,不過是精神真實的象征。所以對攝影而言,對作為藝術家的攝影家陳啟基先生而言,重要的不是拍攝了什么,而是呈現了什么和引發了什么。
Ⅱ. 發生的和背后的
陳啟基無論拍照片,還是畫畫,其創作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很原生態。他總是從個人觀察出發,去呈現那些深有體味的東西,從來不管什么技術規范或學院要求,也不管自己的作品能否成為畫廊所需的樣式。他和他的作品處在不斷發生的狀態之中,這樣的創作過程讓他很快樂,很投入。
近些年來,他在周圍朋友中進行家庭調查,收集照片,整理線索,生活在歷史追尋里。貴陽這座城市,地處高原,遠離中心,避禍、避世的移民歷代有之,至今尚存不少淵源甚深的家庭,像陳啟基長期關注的呂氏家族便是一例。但陳啟基并非社會學家,也無意于調研成果,那些已經破碎、正在消逝的歷史記憶,帶給他深入個人內心、也深入社會現實的感慨與感動。于是他開始以《中國家庭》為題進行繪畫創作。
第一個階段是用丙烯手繪方式畫出版畫印制的效果,不獨因貴州有當代版畫創作傳統,而且因借用過去常見的獎狀式樣來表現中國家庭給人以復制印象,其標準化與模范化不啻是強權時代的隱喻。當家庭成為社會整齊劃一的單元時,個人更是早已不見蹤影。我相信陳啟基在這樣的創作中是深知痛苦的,因為他難以把那些個別家庭、具體經歷的真實感受表現出來,于是他不惜破壞剛剛定格的圖式,讓鮮活的歷史記憶自由進入創作之中。不僅圖框被任意打破,背景紋樣也因其雜糅而變得隨心所欲。特別是人物畫法,取線條勾勒,淡彩涂抹,類似水彩速寫的生動性,有一種未完成效果,仿佛是畫家難以抓牢那些歷史影像,它們正在淡化、正在消逝,正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文化境遇中變得殘缺、破碎,永遠不再完整。這種使記憶真正成為記憶的繪畫方式有一種力量,就是讓藝術在場,指向造成問題的現實境遇與文化背景,而不僅僅是回憶歷史和歷史回憶。集權時代對中國家庭的傷害、對人的傷害是不能忘記的,其根本原因是這種傷害并未真正得到反省,甚至仍在繼續。藝術家并非公訴人,他只能在藝術不斷發生的過程中、在自己的創作方法中去觸及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所以對陳啟基而言,繪畫生活將與問題意識并存而同步。
Ⅲ. 讓歷史回到個體
歷史一旦過去,就只能存在于遺物、記錄、敘述與闡釋之中。而現有體制規定的敘事模式,一切相違的東西皆被視為機密而不得解,由此官修史成為被遮蔽的歷史。
去蔽歷史的要求必然求助于個體敘事。盡管個體敘事零碎、片面,不無記憶模糊性,也不能排除敘述者的意圖性,但這種敘事的真實性有人負責,并可進行參照和比對。其細節性與具體性難以被空殼化和概念化,因此與真實最為接近。眾多個體敘事有一種力量,就是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不同方向并以不同敘事方式指向歷史的本來面目。在中國學界,以歷史闡釋的主觀性來否定歷史真實的必要性,是一幫御用文人的機會主義策略。面對正在興起、無處不在的個人回憶錄和口述史,他們將無能為力。
此所謂“禮失求諸野”。
陳啟基一直生存在野地之中。他在貴州五十年人生經歷,既是中國社會經歷變遷的投影,又是當代藝術發生過程的案例。陳啟基的寫作方式,就像他的為人,天然而質樸,坦率而真誠,從不虛妄,從無夸飾。我們在他的文字中經常可以發現斷裂,那是記憶的斷裂處,無須修補也無法修補。甚至他不想去尋求某種敘事的統一性,其實過度的修辭方法反而會損害直言不諱的真實。于是我們在他的回憶中,讀到了那些已經被遺忘或正在被遺忘的故事:1984年清污運動波及貴州,有關部門竟以洗印人體模特照片為由抄家抓人關押審訊;1987年貴陽《現代藝術展》以裝置等觀念藝術為主,居然美協主席董克俊請來了市長剪彩;1989年前后一群貴陽藝術家以“人·生命與信仰”為題,策劃實施行為藝術活動長達三年之久,等等。其敘述之生動、描繪之細致,讓人身臨其境。往事并不如煙,也不會因主流敘事的強大而煙消云散。往事的追尋不僅是消遣,而是為了捕捉記憶,揭示真實。
這是誠實的陳啟基所作的一件誠實的工作,做得很認真很地道。謹以此文向陳啟基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