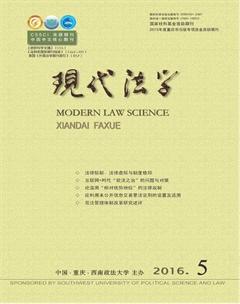廣義行為能力在我國民法典中的定位
摘要:在大陸法系傳統民法上,廣義行為能力是民法學者在法律行為能力和侵權責任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抽象出來的一個學理概念,其在本質上是人的意志能力。廣義行為能力理論之目的,旨在說明法律行為能力制度和侵權責任能力制度具有同根性,而不是要取代這些既有的概念類型。然而,蘇俄民法對傳統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進行了實質改造,使之成為了其民法典中的一個統轄民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的法定概念,并對我國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學說產生了深遠影響。不過,這種做法忽視了法律行為能力與侵權責任能力之間存在的本質區別,抹煞了侵權責任能力制度獨立存在的價值及其必要性,并且在實踐中也出現了諸多難以克服的問題。在我國的民法典編纂和民法總則立法過程中,不應繼續沿襲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來實現法律行為能力制度和侵權責任能力制度的體系化構造。
關鍵詞:廣義行為能力;法律行為能力;侵權責任能力;民法典
中圖分類號:DF 525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5.05
一、問題的提出在大陸法系傳統民法中,法律行為能力制度是民法總則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我國,關于民事行為能力的內涵及其與侵權責任能力的關系 “民事行為能力”之概念乃我國《民法通則》所獨創,其目的是為了在理論上和立法上將民法上的概念與其他部門法上的概念區別開來。但是這一術語并不能直接、明確地區分大陸法系傳統民法上的廣義行為能力和法律行為能力,并且在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的影響下,更是加劇了相關概念在理解上的混亂,參見正文后述。,學界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論。如有的學者認為:“民事行為能力包括公民以自己的行為取得和行使民事權利的能力,承擔和履行民事義務的能力,以及對自己違反民事義務的違法行為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1]也就是說,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民事行為能力應采廣義的概念,其不僅包括了狹義的民事行為能力,還包括了侵權責任能力(下文簡稱為“責任能力”) 參見:郭明瑞,房紹坤,唐廣良.民商法原理(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34.。
更多的學者則認為,民事行為能力應采狹義的概念。因為“非法行為,如侵權行為,唯發生行為人的責任問題,而不發生行為是否生效的問題,不要求有民事行為能力。至于合法行為中的事實行為,亦僅有構成問題,而無效力問題,也不要求有民事行為能力。”[2]盡管主流觀點認為民事行為能力應采狹義概念,從而與責任能力相區別,但是仍然主張以民事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 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9.。那么,這種主張是否合理?在未來的民法典中繼續堅持以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是否妥當?而更具根本性的問題是:在民法典編纂,尤其是民法總則制定的重要關口 關于民法典編纂的相關最新消息是,中國人大網2015年12月28日公布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關于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主席團交付審議的代表提出的議案審議結果的報告》。報告明確指出:“孫憲忠等代表提出的第70號議案,提出民法總則基本的制度框架及立法指導思想。對于議案提出的建議,法律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將在民法典編纂工作中認真研究。制定民法總則已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2016年立法工作計劃。”,我們該如何妥當地認識與評價大陸法系傳統民法上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以及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對此,我國學者尚未有專門的理論分析。在本文,筆者將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步探討,以期深化并推進相關的理論研究,從而為我國民法典的體系化和科學化貢獻綿薄之力。
二、廣義行為能力理論之源流如前所述,我國民法學者圍繞民事行為能力的內涵及其與責任能力的關系產生了極大爭論。究其根源,主要是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學說受到了蘇俄民法上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及制度的深刻影響。而蘇俄民法上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又是對大陸法系傳統民法中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的實質改造。因此,要在民法典編纂和民法總則的制定過程中對民事行為能力制度和責任能力制度作出較為妥當的定位,有必要考察廣義行為能力理論的內涵及流變。
現代法學鄭曉劍:廣義行為能力在我國民法典中的定位在具體展開之前,須說明的是,我國民法學者圍繞“(民事)行為能力”所存在的“廣狹之爭”,在德語法學界并不存在。因為,廣義行為能力的德文單詞為“Handlungsfhigkeit”,而狹義民事行為能力(即法律行為能力)的德文單詞為“Geschftsfhigkeit”。二者在概念、內涵及構成上均有著較為明確的區分,因此在使用時不致發生混亂和歧義。但是,自清末變法修律以來,民法學者就在日本民法學說的影響下 例如,作為《日本民法典》的起草人之一的富丼政章,在其著作《民法原論》一書中認為:“行為能力者,得為發生法律上效果之行為之能力也。有法律行為能力及不法行為能力之二種。”(參見:富丼政章.民法原論(第一卷)[M].陳海瀛,陳海超,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92-93.),使用“行為能力”的稱謂來統稱德語中的上述兩種能力,但是在具體闡述時往往將其進一步區分為“廣義的行為能力”和“狹義的行為能力” 例如,清末民初的民法學者邵義在其所著的《民律釋義》一書中即明確指出:“惟行為能力又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分為法律行為能力、不法行為能力與特別行為能力之三種。狹義之行為能力僅指法律行為能力而言。本節所規定,系采第二主義。”(參見:邵義.民律釋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6.)。自此,在漢語法學界,“行為能力”便具有了廣、狹二義。
從現存的德國法律文獻來看,薩維尼(Savigny)最先在《當代羅馬法體系》第三卷中使用了廣義行為能力(Handlungsfhigkeit)的概念,并將其界定為完全自由的理性運用的能力,其是自由行為的必備條件[3]。而薩維尼使用這一概念亦淵源有自,而非憑空創設。從概念發生史的角度考察,薩維尼提出這一概念的背景當是受到了以康德為代表的德意志理性意志哲學的直接影響。康德指出:“人,是主體,他有能力承擔加于他的行為。因此,道德的人格不是別的,它是受道德法則約束的一個有理性的人的自由。”[4]在康德看來,一個有理性的人之所以是自由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意志。因為,“意志是有生命東西的一種因果性,如若這些東西是有理性的,那么,自由就是這種因果性所固有的性質,它不受外來原因的限制,而獨立地起作用”[5]。著名的法律史學者維亞克爾認為:“一些相當有前瞻性的法律思想家,其中最重要的是Hugo、Feuerbach與薩維尼,早在1800年左右即基于各種不同的觀點認同康德的學說,自此,實證法之正義的問題乃根基于康德的人格及其倫理意志之自律性的倫理學,及其法秩序為實現最大自由,并使法律成員之自由得以并存的觀點。”[6]可以說,近代理性意志哲學是開啟廣義行為能力理論之門的一把“鑰匙”。
在薩維尼之后, 普赫塔(Puchta)[7]、溫德沙伊得(Windscheid)[8]等潘德克頓學者也在其著作中采納了這一概念,用以說明理性的意志能力是自然人所實施的法律上的行為能夠發生法律效果的內在準據。自此,廣義行為能力成為了德國法系中的一個基本法學概念。德國民法通說認為,廣義行為能力是使一個人實施的法律上的行為(Rechtshandlung)發生效力的一般性能力[9]。主體具有了廣義行為能力,其就可以實施法律上的行為,并能承受相應的法律后果。如果欠缺廣義行為能力,則人們不僅無法通過自己的行為取得權利,也無法通過自己的行為來行使權利[10]。由于“法律上的行為(Rechtshandlung)”主要包括法律行為(Rechtsgeschft)和侵權行為(unerlaubte Handlung)兩種 在德國民法上,“Rechtshandlung”是指“法律上的行為”或者“與法律相關的行為”,其包括了法律行為(Rechtsgeschft)、侵權行為(unerlaubte Handlung)和其他有法律意義的行為。,因此,廣義行為能力在邏輯上涵括了法律行為能力和侵權責任能力兩種具體的能力[11]。
雖然廣義行為能力(Handlungsfhigkeit)是德國法系中的一個基本法學概念,但是在德國民法典中并沒有廣義行為能力的一般性概念[12]。廣義行為能力只是學者在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抽象出來的一個上位法學概念,其目的旨在說明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之間具有共性或者同根性。一方面,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均是與“法律上的行為”有關的能力;另一方面,二者均與對此行為“承擔責任”有關:一個是對意思表示承擔責任,表意人要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另一個是對不法行為承擔責任[13]。事實上,廣義行為能力的價值也僅在于這種理論性的闡釋而無法為實踐提供更多的指引。因為,盡管均屬“法律上的行為”,畢竟法律行為與侵權行為存在性質上的差異,二者對于主體能力的要求自然不可一視同仁 對此,筆者將在后文詳細探討,此處不再展開。,這也是法律行為能力制度和責任能力制度能夠成為實證法上的制度,并在民法典中得以分別構建的內在根由。
因此,在德國民法上,廣義行為能力只具有理論上的意義而不具有實證法上的功能。不過,這種做法為蘇俄民法所打破。1922年制定的《蘇俄民法典》第7條規定:“已屆成年之人,有完全以自己行為取得民事上權利,及承擔民事上義務之能力(行為能力)。滿18歲者,為成年。”[14]對此,前蘇聯權威民法學者認為:“行為能力是人獨立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及用自己的行為取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對自己行為擔負責任的能力也是行為能力的要素之一。”[15]也就是說,蘇俄民法上的行為能力制度不僅包括了法律行為能力,也包括了責任能力,從而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
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和制度對新中國的民法理論和民事立法產生了深刻影響。在1958年出版的新中國第一本民法教材中,作者就認為:“所謂行為能力,就是國家給予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的能力或資格。享有行為能力的人,就可以用本身獨立的行為,去取得、實現民事權利和設定、履行民事義務,并且還要對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一切法律后果負完全的責任。”[16]不過,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及制度在我國民法學界的影響力就開始不斷衰減。隨著德國、日本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作品不斷地被介紹、引進到祖國大陸,我國民法學者開始對深受前蘇聯模式影響的我國民事行為能力理論及相關立法展開反思。例如,梁慧星教授在其于1996年出版的《民法總論》一書中,就從目的、效力和性質等三個層面論證了民事責任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存在不同,認為不能將二者混淆,并主張民事行為能力應采狹義之概念 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60.。經此反思和批判,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在我國的民法理論上由曾經的通說逐步淪為了個別說。
三、廣義行為能力理論之評價在大陸法系傳統民法上,廣義行為能力是自然人實施與法律相關的行為的能力[17]。無論該法律上的行為是法律行為,還是侵權行為,均要求行為主體具有相應的認識、辨別其行為性質及后果的主觀精神能力,即具有意志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漢語法學界普遍將德文單詞“Willensfhigkeit”翻譯為“意思能力”,但是這一譯法并沒有深刻地揭示這一單詞的內涵。“Willensfhigkeit”的本來涵義在于強調:自然人具有根據其意志實施有法律意義的行為的能力,這一能力的具備是法律賦予其行為以一定的法律效力的根據。因此,將其翻譯為“意志能力”更能貼合其原義,也能夠直接彰顯近代德意志的理性意志哲學對近代民法所產生的深刻影響。而將其翻譯為“意思能力”,則無法凸顯行為意志對于行為效力的決定性作用。。只有具備了這一能力,自然人所實施的舉動才能被評價為法律上的行為,并能承受相應的法律后果。欠缺意志能力的自然人由于不能辨識相關事務的性質和意義,也不能作出恰當的選擇,因而要求其承擔由此所產生的法律后果就會欠缺倫理上的正當性。哈耶克指出:“課以責任,因此也就預設了人具有采取理性行動的能力,而課以責任的目的則在于使他們的行動比他們在不具責任的情況下更具理性。”[18]而意志能力欠缺者顯然并不符合這種理性預設和課以責任的效果假定。
由于廣義行為能力是與人的行為有關的一種法律能力,而法律上的“行為”是指“吾人有意識的身體動靜”[19]。如果“吾人身體之動靜,而出于無意識者,亦不得謂之行為。必也基于有意識之身體動靜,始得謂之行為。”[20]因此,有學者將廣義行為能力界定為“人類有意識之身體動靜而能發生法律上效果之能力”[21]。這也反映了在法律上意志與行為之間具有不可分的關系——“某一行為要具有法律意義,它必須與意志相聯系:客觀的外在的行為只是一個外殼,其實質內容是意志,行為不過是意志的外在表示而已。”[22]因此,廣義行為能力實質上就是人的意志能力,即“主體表示意志的動作(能夠)成為行為的資格。”[23]行為人只有具備意志能力,法律才能確認其所實施的相關舉動表示了主體的意志,因而具有行為的意義,能夠產生相應的法律效果。意志能力欠缺者所實施的“行為”,只能被視為單純的舉動或動作,而無法接受法律的調整和評價。黑格爾指出:“行動使目前的定在發生某種變化,由于變化了的定在帶有‘我的東西這一抽象謂語,所以意志一般來說對其行動是有責任的。……行動只有作為意志的過錯才能歸責于我。”[24]因此,廣義行為能力理論的背后,深深地烙刻著古典自然法和理性意志哲學的印跡,彰顯了理性意志哲學對近代民法理論所產生的支配性影響 拉倫茨指出:“康德的倫理人格主義學說(ethischen Personalismus)對《德國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所產生的影響,類似于18世紀的自然法學說對《普魯士普通邦法》和《奧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制定者所產生的影響。”(參見:Karl Larenz, Manfred 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M]. 9.Aufl. Verlag C.H.Beck München , 2004: 21.)。
由于廣義行為能力在本質上是人的意志能力,而人的意志的正態運動構成了法律行為,反態運動則構成了侵權行為,從而能夠合乎邏輯地推導出廣義行為能力包括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兩種具體的民事能力。也就是說,廣義行為能力表達了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之間的“共性”。而在大陸法系的傳統民法中,廣義行為能力之所以沒有成為一項實證法上的制度 當然,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及制度是一個特例,對此,筆者將在后文進行探討。此外,需要說明的是,《瑞士民法典》中明確使用了“Handlungsfhigkeit”的術語。瑞士民法學者認為,盡管民法典中的Handlungsfhigkeit包括了法律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但是二者的內涵及功能并不相同,從而與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大異其趣,而更接近傳統民法上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參見:貝蒂納·許莉蔓-高樸,耶爾格·施密特.瑞士民法[M].紀海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207.),則是因為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之間的個性遠大于其共性。也就是說,盡管法律行為和侵權行為均是主體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實施的,但是這兩種行為類型所涉及的價值沖突和規范方式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前者涉及智慮不周者的保護與交易安全之間的協調,因而對于行為人的法律行為能力狀況需要有客觀統一的判斷標準;后者則涉及行為自由與損害救濟之間的平衡,因而需在具體個案中判斷行為人的責任能力狀況。“蓋不法行為系應受制裁之問題,理宜就具體情形決定,不適于依抽象的標準斷之也。”[19]
此外,盡管法律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均根植于人的意志能力,但是二者對于行為人的意志能力有著不同程度的要求。具體而言,在法律行為領域,行為人要積極地參與法律交往,其必須具備較高程度的意志能力,必須對相關利害具有正確的判斷計算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從而使其行為能夠取得預期的法律效果。因為,“法律行為是追求一種法效生活,需要有交往關系中平衡和合理計算利益的智慧”。[25]如果行為人不具有這種程度的認識能力和理解能力,其就不可能自主地參與法律交易,并為自己或他人創設相應的權利或義務。而在侵權行為領域,并不需要行為人通過自己的意志去積極地追求法律上的利益,其只要不去侵害別人的合法權益即可。而且,認識行為是非善惡的意志能力無論如何要比參與合同交易所需的意志能力低得多 大陸法系傳統民法理論將適用于非交易領域(侵權行為領域)的意志能力稱為“識別能力”,其理由即在于此。,“一個12歲的未成年人通常都知道打傷別人是不對的,但卻未必知道出租一套房屋的法律意義和風險”[26]。因此,對于意志能力的不同程度之要求,使得“民事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的抽象化程度不同,無法一體適用。”[27]調整市民生活關系的民法必須要顧及這種差別的存在而不能作劃一的處理,否則就有可能出現不當之結果。
正是因為法律行為與侵權行為存在著上述本質區別,使得法律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在具體的規范構造及適用中所面臨的個性遠遠超出其共性,這就決定了即便在立法上規定廣義行為能力制度,也難以在實踐中發揮應有的功效,也無從實現民法制度的體系化構造。因為廣義行為能力的本質是人的意志能力,雖然具有意志能力是主體的動作能夠被評價為法律上的行為并據此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的內在理據,然而為了維護法律交易的簡便性和安全性,不可能要求行為人在從事每一項法律行為之前,對相對人是否具有意志能力進行某種“成熟檢測”[10]。否則會極大地妨礙交易效率,損害交易安全,使法律秩序陷于極大的不確定性之中,最終也無法實現法律對行為和社會關系的有效調整。也有學者認為:“如果立法規定廣義行為能力,強調在法律調整的行為范疇內需有行為資格,無疑等同于對自然法則的重述,其價值不大。”[28]這就決定了廣義行為能力只具有概念或學理上的意義而不具有實證法上的功能。這也是近代民法專門對分別適用于交易領域和非交易領域中的民事能力,即法律行為能力和侵權責任能力進行明確規定的內在緣由,由此也實現了民法理論和制度構造的體系化。
不過,后來蘇俄民法對傳統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進行了實質改造,使之由一個只具有理論意義的法學概念上升為一個具有實定法效力的法定概念,并對我國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學說產生了深刻影響。但是這種將法律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不予區分、一體規定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均存在諸多難題 對此,筆者將在后文詳細探討,此處不再展開。。在我國的民法典編纂中,有無必要固守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實不無檢討之余地。當然,無可否認,傳統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仍有其合理性及認識論上的價值 事實上,盡管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受到了我國學者的批判,但是我國學者并不否認廣義行為能力本身所具有的重要的理論價值。例如,徐國棟教授就認為:“(廣義的)行為能力制度被一分為二:積極的行為能力是實施合法行為的能力;消極的行為能力是實施不法行為的能力,它們共同構成了一般的行為能力制度。”(參見:徐國棟.民法哲學[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180.)楊代雄教授更是明確指出:“關于民事責任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在概念層面上是什么關系之問題,筆者認為,民事責任能力是廣義民事行為能力的一種。”(參見:楊代雄.重思民事責任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的關系[J].法學論壇,2012(2).)。也就是說,包括民法在內的法律只能對意志支配下的行為進行法律調整,行為人具有意志能力是法律賦予其行為以相應的法律效果的根本原由。無論是法律行為還是侵權行為,均是在行為人的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實施的。作為分別調整上述兩種行為的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亦根植于自然人的意志能力,這種共性是客觀存在的。當然,我們承認廣義行為能力的價值,并不是主張將其改造成一個實定法上的概念,更不是主張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之間的個性已經不存在了。畢竟,“廣義民事行為能力概念,僅是學者理論上的一種概括,并不是要取代本義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這些概念區分,在法律技術上,這兩種能力實有區別標準的必要。”[25]
四、“變廣為狹”:我國民法典的應然選擇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宣布廢除國民政府時期的六法全書,掀起了全面向前蘇聯學習的時代浪潮。在這個過程中,我國自清末從日本輾轉繼受而來的傳統廣義行為能力理論亦隨之中斷,同時對前蘇聯民法上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和制度進行了全面吸收。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則》在第二章的公民(自然人)部分規定了民事行為能力制度。對此,無論是參與《民法通則》制定的學者,還是立法者,均認為《民法通則》中規定的是廣義民事行為能力。例如,由時任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室負責人的穆生秦主編的《民法通則》條文釋義書中,作者就明確指出:“行為能力不僅是指實施合法行為的能力,也包括對違法行為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29]在同時期的一本具有廣泛影響的民法教材中,作者也認為:“廣義的民事行為能力不僅包括實施民事法律行為等合法行為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不合法行為的能力,即對不法的實現和不履行義務行為負責的責任能力。從我國立法規定看,民事行為能力包括合法行為能力和不法行為能力兩方面的內容。”[30]
直接體現我國受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影響的法律條文是《民法通則》第133條。該條第1款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監護人盡了監護責任的,可以適當減輕他的民事責任。”該條雖然沒有直接對責任能力制度作出明確規定,但是主流觀點認為,從該條關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應由其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解釋,則不僅有民事責任能力之存在,而且將民事責任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相聯系:凡依法具有民事行為能力者,均具有民事責任能力 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8.。也就是說,該條實質上是將責任能力納入到民事行為能力制度中進行規定,并以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基本判斷標準,而這正是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的核心特征。
如前所述,在大陸法系的傳統民法理論體系中,廣義行為能力之概念僅是學者從理論上對法律行為能力和侵權責任能力之間的共性所作的一種概括,其本身并非一個實證法上的概念。因為,法律行為能力和侵權責任能力在適用的行為領域、制度構造機理、價值基礎等方面存在著本質區別 對此,請參見:鄭曉劍.侵權責任能力判斷標準之辨析[J].現代法學,2015(6).本文不再展開。,二者所涉及的價值沖突和規范方式也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這就決定了二者相互間的個性要遠遠超出其共性。因此,在傳統民法上,法律行為能力制度和責任能力制度是分別予以構造和規定的。但是,《蘇俄民法典》將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熔于一爐進行規定,從而對傳統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進行了實質改造,形成了頗具爭議的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
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的致命缺陷在于:由于其忽視了法律行為能力制度和責任能力制度之間存在的本質區別,從而難以實現妥當的法律調整。例如,一名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因暫時喪失識別能力而實施致害行為的情況下,因其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而可能需要承擔過于嚴苛的責任,而一名17歲的加害人即使嚴重侵害了別人的合法權益,其也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因為其不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我國《民法通則》第133條受到了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的深刻影響,將責任能力制度納入到行為能力制度中進行規定,并以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但是其并沒有完全照搬前蘇聯民法上的相關規定和做法。這突出表現在我國并不承認限制行為能力人具有責任能力,而根據《蘇俄民法典》第9條的規定,滿14歲的未成年人需要對因自己的行為而遭受損害之人承擔賠償責任,即承認限制行為能力人具有責任能力。。對此,有學者指出:“這種做法的優點是,簡便易行,但必須承認,其缺陷更為明顯,即嚴重忽視了侵權責任能力與法律行為能力之間的本質差異。”[31]
此外,前蘇聯模式也容易導致邏輯上的悖論。一般情況下,無行為能力人往往沒有責任能力,而完全行為能力的人往往同時具有責任能力,因此在實踐中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的主體范圍在很大程度上發生重疊。這也是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盡管存在種種缺陷但在實踐中仍能得以適用的原因 當然,這種適用是喪失以責任認定的精確性為代價的。誠如朱巖教授所言:“我國《侵權責任法》沿用了《民法通則》第133條的規定,在第32條中繼續以民事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在實踐中雖仍可勝任,但并不能掩蓋其理論上的偏差乃至錯誤,其適用于個案中的實際精準效果——個案正義頗值得再做深入考證。”(參見:朱巖.侵權責任法通論·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24.)。問題是:“如果因為二者在多數情況下發生同步,便認為行為能力‘包括責任能力;反言之,則也可以認定責任能力‘包含行為能力。”[32]只不過如此一來,既有的民法理論和制度體系恐怕要推倒重建了。因此,盡管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曾經長期占據我國民法理論的通說地位,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以梁慧星教授的《民法總論》的出版為標志,這一理論的影響力就日趨勢微。如今,就民事行為能力的教義學定位而言,狹義的民事行為能力(即法律行為能力)已經取代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而成為我國目前民法學界的通說。
不過,盡管目前我國民法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法律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之間存在著本質區別,主張在民法典中采用狹義的民事行為能力,但是很多學者仍然贊同現行法上的以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之判斷標準的做法。例如,梁慧星教授認為:“以民事行為能力之有無,作為判斷民事責任能力之根據,實有利于實務及對他人和社會利益之保護。因此,較通說為優。”[2]筆者以為,此種觀點的合理性亦值商榷。其一,這種觀點容易抹煞法律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之間存在的本質區別,從而與狹義的民事行為能力之主張形成邏輯上的悖論。因為,“行為能力既然包括不法能力怎能繼續稱為狹義?”[28]既然主張采用狹義的觀點來界定民事行為能力,就意味著承認責任能力的獨立性。在這樣的邏輯前提之下再主張以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無疑存在邏輯上的悖論,難以自圓其說。
其二,這種觀點難以充分發揮侵權法的教育、預防功能,不利于為具有識別能力的未成年人樹立良好的行為觀念和責任意識。根據我國現行法的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沒有責任能力,其對他人所造成的損害均由其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除非其擁有獨立財產),其本人并不用承擔任何民事上的責任。然而,這種做法在注重救濟受害人的同時,無疑“放縱了”責任意識淡漠的限制行為能力人,助長了其繼續實施侵權的可能性 例如,在“戴某某與馮某某等健康權、身體權糾紛上訴案”中,未成年人馮某某與不滿14周歲的幼女戴某某發生性關系,給戴某某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損害。二審法院在判決中認為:“馮某某不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戴某某要求馮某某承擔侵權責任缺乏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把板子全部打在了其監護人的身上。二審法院認為:“馮某某、黃某某作為馮某某的監護人,既沒有對馮某某進行正確的性教育,幫助馮某某合理控制青春期客觀存在的生理沖動,也未盡合理的監管義務,對家中留宿幼女毫不知情,使未滿16周歲的馮某某在不能充分認識自身行為的性質和法律后果的情況下,作出了與幼女戴某某發生性關系的侵權行為,依法應當承擔馮某某侵害戴某某合法權益的侵權責任。馮某某、黃某某的監護意識淡薄,監護措施不力,是本案侵權事實發生的重要原因力,且二人事后沒有及時采取補救措施以減少對戴某某的精神損害,過錯嚴重。現戴某某要求馮某某、黃某某承擔侵權責任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予以支持;但馮某某不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戴某某要求馮某某承擔侵權責任缺乏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如何教育馮某某以及預防其再次侵權,判決書中則根本沒有任何提及。(案例來源:“北大法寶司法案例數據庫”,【法寶引證碼】CLI.C.2143590。[2015-12-27])。。一般而言,限制行為能力人通常都具有一定的識別能力,能夠認知并判斷其所為事務的是非、善惡。一概否認其具有責任能力,使其不能對自己的過錯行為負責,并不能使其深刻認識侵權損害后果的嚴重性,遑論要求其對自己的行為方式作出必要且有效的調治與矯正。因而,我國現行法的規定并不能使限制行為能力人樹立良好的行為觀念和責任意識,也不利于其融入社會并習得必要的社會交往規則,從而影響其人格的健全發展,也會給社會帶來潛在的危害。比較法上一般規定,有識別能力的被監護人具有責任能力,其需要為自己的過錯侵權行為承擔賠償責任。這樣既可貫徹民法上的自己責任原則,也可實現侵權法上的教育、預防功能 參見:鄭曉劍.侵權責任能力與監護人責任規則之適用[J].法學,2015(6).。因而,被監護人的識別能力和責任能力狀況對監護人責任的承擔及其形態均有重大影響[33]。但是,類似這樣的規定在我國法上均付之闕如。
其三,這種觀點也無法妥當解決限制行為能力人所實施的法律行為和侵權行為在法效果上存在的評價矛盾問題。根據我國現行法的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獨立實施純獲利益的法律行為和經其法律代理人允許或同意的法律行為。即使其擅自實施了某種較為重大的法律行為,其效力也只是處于未定狀態,而并非當然歸于無效 根據《民法通則》第58條和《合同法》第47條的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經其法定代理人許可而實施的合同行為,屬于效力未定的法律行為,如果其實施的是依法不能獨立實施的單方行為,則該行為的效力應為無效。。但是現行法并不承認限制行為能力人具有責任能力,其所實施的侵權行為之后果均由其監護人承擔,其本人并不承擔任何責任(除非其擁有財產)。由是觀之,盡管同是限制行為能力人,然而其所實施的法律行為和侵權行為在我國現行法上卻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評價結果。對此,有學者指出:“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自己實質上具有理性能力而從法律交易中獲益,而卻完全不承擔因自己的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不利。這種惟使之獲益而不使之負侵權責任的做法,明顯不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31]因此,我國現行法對于限制行為能力人的責任能力問題所進行的異化處理,不僅與社會實情不符,也加劇了相關規則在理解和適用上的困難,難以從法理層面予以正當解說,亟需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解決。
由是觀之,以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之判斷標準的主張和做法,并不能取得合理、妥當的結果 除了筆者在正文中所探討的相關問題外,以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的主張和做法,還存在邏輯不周延、不能合理解釋刑事責任能力的最低年齡比侵權責任能力的最低年齡還要低的現象以及無法為司法實踐中過錯侵權責任的認定與承擔提供合理化論證等諸多不足。對此,筆者在相關論文中已有探討,茲不贅述。。此外,值得探討的是,本來傳統民法上的廣義行為能力同時包括了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二者分別作用于法律行為領域和侵權行為領域,但是我國學者在注重反思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之妥當性的同時,并沒有給予責任能力制度以應有的關注。在侵權法立法過程中,我國學者圍繞責任能力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但是,我國的立法者和相關學者對此之態度頗為消極 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中國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25;楊立新.侵權法總則[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324.。事實上,責任能力制度具有不能為行為能力制度所涵括的獨立價值和功能:其不僅可以在個案中起到強化過錯侵權責任之認定及承擔的合理性的效果,其還可以在宏觀上成為一把打通過錯侵權責任體系內部諸要素之間的邏輯關聯的“鑰匙”——其與監護人責任、過失相抵、共同侵權等具體的侵權法制度密切相關,可以為其提供統一的理論基礎和正當化說明,從而對整個過錯侵權法體系發生作用 對于侵權責任能力制度的獨立價值及其體系性功能的詳細探討,請參見:鄭曉劍.不應被淡化的侵權責任能力[J].法律科學,2011(6).。否認責任能力制度在實質上的存在或者主張淡化其價值,不僅可能會使過錯責任的認定與承擔失去應有的合理性而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和倫理危機 如過錯責任可能會淪為結果責任或者絕對責任,從而完全剝落了其天然具有的倫理色彩。,而且也會使得監護人責任、共同侵權、過失相抵等具體的侵權法制度因為缺乏必要的理論支撐,從而喪失其應有的理論基礎,成為彼此之間沒有內在邏輯牽連的規范疊合。
前已述及,傳統民法上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只是表達了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之間的共性,但是二者所涉及的價值沖突和規范方式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其個性遠大于其共性。也就是說,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只是有條件地屬于相同的問題:前者表達的是市民的自由,即可以通過法律允許的方式與他人協作以形成其法律關系;而后者則規定了將特定的義務和風險歸責于某人的前提[13]。蘇俄民法由于忽視了法律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之間的個性,將二者予以一體化構造和規定,從而引起了理論和實踐層面的諸多問題。因此,在我國的民法典編纂和民法總則立法過程中,我們需要正視二者在規范及價值層面所存在的本質區別,承認責任能力制度獨立存在的價值及其必要性。既需要對法律行為能力制度進行全面規定,也需要對責任能力制度作出專門規定。
目前,我國立法機關正在推進民法總則的制定工作,學界也推出了數個相關的草案 目前,最新推出的主要有中國法學會民法典編纂項目領導小組牽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民法總則專家建議稿(征求意見稿)》、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國民法典建議稿——總則編》和楊立新教授主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編(建議稿)》等幾個草案。。總的來看,這幾個草案均對民事行為能力制度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是只有梁慧星教授主持的草案對民事行為能力的概念進行了明確界定 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國民法典建議稿——總則編》第27條規定:“自然人的民事行為能力是自然人獨立實施法律行為、行使民事權利和履行民事義務的資格。”http://www.lawinnovation.com/html/xjdt/13752.shtml。[2015-12029]。筆者以為,為了避免出現不必要的爭論,有必要在民法典中對民事行為能力的概念作出明確規定。同時,為了厘清民事行為能力與侵權責任能力之間的關系,并為責任能力制度的立法提供必要的空間和余地,我們也不應在民法典中繼續沿襲前蘇聯模式的廣義民事行為能力理論及制度,而應當采用狹義的法律行為能力之概念和制度 筆者建議直接使用“法律行為能力”的稱謂:一來可以直接與“法律行為”相對接;二來可以免卻因使用“民事行為能力”之概念所引起的“廣義”與“狹義”的無謂爭論。。在此基礎上,我們也需要借鑒域外先進經驗,廢除現行法上的以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的做法,在侵權責任編中確立以“年齡+識別能力”的模式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 關于侵權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筆者已經專文進行了探討,參見:鄭曉劍.侵權責任能力判斷標準之辨析[J].現代法學,2015(6).此處不贅。。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在民法典編纂中變“廣義的”民事行為能力為“狹義的”法律行為能力!
五、結論在大陸法系傳統民法上,廣義行為能力是民法學者在法律行為能力和侵權責任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抽象出來的一個學理概念,其在本質上是人的意志能力。廣義行為能力理論之目的,旨在說明法律行為能力制度和侵權責任能力制度具有同根性,強調意志能力的具備是行為效力的發生根據,而不是要取代這些既有的概念類型。由于民事行為能力和侵權責任能力所涉及的價值沖突和規范方式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二者在具體的規范構造及適用中所面臨的個性也遠遠超出其共性,這就決定了反映二者之共性的廣義行為能力理論難以發揮實證法上的功能,二者在民法典中只能分別予以構造和規定。
我國現行法受到了前蘇聯模式的廣義行為能力制度的深刻影響,將責任能力納入到行為能力制度中進行處理,并以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基本判斷標準。但是,這種做法混淆了責任能力與行為能力之間存在的本質區別,抹煞了責任能力制度獨立存在的價值及其必要性。既不能合理解釋刑事責任能力的最低年齡比侵權責任能力的最低年齡還要低的現象,也無法妥當說明過錯責任之認定及承擔的法理邏輯和倫理基礎。而一概否認限制行為能力人具有責任能力,除了存在邏輯不周延的問題,也不利于為未成年人樹立良好的行為意識和責任觀念,難以充分發揮侵權法的教育、預防功能。此外,在現行法上,限制行為能力人所實施的法律行為和侵權行為在法效果上存在評價矛盾,違反了法律體系統一性的要求。
由于無論是主張行為能力涵括責任能力,還是贊成以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均存在著諸多難以消弭的缺陷;因此,要破解我國現行法上存在的上述問題,我們需要厘清法律行為能力與侵權責任能力之間的關系,并為責任能力制度的立法提供必要的空間和余地。在民法典編纂和民法總則的立法過程中,我們需要正視民事行為能力與侵權責任能力之間在規范及價值層面所存在的本質區別,承認責任能力制度獨立存在的價值及其必要性,對二者分別予以構造和規定,而不應在民法典中繼續沿襲前蘇聯模式的廣義民事行為能力理論及制度,更不能為了所謂操作方便而置相關制度的內在邏輯機理于不顧,而在立法上繼續混淆法律行為能力和侵權責任能力這兩個具有特定內涵、發揮特定功能的實證法概念。為此,筆者建議,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應當廢除現行的以行為能力包含責任能力、以行為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的做法,在民法總則中規定狹義的法律行為能力概念及制度,同時借鑒德國法上的做法,在民法典中確立以“年齡+識別能力”的模式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當然,民法典編纂是一項重大的系統工程,如何構造出科學合理的民事行為能力制度和侵權責任能力制度,端賴中國民法學人和全體法律人的共同努力!
ML
參考文獻:
[1] 李開國.民法總論[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3:94.
[2] 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7、69.
[3]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 Band3, Berlin, 1840: 22.
[4] 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M].沈叔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6.
[5] 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苗力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00.
[6] 弗朗茨·維亞克爾.近代私法史(下)[M].陳愛娥,黃建輝,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349.
[7] Georg Friedrich Puchta. Vorlesungen über das heutige rmische Recht Band1[M]. 3Aufl. Leipzig, 1852: 104-106.
[8] Bernhard Windscheid, Theodor Kipp. 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 Band 1[M]. 9.Aufl. Frankfurt am Main, 1906: 241-243.
[9] Karl Larenz, Manfred 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M]. 9.Aufl.Verlag C.H.Beck München, 2004: 110.
[10] Dieter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M]. 10.Aufl.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10: 428、222.
[11] 漢斯·布洛克斯,沃爾夫·迪特里希·瓦爾克.德國民法總論[M].張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419.
[12] Haimo Schack. BGB-Allgemeiner Teil[M]. 12.Aufl. C.F.Müller Verlag, 2008: 15.
[13] Dieter Schwab, Martin Lhnig. 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M]. 17. Aufl.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 2007: 75.
[14] 蘇俄民法典[M].王增潤,譯.北京:新華書店,1950:5.
[15] O·C·約菲.損害賠償的債[M].中央政法干部學校翻譯室,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52.
[16] 中央政法干部學校民法教研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基本問題[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61.
[17] Helmut Khler, BGB-Allgemeiner Teil[M]. 33. Aufl. Verlag C.H.Beck München , 2009: 256.
[18] 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鄧正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90-91.
[19] 鄭玉波.民法總則[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119,122.
[20] 張德周.契約與規范[M].臺北:文笙書局,1987:10.
[21] 詹森林,馮震宇,等.民法概要[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38.
[22] 薛軍.法律行為理論在歐洲私法史上的產生及術語表達問題研究[J].環球法律評論,2007 (1).
[23] 李錫鶴.民法哲學論稿[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119.
[24]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118-119.
[25] 龍衛球.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275,274-275.
[26] 楊代雄.適用范圍視角下民事責任能力之反思[J].法商研究,2011 (6).
[27] 陳幫鋒.民事責任能力:本源與異化[J].中外法學,2012 (2).
[28] 張弛.自然人行為能力新思考[J].法學,2009 (2).
[29] 穆生秦.民法通則釋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12.
[30] 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論(上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154.
[31] 朱廣新.被監護人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配置[J].蘇州大學學報,2011 (6).
[32] 尹田.民法典總則之理論與立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0:223.
[33]吳國平.成年人監護人的權利與責任解析[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10(5).
Abstract:Under traditional civil law of continental law system, the concept of general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is concluded from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and delictual capacity by scholars of civil law. In essence, the concept of general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is the will power of natural person.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is to reveal that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and delictual capacity have the same root instead of replacing these legal concepts. But in the civil code of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concept of general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of traditional civil law had been substantially transformed. As a result, general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became a legal concept which included delictual capacity. Whats more,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former Soviet Union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as civil legislation and theory. However, such transformation gave rise to lots of problem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one thing, it disregarded the basic distinction between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and delictual capacity, for another, it repudiated the value and necessity of delictual capacity. In a word, the concept of general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has an important meaning in theory and epistemology, but we should not adhere to the former Soviet Unions model of general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to stipulate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and delictual capacity systematically in future civil code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Key Words: general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delictual capacity; Civil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