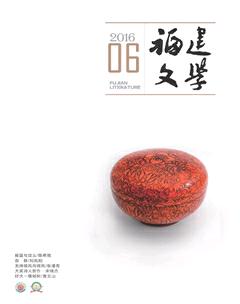白樂橋1號
肖世慶
2003年初春的一天,中國作協創聯部的李軍杰打來電話,問我最近忙不忙。我說不太忙,領導有什么指示?軍杰說作協在杭州的創作基地經過簡單維修,將重新對作家們開放。正式運行前,打算請幾個省的創聯部同志過來實地體驗一下,看看還有哪些需要改進的。你要是不太忙,就過來吧。
這樣,我千里迢迢從春寒料峭的東北,到了春風又綠的江南。下火車時,杭州的天還沒亮,街上正下著小雨。“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下車便沐浴在江南的春雨中,心內先感到了濕潤和溫暖。按作協傳真發來的地址,在濛濛夜色中花16元搭出租車,沿波光瀲滟的西子湖畔來到了靈隱寺附近的白樂橋1號——中國作協杭州創作基地。
是一棟白墻黑瓦古色古香的小樓,層疊起脊,造型別致,乍看像靈隱寺的附屬建筑,其實與靈隱寺毫無瓜葛,據說解放初這里曾是一處醬菜園子,50年代初被中國作協買下,作為江南的一處文學講習所,幾經滄桑,建設成如今這般模樣。綿綿雨絲中,小樓佇于翠竹樹叢里,極靜極幽,水墨畫一般。兩扇黑漆大門,被雨水淋得濕漉漉的。舉手敲門的剎那,腦子里竟涌出賈島的詩:“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被引進樓內之后,雨聲依然不絕,我還以為是房子漏了。抬頭一看,原來,門廳被設計成天井式,一方青天鑲嵌在廳堂上方,下面是一泓清澈見底的魚池,幾條金魚在池子里游來游去,雨點打在水面上,蕩起一串串漣漪......這天井是有名字的,叫“聽雨”。名字既雅又形象。廳堂上方開有天井,是江南一帶民居的特點,但未必都有名字。
天亮時,雨停了。出門便見著名的北高峰橫亙在眼前,云霧繚繞,青翠欲滴。峰下是一大片茶園,有茶農在侍弄一壟一壟梯田般的茶樹。我以為他們是在采龍井茶,但這里的人說,他們采的只是普通的明前茶,而非龍井茶。正宗的龍井要在梅家塢那里采。
順山腳下的小道漫步向前,不遠就到了靈隱寺的后門。所謂后門,只是一道放下來的細木欄桿,無人把守,隨意就可以繞進靈隱寺里。以后的幾天,我幾乎每天早晨都繞進靈隱寺晨練,跑步。沿著峰壁佛龕下的溪水跑步,格外的腳底生風。
“小白樓”的房后有一條深深的小河,系靈隱寺內的溪流匯集而成,隱在樓后面的綠地和樹叢里,快到白樂橋了,才見它從溝壑中蜿蜒出來,有時水大,有時水小,視雨晴而定。茶園的盡頭是連片的農舍,都是舊屋。靠近路邊,有幾家店鋪和農家小吃部,木門木窗木柵欄,店家和老板皆憨厚可愛。我在那里買過幾次啤酒,瓶子也不收押金。“知道你是那里的。”老板的下顎朝“小白樓”方向一揚,說道:“喝光了,喊章師傅他們送過來,沒關系的。”他說的章師傅是基地餐廳的廚師,人品和廚藝俱佳。所有來創作基地的人都吃過他的拿手菜:西湖醋魚、油燜筍、東坡肉......魚鮮,筍嫩,肉糯,燒的青菜也極為新鮮,且品種多樣。店鋪和小吃部的后面有一個依山而建的農貿市場,規模不小,什么都賣。章師傅說,作家們想吃什么,到那里現買都趕趟。我在那個市場逛了兩次,居然買到了江南的名吃——大陳島咸鰲魚。
創作基地里的服務人員不多。章師傅是一個,還有大劉、王寬和王戀,一共才四個人。操持如此規模的小基地,也是從早忙到晚。王戀是個小女孩,瘦瘦的,個子也不高。基地的領導大概想培養她,有時我們外出采風,也讓她跟著。記得,在胡雪巖故居拍紀念照時,她說什么也不肯跟大家合影。我們好說歹說,小姑娘才怯怯地站到了邊上......
我在基地逗留了不到一周,機關有事就把我叫回去了。臨別時,王戀捧來一本留言冊,讓我寫幾句話做紀念。我見在上面留言的都是名家,如河北作家何申等人。我說人家都是名人,我就免了吧。王戀說是領導讓我來的,你就寫了吧。恭敬不如從命,我便在上面寫了幾句:
“西湖最美三月間,
靈隱偷閑五六天。
(中間一句忘了)
離別留言贈王戀。”
十年前的杭州創作基地之行就這么結束了,時間雖然短暫,印象極深,白樂橋1號“僧敲月下門”的剎那間,像一幅江南美景,深深鐫刻在腦海。
然而,想不到的是十年后,2013年初冬,我突然接到通知,正式邀我去杭州創作基地休假。發通知函的經辦人仍是創聯部的李軍杰。
十年,我從中年步入到花甲之年。但那一次的江南之行,白樂橋1號“僧敲月下門”的一幕卻依然清晰如故。沒有絲毫的猶豫,我立即定了票,再赴江南舊地重游。
11月份,沈陽至杭州的高鐵還沒開通,旅途仍耗時兩宿一天。原以為我對杭州火車站一帶有印象,可是下車出了車站卻完全找不著北了。曾經寬闊的站前廣場,平地聳起一片鋼筋混凝土“森林”——過街天橋、高架橋、滾梯及車站廊橋的水泥柱子比比皆是,擁塞而混亂,給人處處碰壁之感。雖然午夜時分,這里竟還車水馬龍,亂哄哄的。好容易攔下一輛出租車,一問價錢,去靈隱白樂橋竟要價60元!十年前才16元,數字整個倒過來了。盡管單位給報銷出租車票,我也不能坐!太不像話了!
回到候車室,捱到了5點鐘,坐首發的7路公交車,終點就是靈隱寺。下了撤,還是找不著北——這里與火車站沒什么兩樣,一樣的鋼筋混凝土,一樣的處處碰壁之感。記憶中的汽車站不見了,7路車停在一個陌生的混凝土修建的豪華大院里,雕花的鋼鐵柵欄和水泥柱子代替了十年前的香樟樹林及林邊簡樸的汽車站牌。我像只沒頭蒼蠅在汽車站里亂轉,天麻麻亮時,才從一群早起晨練的大媽嘴里打聽到白樂橋的方位。
找到白樂橋,我徹底傻眼了。白樂橋對面一側的農舍和店鋪也不見了,一個龐然大物——“北高峰索道”橫亙在面前,轟隆轟隆,成串的纜車像一只只大鳥,從頭上掠過,在黎明的曙色中投下斑斑陰影。索道站的兩側被一些造型現代的建筑物占據得滿滿當當,左側好像是一個什么會館,而右側——當年的農貿市場蹤跡全無,花團錦簇的山坡上矗立著一幢幢洋房別墅。家家門前均停有豪車……十年前幽靜如畫的記憶被顛覆,我仿佛來到了城里的富人區。焦慮和疑惑油然而生:找錯地方了?白樂橋1號——杭州創作基地還在這里嗎?
憑記憶,順索道左側的小道向靈隱方向尋覓,卻被一道不銹鋼拉鏈門攔住了去路。門旁佇立一崗樓,上書:“靈隱風景區,外車禁入”。這里被列入風景區了?天沒亮,崗樓無人值守,我從側旁擠進去,發現了一座公家建筑——“靈隱泵站”,門牌上標注:白樂橋2號。有2號自然會有1號,可是,白樂橋1號在哪兒呢?正疑惑間,泵站里出來一個人,便向那人求助。你問的是作家協會吧?泵站的人很熱心,指著路對面的一處林叢,說那里就是。原來,十年間,竹木成林,已將小白樓遮擋住,不到近前很難發現它仍坐落在原處。
還是那條臺階,那兩扇黑漆大門,迎出來的竟也還是老人兒——大劉。大劉比十年前發福了,居然還記起我是“肖老師”。不止大劉,章師傅、王寬也都在,只是王戀走了。大劉說,基地的工作比較閉塞,與當地外界接觸不多,王戀在這里不好找對象,所以走了。除去少了一個小姑娘,白樂橋1號一切還保留著原貌。七八間簡樸的客房,雅致、溫馨的小餐廳,袖珍但精巧的茶室......還有“聽雨”等等,都原封不動地保留著。茶室的墻壁嵌貼的各地作家留言,走廊兩側懸掛的老中青作家在基地創作活動的留影,以及基地內設的“中國作家書庫”等文學元素,無聲地記錄著作家們跋涉的足跡。
基地后院的那一小塊綠地不見擴大,也未見縮小,院子里的那兩棵香樟長到一人腰粗了,樹下的一塊巨石上鐫刻著巴金先生的親筆留言:
“這真是我的家。我忘不了在這里過的愉快的兩個星期。謝謝你們。”
留言的時間是1990年10月14日。當時巴金先生是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來杭州的,他沒在官方為他安排的住處下榻,卻在簡樸的創作基地住了近半個月。老人家和我們一樣,把白樂橋1號當成自己的家了。這次和我一起來創作基地休假的中國作協柯小衛先生在小院里招待來看望他的杭州親屬,章師傅給他們添了幾個小菜,一家人在樹下把酒敘親情,樹葉兒也來湊熱鬧,不時地往碟子里掉……十分有趣。柯先生的親屬說,他在杭州這么多年,頭一次走進這座“小白樓”,想不到靈隱寺這里還能有這么一塊凈土。難得啊。
與如今的周邊環境比較,白樂橋1號算得上是一處凈土。能保有這一塊凈土實屬不易。杭州的房價與京滬廣相差無幾,靈隱這片寶地的地價估計也低不到哪兒去。大劉告訴我,北高峰下面的那片農舍、店鋪和農貿市場的地皮先是被政府收購,然后租給一些成功人士,建起了別墅和會館等設施。那些人也不在這里住,只是談生意或招待親友到杭州游玩時,才小住一陣。平時基本閑置著,旅游旺季也有臨時接待游客的。時至初冬,來靈隱寺燒香拜佛、祈福求財的人整天人山人海,靈隱寺的門票已從十年前的20元漲到了80元。靈隱的后門也建了售票室,24小時有人把門收票。再想進靈隱跑步晨練,得掏腰包了。“小白樓”對面的那片茶園也身價大漲,由普通茶園變成了“龍井茶種植基地”。龍井茶現今已賣到了天價,插著“龍井茶種植基地”標牌的茶園向“小白樓”前的小道擴張了大約兩條壟溝,使原來就很窄的小路成了羊腸小道,幾乎頂到了“小白樓”的臺階。
回首再看“小白樓”,我不由心生敬畏。十年之間,周圍的一切都變了,唯有它還能保持原貌,固守在白樂橋1號,以不變應萬變,不能不令人驚嘆文學的力量。這樣一塊寶地,這樣一處雅致的建筑,不會沒有人覬覦,不會沒人打它的主意。它至今還能完好無損地存在著,皆源于人民心中有文學。只要文學沒在人心中消亡,它也不會消失。如同與它比鄰的古剎靈隱。佛在,寺便在。
責任編輯 陳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