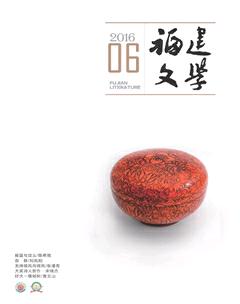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張家鴻
說起豐子愷先生,關(guān)于他的身份,人們所能想到的是“漫畫家”、“美術(shù)教育家”與“散文家”。這幾個身份是對豐子愷先生文學藝術(shù)成就的公正評價,亦可以說它們是豐子愷先生的歷史身份。除此之外,豐子愷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常身份,那就是教師。我亦忝列教師隊伍之中,品讀此書,斗膽地說,我似在尋找一種精神標桿。雖不自量力,然心向往之。
這本《教師日記》的寫作時間起于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的十月二十四日,止于次年的六月二十四日,前后時間的跨度恰好八個月整,是豐子愷先生于抗戰(zhàn)期間流寓廣西桂林擔任教職時的日常詳細記錄。我平素喜歡讀傳記、回憶錄、書信集等散發(fā)出鮮活氣息的書籍,其中最吸引我的當屬日記。日記,是最接近本來面目的第一手材料,瑣碎、生動、新鮮。品讀此書,如親見歷史,可以觸摸到它真實可感的溫度。
此書名為“教師日記”,“教師”二字旨在于強調(diào)作者的職業(yè)或身份,然而日記中所記之人所論之事并不局限于學校之內(nèi)課堂之上,而是拓展涉及廣闊無邊的人與事,以及硝煙彌漫國破家亡的時代背景。在好奇心的推動下,我一個字一個字,一行行一行行地仔細爬梳、揣摩、感悟著。
在1938年12月9日的日記中,豐子愷先生慷慨激昂地抒發(fā)著自己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念,“今日吾民族正當生死存亡之關(guān)頭,多些麻煩,誠不算苦。吾等要自勵不屈不撓之精神,以為國民表式。此亦一種教育,此亦一種抗戰(zhàn)。”在先生眼中,教育即為抗戰(zhàn),而且是最為特殊最為持久的抗戰(zhàn),對于抗戰(zhàn)的全面勝利,教育起著不可忽視的推動和促進作用。身肩如此重擔的教師,定然是個勇敢的戰(zhàn)士。
同是1938年的早些時候,先生即寫過“凡武力侵略,必不能持久。日本遲早必敗”,真是擲地有聲,如雷貫耳,振奮人心。寫下這一行字的當時,正值抗戰(zhàn)最艱苦的階段,更可見其實為見識與信念兼具的可貴言論。在日記里,可見先生的痛心與怒氣,亦可見先生的牢騷與擔憂,但絕對見不到哪怕一點點的頹唐與消沉。即使面對一個陌生小女孩的新墳,先生亦可樹起“不久當有凱歌迎爾歸葬于西湖之旁也”之信念。這個戰(zhàn)士以思想為武器,在教育的戰(zhàn)線上,執(zhí)筆勝過刀槍,在學生們的心靈里種下一株株參天大樹,以抵擋亂世的狂風暴雨。
我很珍視1939年1月19日這一天的日記,這一天里,豐子愷先生慷慨激昂地寫道:“我等側(cè)身文化教育界者,正宜及時努力,驅(qū)除過去一切弊端,必使一切事業(yè)本乎天理,合乎人情。凡本天理,未有不合人情者;凡合乎人情,亦未有不成功者。”作為一個不上前線的戰(zhàn)士,先生沒有子彈,先生只有一顆努力實現(xiàn)“本乎天理,合乎人情”之理想境界的心。一顆火熱的心,在邊陲之地悄悄地燃燒著。幸而有《教師日記》留傳后世,否則抗戰(zhàn)史中則埋沒了一道鮮明的印記,一道亮麗的風景。在先生眼里,“本乎天理,合乎人情”乃凡事成功之關(guān)鍵。這關(guān)鍵之道,看似宏偉,看似壯觀,實則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卻顯得格外繁瑣、細碎,甚至在許多人眼中,可能顯得不值一提。但是,它們卻是我在這本書里竭力尋找的光芒,可以劃破時代暗夜的光芒。
回憶起初來乍到時,先生寫道:“我被邀請到桂林時,會見校長,即承告‘以藝術(shù)興學、‘以禮樂治校之旨。此旨實比抗戰(zhàn)建國更為高遠。我甚欽佩,同時又甚膽怯——怕自己不勝教師之任。”“膽怯”二字恰恰體現(xiàn)了先生如履薄冰誠惶誠恐的真實心態(tài),擔心之余,還有憧憬,勉力為之可也。于是,作為讀者的我才見到那個桂師的美術(shù)教員兼國文教員,那個已過不惑之年的豐子愷。
11月1日,先生自言自語道:“因為我未諳他們的性格,尚不能決定教學的方針。”這是懂得教育又憂心忡忡的老師。11月8日,先生要求學生寫作時,“標點不準亂用,字不許潦草。潦草者不給改。”這是對學生的要求嚴格到近乎苛刻的老師。11月26日,“不求學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畫,但求涵養(yǎng)其愛美之心。能用作畫一般的心來處理生活,對付人世,則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為藝術(shù)的最大效用。”這是對教育之美好未來有巨大期盼的老師。12月1日,“昨天,昨天下午,你們那組人正在對著所畫的無頭嬰兒哄堂大笑的時候,七十里外的桂林城中,正在實演這種慘劇,也許比我所畫的更慘。”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老師。相對于“授業(yè)”“解惑”來講,“傳道”應(yīng)是教師的第一天職,也是教育的第一要義。所傳之道,并非是一味形而上學之道,而是做人的基本道理,熱愛生命又是其中最為懇切與重要的。熱愛生命,熱愛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包括漠不相關(guān)的陌生人的。是的,在成長階段里,促成學生形成對生命的敬畏之心,進而養(yǎng)成悲憫之心,豈不是功德無量的善舉?
這些貌似樸實簡單的話語,無不“本乎天理”,無不“合乎人情”,而在彰顯著一個藝術(shù)家令人崇敬的教育思想。逢著戰(zhàn)亂時代,先生不因?qū)W生基礎(chǔ)水平的粗淺而降低對學生的要求,亦不因校舍的簡陋與環(huán)境的惡劣而有絲毫的隨意應(yīng)付,如此作為怎能不讓如今的教育者汗顏?將心比心之后,我們能從這本書里得到的思考與啟發(fā)實在太多。
身為教育者,身為閱讀者,身為一個且呼吸且行走的普通人,多年以后,我仍會記著豐子愷先生那顆可貴的反省向?qū)W之心。1938年12月2日,當先生以“桂林城里受難,你們鄉(xiāng)下就很好”的言語來安慰目不識丁的鄰人時,鄰人搖搖頭回答:“要大家好才好!”這看似平常的一句話引起了先生的肅然起敬。先生寫道:“我目送他。此是仁者之言,我用尊敬的眼光送他回家。”這于日常瑣事中切實而鄭重地向下看的藝術(shù)家,世間能有幾個?不僅如此,在尋常的買賣中,先生亦會發(fā)現(xiàn)商人的“用心誠善”。
由此可見,先生在抗戰(zhàn)歲月里,不僅高舉著理想的旗幟與必勝的信念,更睜開著一雙藝術(shù)的眼睛,發(fā)現(xiàn)并記錄著普通百姓身上德行的美。這是一種志存高遠的低頭,埋首于平凡的人群里,擷取更多的地氣,久而久之,正可以提升自己的藝術(shù)境界。《圣經(jīng)》有言:“眼睛就是身上的燈。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在豐子愷先生擁有輝煌成就的一生里,這八個月的教書生涯并不驚天動地,并不精彩紛呈,甚至顯得平凡普通。然而,我卻覺得這段經(jīng)歷著實珍貴。真正的藝術(shù)家投身教育,總是毅然決然,高擎理想主義的旗幟,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
戰(zhàn)爭的出現(xiàn)固然是國家與百姓的大不幸,然而此不幸中亦有幸運。幸運之處在于大師們因環(huán)境的艱難、謀生的不易等諸多因素的存在,要么身不由己要么心甘情愿地身居中學教職。大師們進入中學,不僅是所在學校學生之福,亦為國家民族之福。自從民國以來的文化傳播中,他們影響著一代代年輕人,走向覺醒,走向抗爭,走向追趕理想的道路。我猶記得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亦記得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大師們在課堂上的言傳身教,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中國教育史上。大師們在中學里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般的辛勤耕耘,最讓我感動的并非高深的學問,亦非高明的思想,而是他們對學生的高度責任心以及傾注于每一個學生身上的深情厚誼。
如果教育辦不好,國家就不會有美好可期之未來。戰(zhàn)爭越是瘋狂,教育越是需要堅持,越是需要這些投身教育的知識分子兢兢業(yè)業(yè)地貢獻光和熱。即使亡國了,教育也可以為國家保留著源遠流長的文化血脈。在這個功利化的社會里,閱讀《教師日記》是一種別樣的返璞歸真,是品味一道思想盛宴,這其中既有關(guān)于教育的真知灼見,更有在艱難困境中迎難而上的卓絕勇毅,以及心憂天下的大師風范。
弘一法師李叔同是豐子愷先生的恩師,他們之間的往事所在不少,然而最讓我刻骨銘心的是與《護生畫集》有關(guān)的點點滴滴。晚年豐子愷在政治動亂的歲月里,不顧老邁之軀,依然信守對恩師的承諾,完成了最后的一幅幅作品,雖然筆力不及當年,筆墨里汩汩流出的風采卻始終依然,一只鵝的“聽課誦”,一只鱉的孤獨,一條狗的失蹤,一個個日常的畫面,在豐子愷眼中,都是生命偉力的自然展示與完美呈現(xiàn),都可以引起內(nèi)心的深刻感觸。這是作為學生的豐子愷,他的畫筆流布人間的是對世間一切生命的敬意,以及深蘊其中的眾生平等的博愛之心。不管是身為教師,還是扮演學生的角色,豐子愷始終是豐子愷,沒有絲毫的褪色。大師與否,并不僅僅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擁有多大的影響力,更在于在低頭俯視人間萬物的時候,擁有一顆與生俱來的良善之心。這顆良善之心,時時刻刻地促成了他的作品與普羅大眾的無縫對接,作品中的一字一句無時無刻地影響著每一個愿意諦聽的平凡人等。
在這個“大師”滿天飛的時代里,真正的大師是嚴重稀缺的。嗚呼,媒體話語如此強勢,但凡在某個領(lǐng)域里出類拔萃、稍有成果的人,總是身不由己地被冠上“大師”的名號。面對此情此境,清醒者,不以為然;渾噩者滿足者,享受之余還飄飄然。于是乎,久而久之,大師的內(nèi)涵與外延也就漸漸顯出窮山惡水的面貌了。
回顧往昔,大師的聲音振聾發(fā)聵;環(huán)顧而今,大師的背影漸行漸遠。此時此刻,我想起了范仲淹在《嚴先生祠堂記》中對嚴子陵的動人贊許:“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發(fā)自肺腑的贊許用在豐子愷先生身上,應(yīng)當也是可以的吧!
責任編輯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