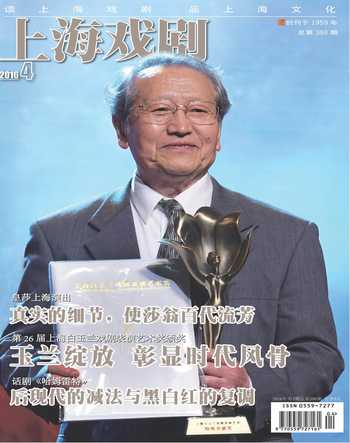是比較,更是對話
夢珂
陳靝沅簡介
陳靝沅(Tian Yuan Tan),1972年生,新加坡人。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現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同時擔任歐洲漢學學會秘書長。著有專書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哈佛大學出版社,2010年)、《康海散曲集校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Text, 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sic: Essays in Honor of Wilt Idema(合編)(荷蘭萊頓布里爾出版社,2009年),《英語世界的湯顯祖研究論著選譯》(與徐永明合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并與羅馬大學Paolo Santangelo教授合作研究《牡丹亭》中的情感用語。
今年是莎士比亞和湯顯祖逝世400周年。在英國,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陳靝沅教授及臺灣大學汪詩珮教授主編的《1616:莎士比亞和湯顯祖》一書正式出版,標致兩國戲劇文化的交流翻開了一個新的篇章。本刊就本書對陳教授進行了專訪。
夢:陳教授您好。可以先簡單介紹一下這本書的來由嗎?
陳:好的。這本書是在兩年前亞非舉辦的學術會議“美麗新劇場:1616年的中國和英格蘭”的基礎上集結出版的。最早的想法是我在美國念博士時選擇了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一門課。課上老師問,1616年發生了什么事?很明顯,老師的標準答案就是莎士比亞的去世,以及本·瓊生《第一對開本》發行,這是在英國戲劇史上第一次戲劇文類進入個人文集。
夢:也是文學出版,戲劇堂而皇之地登入了文學的大雅之堂。
陳:對,非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學出版。所以授課老師當時想的應該就是這兩個答案吧。
夢:但是對您來說,可能第一反應是湯顯祖的逝世吧。
陳:不僅僅是湯顯祖的逝世,我也想到了臧懋循的《元人百種》。接受中國文學訓練的人,會想到我們文化中重要的事件,他們也會想到他們的。所以我就希望能寫一本書,處理一下1616年這個中西戲劇史上重要的一年。之后和遂昌政府以及莎士比亞基金會合作,終于完成了自己的一個心愿。
夢:書里面有什么令人印象比較深刻或者耳目一新的內容?
陳:我覺得它意義重大的一點,可能是這本書的設計。我認為它必須要是對話的形式,所以我們當時擬定了十個議題,每一個議題都請同一個領域的中英兩位學者進行一個對話。后來我們索性再進一步,為了讓對話性更強,我們決定同一個議題的兩位學者互評對方的論文。
夢:相當于讓他們必須去了解對方在說什么。
陳:是這樣的沒錯。(笑)我覺得這樣意義還是很大的,因為我們所說的對視、對話,這和我們一般所說的比較文學還不太一樣。
夢:說到比較文學,一直也有反對的聲音存在。如果是互有影響的文學傳統,比如中國和越南,英國和法國,在影響的基礎上做比較文學會比較容易。然而中國戲劇和英國戲劇,是在各自的文化傳統上獨立形成的,彼此之間并沒有交流和影響。如何去打下一個對視、比較的基礎呢?
陳:更為確鑿的文學傳播研究也有人在做,而這本書的想法則是鎖定了1616年作為對視和比較的基礎。否則的話,比較的點會太寬泛。
夢:這樣可能就會偏向跨文化研究了。它不應該是簡單地指出彼此的同與不同,而是將同一個文本放到不同的文化語境中,解決舊的問題,發現新的問題。比如說戲劇起源這樣的問題,在英國戲劇學界也是爭論不休。有說是宗教劇的世俗化,也有強調經濟基礎的,但似乎不太強調它的文學性。而相反,在中國戲劇的文化傳統中,雖然也有祭祀說、優伶傳統等不同的說法,但總體來說,尤其是到了湯顯祖這個時期,其核心還是一脈相承的中國文學。在這本書里,有沒有深入探討這類問題的呢?
陳:你說的也正是莎士比亞和湯顯祖這兩個劇作家最大的不同。莎士比亞是一個商業劇作家,而湯顯祖是個百分之百的文人作家。然而把他們放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就會發現無論是湯顯祖還是莎士比亞,都是很多面的。整個晚明和明清,戲劇在宮廷里的表演、在民間的表演也非常興盛,但我們的文學史戲劇史幾乎只注意到了文人創作的傳奇和雜劇。
夢:是的,文學系和戲劇系的教材也是這么教的。(笑)
陳:是呀,你看我們現在所謂的“戲劇研究”和“曲學研究”的分化,也正是因此而來,現在也走向了幾乎是完全不同的領域。我現在在研究的清代宮廷文人劇,也有想要融合這兩個領域的想法。
夢:宮廷這一塊也非常有意思,因為其實莎士比亞也是個宮廷的“御用劇作家”。
陳:但莎士比亞的情況又更特殊一點。他雖然也是宮廷劇作家,但他的作品一般都是在商業劇場先進行演出,再引進到宮廷里。晚期的中國宮廷劇則是專門為了宮廷進行編演的。
夢:而且宮廷劇似乎有更多儀式性的內容,比如莎士比亞時期的戲劇,會在劇中插入假面舞會。
陳:對,這種儀式性的橋段,在清代的宮廷戲里就非常明顯。尤其是當我們比較同一部作品的不同文本,就可以發現宮廷演出本會加入大量儀式性的橋段。所以如果只研究文人戲劇是不充足的,因為在以案頭為導向的文人戲劇中,儀式性的內容很不常見。
夢:說到案頭劇,似乎案頭劇也并非中國傳統戲曲獨有,莎士比亞時期的英國戲劇也有非常多的、并沒有表演過的案頭劇。這個情況在本書中有沒有討論到呢?
陳:我們當時開會有幾個主題比較有意思,其中一個就是你提到的這個案頭劇的情況。我們一直在提晚明文人戲劇(literati)的時候,對英國的學者來說,一個似乎可以拿來作對照的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學才子劇作家(university wits)。
夢:比如馬洛?
陳:對,可是除了馬洛別人你也叫不出來了吧。(笑)在英國的商業戲劇文化下,這些劇作家基本沒有在戲劇史上留下名字的。而反觀我們晚明時期的中國劇壇,現在保留下來的,大部分都是文人劇作。所以你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從歷史的相似性、劇作家的出身這些方面來找一個對應的話,那就是大學才子和文人劇作家。
夢:可是其實根本對不上。
陳:對不上(點頭)。比起這種看上去可比的相似性,我們還是選擇了1616年,在那個時空的語境下對談。我們可以談室內/室外劇場,我們可以談商業戲劇,可以談案頭劇。在特定的時空語境下,你剛才說的地基,會更好地建立起來。
夢:還是那句話,不能為了比而比。比較和對話都是為了發現新的意義的。
陳:這次還有一個問題是比較吸引人的,就是地域性(locality)的問題。
夢:比如說中國的江南,和英國的倫敦?
陳:對。但是你也知道,江南有多大,倫敦有多小。這是其一。其二,即使江南內部,差別也非常大。與會的英國戲劇學者就非常驚訝,中國戲劇的空間跨度可以有這么大。劇作家在他的出生地、任職的地方、退休的地方、交友的圈子都會有他創作的痕跡。但是同樣的情況在英國戲劇就不太可能了,大家都來倫敦,倫敦就是焦點。
夢:可能就是以泰晤士河南岸的那些劇場為主。
陳:對。我們書里有一張1616年的倫敦地圖,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倫敦劇場的分布。原因是什么?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就是因為英國戲劇是商業劇場的傳統,而商業經濟中心就是在倫敦。
夢:而中國晚明這一塊的劇場,主要的演出形式還是私人家班而不是商業演出。
陳:家班是一方面。我自己的論文里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其實宮廷對我們戲劇的發展影響非常大。晚明宮廷到底怎么演戲?我們大家都不知道。如果對內府本進行研究,就會發現一些線索。比如晚明劇本如果要進入宮廷的話,就必須上交所謂史官來評定,其實有點像審查(censorship)。
夢:審查也是可以對話的一個點。
陳:對。英國戲劇你也知道,審查戲劇的制度很嚴格。
夢:好多劇作家都因此進監獄了。
陳:對,這個領域在英國戲劇研究得非常充分。但是相比之下,晚明劇壇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不足的。同時期英國戲劇的檔案保存得都很好,而中國可能需要等到18世紀才有更為系統化的記錄和類似升平署的演出機構,慢慢才有宮廷戲劇這個概念。
夢:所以資料的完整性也是一個焦點。
陳:對,還有可比性。那時候的戲劇審查制度是非常可比的。但是因為資料的匱乏,所以現在研究晚明宮廷劇壇只能曲線救國。我自己的論文就是通過幾十部晚明內府本的劇作,來大概猜想、考察晚明時期的宮廷戲劇演出。
夢:那這本書里,有沒有探究雙方對于戲劇整體性、戲劇本質的觀念呢?
陳:這些問題都是我們現在懸而未決的大問題。比如,中國戲曲到底怎么翻?
夢:現在好像都直接用拼音。
陳:對,我自己的做法是視受眾而定。如果是一個面向普羅大眾的講座,我可能會用opera,因為感官上非常直觀。但是作為一個學者,opera不是一個足夠理想的詞。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兩個戲劇傳統的學者坐在一起,還是有很多鴻溝需要去解決。比如courtesan和名妓是不是也是對等的?因為名妓的文化內涵和西方所謂高等妓女還是不一樣的。結果用了geisha(藝伎)一詞,英國的學者反而更好理解了。
夢:從翻譯的技術性問題出發,為什么沒有辦法翻譯?可能就是因為詞語背后的文化內涵、語境都不一樣。
陳:文人、名妓、地域,究其根本還是中英戲劇場域不同,劇作家不同,階層不同。正是因為諸多不同,我認為才有交流和對話的必要。其實本書的一部分是比較總結介紹性的,再在介紹的基礎上推進。1616年這個點是為了讓學者也可以在學術上有所建樹。
夢:您之前說了許多不同點,可以說說雙方戲劇的共同點嗎?
陳:其實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焦慮感。從劇作家和出版商的角度來說,都有這樣一種焦慮。書里面有篇英國學者的文章談到的就是著作權(authorship)這個問題。
夢:還有版本眾多好像也是共同點。《哈姆雷特》有三個版本,《李爾王》有兩個版本,湯顯祖的臨川四夢改本也很多。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否也可以互相聯系呢?
陳:比如《牡丹亭》有一個宮廷本就刪除了所有和抗金有關的場面。這個例子就可以說明即使是同一個文化傳統,形成多版本的原因也是非常多的,有商業本,案頭本,也有宮廷本。這就可以看出另一個共同點,就是戲劇文本的不穩定性,并且現在的趨勢越來越尊重不同的版本,而不是說一定要評定一個“最佳版本”。
夢:這種文本不固定性也是多元文化的一種體現吧。
陳:我覺得是的。在所有文學文類來說,戲劇文本不穩定的程度太高了。
夢:是的,文人改本外還有職業戲班的改本。
陳: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很值得交流和對話,因為兩種文化傳統,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別的包括文獻方面,理論方面,都還是有很多對話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