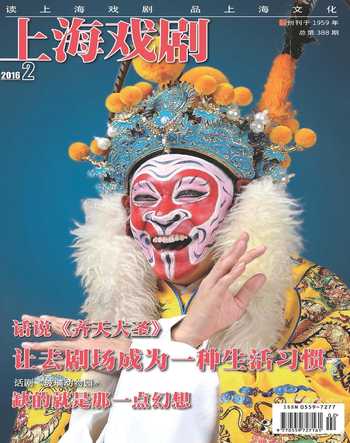演一出戲等于了解一個人
朱木喬
新編滬劇《鄧世昌》以甲午海戰為背景,演出了一曲蕩氣回腸的英雄故事。作為滬劇一部難得的宏大壯美的史詩戲,青年演員朱儉飾演了主角鄧世昌,塑造了一位可親可敬而又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很慶幸,這一次了解的是這么一個偉大的人,他叫鄧世昌。”朱儉這樣說道。
希望每一個細節都能符合“鄧大人”
上海滬劇院曾在上世紀60年代排過一部《甲午海戰》,但是這次的《鄧世昌》完全是另起爐灶,新寫新編。劇本策劃了三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創作過程。作為上海滬劇院的優秀演員,《鄧世昌》就是為朱儉量身定制的作品,院長茅善玉希望這部作品能成為朱儉的代表作。盡管有電影銀幕上熠熠生輝的李默然版的《甲午風云》和滬劇《甲午海戰》在先,但朱儉對《鄧世昌》并沒有很大的壓力,他說:“我的滬劇演藝生涯已經二十多年,一直想演一個男人戲,接到劇本感到非常興奮,完全沒有感到緊張。有人覺得從外形上說,我并不是很適合鄧世昌,演員沒有適合不適合,每個演員都有自己的體系和路數,但不管是怎樣的路數,他演的是一個人,一個人物。我并不想從外形上達到‘像,我要做的是精神的神似;我會去想,他為什么要這么做,我把演戲當課題來做,演一出戲等于了解一個人。”
但是創作的過程依然艱苦,為了演好這部戲,朱儉付出了相比以往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回想創作過程,朱儉確實有很多的感慨,他說:“我小時候看過李默然先生主演的《甲午風云》,他的鄧世昌形象已經深深印刻在觀眾腦海里,我在排練過程中也回顧了李默然老師的表演,并向曾經在滬劇《甲午海戰》中鄧世昌的扮演者張清老師學習了很多。另外,我花了兩年多的時間了解這個人物、接近這個人物。到2016年,我收集和翻閱了大概三十六本關于甲午海戰的書和資料。我很慶幸有那么長的準備期,可以去了解北洋水師,了解致遠艦,了解鄧世昌,了解這么一個活生生的人。”
當問及朱儉怎樣讓自己向鄧世昌靠攏時,他說他的方法是“不當英雄”:“很多人一看到‘鄧世昌,就覺得他是個英雄;但是我認為,鄧大人要求撞沉吉野是他的決定,我們后輩知道了他的壯舉,所以稱他為英雄。但是他在做這件事情的瞬間,沒把自己當英雄。所以我們這個團隊包括陳薪伊導演、蔣東敏編劇和茅善玉院長,達成了一個統一的人物構想:鄧世昌是一個充滿情感的人,他有愛情、親情、友情,更有家國情懷。正是因為他的情感,他才愿意付出他的生命。這次演出就有很多觀眾問我舞臺上的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說我也沒有多想,只是要把鄧世昌的心路歷程盡可能表現得使人信服,能夠在撞沉吉野那一刻達成高潮,要讓觀眾相信鄧世昌是從一個意氣奮發的年輕人逐漸成為為國獻身的英雄,而不是直接告訴觀眾,我是一個英雄。”
滬劇的念白大都是平常說話的口氣,在《鄧世昌》中,為了達到足夠的氣勢,也為了體現鄧世昌的性格,朱儉整個處于一種“嘶吼”狀態,光是鄧世昌向李鴻章討軍餉的一出戲就排了三天。“我在上場門和下場門每天都放兩大杯消炎沖劑;排練廳里則堆放著喉寶、西瓜霜含片、響聲丸……哪怕是下臺十幾秒鐘,單位里都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員為我端藥送水;吃這些藥不僅是為了當天的演出,更是為了明天、后天,為了每一天花錢買票來看戲的觀眾。”排練中,只要感覺沒有達到規定情緒就得重來,一遍又一遍的重來使得朱儉的嗓子在2014年7月開排到12月份首演之前一直是啞的。茅善玉院長和陳薪伊導演建議朱儉在排練中不一定要那么“歇斯底里”,可以適當“減負”;但朱儉堅持著:“可能外表的戲到了,但是我自知內心的戲還是沒到。我希望自己體內的一切都能屬于鄧大人,希望每一個細節都能符合鄧大人。”
在排練過程中,他感覺到了一種深深的責任感,為此他特地塑造了一尊鄧世昌的像,這尊像就放在舞臺的臺口。“不論身處逸夫舞臺還是北京梅蘭芳大戲院,每次演出前,我都會早早地候場,站在最高處,雙手合十對天,心中默念‘朱儉在此拜見一百二十年前海底之魂鄧大人,天上之靈鄧公,來表達對鄧世昌的尊重和敬意。” 朱儉如是說。
為滬劇長廊帶來一抹陽剛
滬劇一直以情感戲見長,在大家印象中,滬劇一直是花前月下、西裝旗袍、情意綿綿的。就題材來說,《鄧世昌》可以說不那么“滬劇”,但是朱儉認為,滬劇一直以題材和內容的開拓創新而走在戲曲的前列:“滬劇的前輩們培養了一代代忠實觀眾。對于我們來說,應該探討的是如何做到引領新老觀眾進劇場看戲。但每個人的審美是不同的,就好比同樣蒸一條魚,四川人會嫌這條魚不夠辣,上海人則會覺得不夠鮮。《鄧世昌》不一定能適合每一個滬劇觀眾的胃口。當然,我們的劇本也在不停地打磨,吸收專家的意見更聽取觀眾的意見,即使不能面面俱到,我們也希望能綜合那些值得學習的看法,讓更多觀眾喜歡。”
同時,朱儉也認為,每個時代都有它的文化,包括節奏和欣賞習慣;滬劇也是從灘簧發展到申曲,再從申曲演變成現在的滬劇。國家都在發展,戲曲也應跟隨著發展。滬劇不像其他的一些劇種,以傳承為多;滬劇一直在發展著。因為滬劇不僅有傳統戲曲的虛擬化手段,更有話劇的現實主義表演方式,他說:“你說我們臺上沒有程式化,但是它還真有,譬如過門表現內心反應,這是滬劇祖祖輩輩留下來的寶貴的表演方法;你說臺上全是程式化的‘叭噠倉吧,它也不是,因為滬劇比較特殊,不像其他劇種那樣每出戲都有約定俗成的相應流派和程式來演繹。對于滬劇來說,它是上海土生土長的戲曲,它很年輕,而且海納百川,會接受新的東西。因此我們不局限于自己的流派和程式。”
滬劇一般以塑造女性角色見長,無論是《星星之火》中的楊桂英、小珍子,還是《羅漢錢》中的小飛娥,或是《蘆蕩火種》中的阿慶嫂,都體現出滬劇委婉動聽的唱腔和女性角色塑造的優勢。在朱儉看來,《鄧世昌》無疑是為滬劇創造了一個新的男性形象,增添了一抹陽剛色彩。朱儉說:“《鄧世昌》里只有一位女性,剩下的全是男性,它集中展示了上海滬劇院幾乎所有主要的男演員,這說明了滬劇的唱腔不僅適合塑造女性,同樣也適合男性,因為滬劇是融戲曲、舞蹈、話劇等于一體的,戲開頭的旗操包括整出戲的形體,都是我們從舞蹈那里學習來的,因此滬劇唱腔的柔婉可以用其他方面的陽剛來補充,這出戲本身對以后男性角色的塑造也是有幫助的。”
最后,當問及《鄧世昌》演出的現實意義時,朱儉簡單而又認真地回答“我們要喚起中國人的一顆愛國心,鄧世昌連生命都肯舍去是為了什么?為的就是后方的將士和百姓能夠過上安定的生活,這是一種正能量。舞臺劇就是一個窗口,《鄧世昌》想要傳遞的,就是愛國心和滿滿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