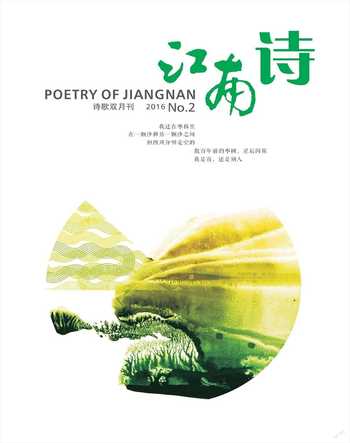復活,而不是復仇
主持人語:
余怒是一位自覺的、具有實驗精神和文本意識的詩人,詩作具有復調、立體、交互、開放的特點,致力于詩與語言、人與世界關系的重構,詩歌、小說、詩論三者并重,不斷拓展自我與寫作的疆域。廖令鵬的評論,通過對余怒詩歌內在演變脈絡的考察和梳理,發現其作品“潛伏著一種異樣的樣式”,其寫作是“左手與右手的自我較量,進行詩人個體,語言、閱讀者,到歷史寫作這樣一個多重關系的‘文本——語言——作品——歷史的詩歌形式探索”。(沈葦)
詩歌是一種精神
如何理解余怒?這既是我自己的問題,也是漢語詩歌的問題。讀余怒的詩歌這么多年,到現在也沒有好好回答這個問題,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還沒有完全理解詩歌,理解詩歌與生命的關系,也沒有弄清楚當代詩歌的核心價值所在。這看起來是個高大上的問題,確實是每個致力于成為詩人的詩歌寫作者必須回答的問題。不過,有趣的是,幾乎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以各種形式表征詩歌的核心價值,以各種形式充斥到漢語詩歌體系當中,以各種形式獲取個人和時代的雙重身份。然而,自朦朧詩以降到如今30多年,現代漢語詩歌的“形式”,更多的是呈現出“形態”、“樣式”,或者是兩者的疊加,它幾乎把讀者排斥在外,它把讀者當成了圍觀者。就目前的漢語詩歌創作來看,真正能夠實現作者不死,讀者新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交互關系的詩歌形式并不多。余怒的詩歌就是其中之一。
余怒在詩集《主與客》的后記中提到:“我一如既往地懷疑語言,著迷于言說的形式,如果有人因此說我是個形式主義者,那么只能說明他有喜歡亂扣帽子的癖好,說‘余怒注重形式與說‘余怒不在乎形式都是一個樣,等于什么也沒說。”——在這里,我要澄清兩點,首先,我也不贊同余怒是個形式主義者,凡是“主義”都存在一定的危險,“主義者”更是讓人厭惡;另外,我對“余怒注重形式”,“余怒不在乎形式”這樣的論調不太感冒,為什么?這種論調語境中的“形式”,充其量乃是一種,或者說是無數種簡單膚淺的形式,也可以說是自朦朧詩以降漢語詩業已泛濫的形式。余怒不是注重形式,也不是不在乎形式,在我看來,余怒的詩歌潛伏著一種異樣的形式,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發覺,所以談不上“注重”或者“在乎”。這種形式構成了除寫作是生命的必需之外,余怒詩歌的核心價值意義;這種形式雖然隱蔽但已然成為其詩歌的重要推動力;這種形式強有力地動搖了30多年來現代漢語詩的“形態之詩”、“樣式之詩”及“行為之詩”。誠然,每個時代都有形式,每個人都有形式,每首詩也有形式,但是我們很少去想那是怎樣一些形式,要不要更新這些形式,久而久之,我們就被無數詩歌“形式”這件金縷玉衣所散發出來的腐朽的歷史氣息所熏染,從而習慣地粗暴地認為“某某是個形式主義者”,或者“某某詩歌的形式不錯”。
一方面,很多人認定余怒固有某種形式,另一方面,余怒可能并不一定隸屬于這種形式,甚至不斷探索更加有意義的形式,所以我想,余怒是孤獨的。這種孤獨不是無意或有意地被一些人忽略、抵觸,不是過度先鋒而缺乏追隨與唱和者,不是喧囂詩壇那點可憐的名利與他絕緣——余怒沒有詩歌之外的敵人。為什么這樣說呢?一個可以真正談論詩歌的詩人,不應該會有與詩歌無關的社會敵人。而如今可以真正談論詩歌的人并不多,當代詩歌領域中可與余怒的知行合一相互檢驗佐證的詩人,同樣并不多。為什么在《守夜人》、《眾所周知的立方體》之后,還要創作《枝葉》、《饑餓之年》、《詩學》、《恍惚公園》,現在又在嘗試《喘息》的寫作?甚至為什么在1997年創作詩論《感覺多向性的語義負載》之后,2000年創作《體會與呈現:閱讀與寫作的方法論》,時隔14年,于2014年又陸續創作包括《話語循環的語言學模型》等在內的系列論文《在歷史中寫作》?
梳理以上這些詩歌、小說及詩論的風格脈絡,我看出余怒在漢語詩歌道路上不斷地更新自己,進行著左手與右手的自我較量,進行詩人個體,語言、閱讀者,到歷史寫作這樣一個多重關系的“文本——語言——作品——歷史”的詩歌形式探索。“對于寫作多年的人來說,你寫下的是不是一首好詩已經意義不大,重要的是你的寫作是不是拓展了詩歌的疆域。我(余怒)一直感覺到詩歌還是固守著我們的美學原則,束手束腳,沒有足夠的勇氣打破一些條條框框。我認為不管是詩歌也好,藝術也好,它之所以能喚起人們審美經驗,是因為它不斷突破藝術和現實之間的界限,拓展藝術的疆界,使藝術無限地逼近現實。”(摘錄自余怒主編的民刊《文本》)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名躁一時的詩人中,至今還在不斷更新并拓展詩歌的疆界,使詩歌無限地逼近現實,堅持詩歌創作并維持較高數量的詩人,已經不多了,更多的是進行著詩歌明星的代言活動。
所以在我看來,余怒是一個具有“詩歌精神”的當代漢語詩人。
一次性詩歌和沒有意義的讀者
首先來看看30年多來現代漢詩是一個怎樣的“形式”。80年代初期,朦朧詩閃耀著強烈的批判鋒芒,喊出了“我要……”,一座座刻著“大寫的人”的雕像巍然屹立:一個健碩的男人激昂地舉起右拳——至于這拳頭砸向何處,大地,敵人,胸膛,還是永遠朝向天空,其實無關緊要。顧城、舒婷則喊出一個略微豐富的句子“我要有一點兒個人的情感”,他們表情稍微豐富一些,但也只是個人雕像的一種,很大程度上與北島、芒克、多多的雕像“形態”并無二致。他們墜入空前的政治想象與歷史想象之中,構建出話語的英雄模型,經過鑄造、加工、鍍膜,這種模型演繹為一種雕像的靜止“形態”,堅挺地豎立在沉悶的歷史天空下。“抗議作為一個詩歌主題,其可能性已經被殆盡了”(歐陽江河,《‘89后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征與知識分子身份》)。鐘鳴更加深刻地指出朦朧詩一代的局限性,“食指、北島、芒克、多多、江河、顧城等,雖然在人道的關懷和自由的張力乃至詩歌趣味之間邁進了一步,但通俗哲學和逸趣、土地、民族、政治、流亡、正義、表現……仍是其話語的主要支架,字里行間,主觀意識對物有著很強的支配權,仍然沒處理好詞語與物或物與人的關系。”(鐘鳴,《秋天的戲劇》)主觀意識一旦對事和物實施支配或者占有,其實已經悄悄地陷入二元對立當中,姿態一旦塑形,變成可以準確描述,清晰呈現,那么延續的創作已變得毫無意義。與此同時,當時比較看好的“非非”詩歌,借助西方后現代美學,進行語言破壞與價值破壞的雙重試驗,但仍基于詞語堆砌、語義散亂、追求觀感刺激的簡單范式,過度“取消”,矯枉過正,無形地削弱了詩歌的文本價值,跌入一個“形態”的圍城當中。
進入90年代,詩歌的形式變得越來越不可捉摸。陳東東、于堅、歐陽江河、韓東等第三代詩人從朦朧詩“雕像”式話語表達體系中,很難找到自身的影子,它必須重新確立一種新的姿態,個人形態便悄悄塑造出來。介入日常生活現場,注重當下經驗表達,個人化及物寫作,結合語言的復雜性和內部緊張性而形成的敘事策略開始愈加凸顯出來。韓東、歐陽江河、于堅、伊沙等都曾在80年代至90年代進行宏大敘事的消解與批判,以反文化、反崇高的平民寫作風格審視詩歌,以傳達回歸日常生活的個人精神指向。當然,還有其他各種各樣形態的詩人,不遺余力地在詩歌中塑造一個、一群或者一類具有某種生活標簽的人。于是,人們歡欣鼓舞,認為這是一批找到自我的詩人,他們的膚色有了光澤,語言有了氣息,行動有了意義,詩人與讀者終于找到一種情投意合的曖昧的滿足感。作為對朦朧詩歌的一種反動,個人的一種姿態,以口語平民化寫作的第三代詩歌拒絕進入象征和抒情建構的詩歌圣殿,而且將莊嚴、崇高、理想、英雄等從詩歌中剔除,這對于當代漢語詩來說無疑意義重大。然而,由于他們仍然是“意思中心主義”者向眾人布道的工具,像古老的言志抒情詩歌一樣,只不過它顯露的是與古老的價值判斷相反的判斷而已。(余怒《答木朵問》)實際上,第三代詩人仍然存在巨大的焦慮與疑問,作為一種自我存在的形態,更多的是像泥牛入海一樣,流沙過后,倏然無影。——他們只有標本和記憶。
第三代詩人的話語模型,是“要認識世界上某個房間中的有血有肉的自己,要用語言拆掉意識形態和歷史價值所負荷的那座房子,建一座個性十足且從日常生活中建造起來的房子——看,就是這座房子。”建造過程大概就是:一個巨大的建筑工場,沒有開工儀式,沒有致辭,成千上萬個工人各自建造房子,泥土是泥土,磚石是磚石,至于如何建造則不必追究。天氣、樹林、性愛及空中飛過的鳥,對于房子都沒有什么重要性。對另外一些詩人而言,知識分子態度、理想主義精神和秩序原則更為重要。西川、楊煉、王家新、肖開愚、孫文波等一批后朦朧詩人,甚至建造一幢幢諸如圣彼德堡式、巴洛克式、哥特式,埃及神廟式、杜甫草堂式,閃耀著歷史(神話)太陽光芒般神圣的建筑,同樣地,至于如何建造,則不必追究,建筑之外的事物,亦無重要性,這是詩人自己的建筑。他們絕對不會去建筑一座墳墓,或者扔個骰子決定參加哪個雞尾酒會。不可否認,這些能工巧匠為現代漢語詩構造了無數精妙的建筑,他們有了“行為”和“姿勢”,建筑有了“形態”和“樣式”,他們跟建筑之間,形成了接近于人類行為學的多元面貌。也可以這樣說,他們總體期望就是,這些輸出神圣莊嚴的歷史或悲憫同情的人性,能夠有效地傳導至閱讀者那里,讓閱讀者變成擊鼓傳花者,其作品才算完成。所以,無論是個人道德“曲線”標榜,時代價值“喊話”,還是日常事件高調鋪陳,公共話語空間陳述,歷史批判或神話崇拜,那種對抗式、二元化、扁平化、靜止型、樣式輸出、平民觀念傳達的漢語詩歌,實際上仍屬于“形態詩歌”的范疇,它的文本模式特征主要是從多樣化的“形”,直接輸出為多樣化的“態”。通俗地講,這些詩歌的意義是在作者那里,讀者只是意義的搬運工和圍觀者。余怒稱之為“一次性詩歌”,這種詩歌只在詩歌史意義上才有意義。(《主與客》,第194頁)
我們回到一個熟悉的化學試驗中。大家都知道,在學習分子轉換與能量守恒的過程中,老師常常為我們演示這個試驗——固態、液態與汽態的變化。固態堅硬,靜止,易碎,但易于描述;液態變化,流動,隨物賦形,親和,易于融合;汽態無形,霧散,可形成正壓或負壓能量,無處不在,卻易于消彌。不管他們的特性如何,其實都可以歸類到“形態”的范疇中去。類似于此,新時期詩歌寫作者在當代漢語詩歌中的反映,朦朧詩一代接近于固態,第三代詩歌傾向于液態,而新世紀的中間代,則帶有較為強烈的汽態屬性。這么說雖然不太恰當,但仍是大家易于理解的方式。問題是,輸出固態、液態、汽態及分子結合方程等化學知識,是初中時期老師的任務,屬于知識普及范疇。而作為科學研究或者更高層次的科學藝術,除了告訴我們這三種常見的“態”的更加微觀的形成過程,如分子內部的分解、分子的關系、排列組合、客觀環境等種種自變量與因變量的相互耦合,還應開創性、想象性、藝術性地體驗或介入這些微觀的過程。實踐告訴我們,世界中仍存在純態,或者說是變態,化成萬物,無法捕捉,甚至無法描述。
實際上,真正認識世界,我們需要的是那些微觀的過程。如果把人類作為一種分子,我們也需要參與到形態的變化當中,如何參與,最根本的就是必須實現交互關系,否則“一個人”與“多種世界”之間很容易形成對立,并陷入輸贏模型或者虛無的博弈當中。30多年過去,時至今日,我們發現大多數詩歌“形式”除了語言意義的存在之外,它只是無數種個人與世界發生某種關系的果實,果實本身,才是其漢語詩歌語言的“所指”。說到底,這只是無數種形態的集結。我們可以用無數只泥牛,扔到無數個世界折射裝置當中,進而構成無數個鏡象。當作者沒有真正獲得一種終極的形式而滿足于形態的輸出快感時,他們的生命與詩歌僅僅發生了簡單的擁抱和觸摸,詩歌陳述的世界根本就是虛幻的,虛偽的,封閉的。“作者構建結構或者說對于文本權威性的塑造驅動不過是幻想或一個注定半途夭折的意向。”(《主與客》,第207頁)
語言幻覺與現實的內部形式
布拉格結構主義學派穆卡洛夫斯基重視詩歌語言的對抗性,認為只有語言的對抗,詩歌才成為可能。這對于漢語詩來說未必適用,甚至形成了流毒。比如“詩到語言為止”,其語言倫理雖然推動了漢語詩的發展,但它的對立性與割裂性,無疑又形成桎梏。語言對于形式發揮著性命攸關的作用,可以說,最初的形式,是在語言中摸索前進的,20世紀西方形式主義美學無疑是巨大的推動力。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那種被稱為藝術的東西的存在,正是為了喚回人對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頭更成為其石頭。藝術的目的是使你對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見的視象那樣,而不是如同你所認知的那樣;藝術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復雜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難度和時延,既然藝術中領悟過程是以自身為目的的,它就理應延長:藝術是一種體驗事物之創造的方式,而被創作物在藝術中已無足輕重。”(什克洛夫斯基,《作為技巧的藝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這是陌生化寫作的根本出發點。眾所周知,陌生化對于漢語詩歌,有著相當裨益的原旨,但自從譯介到中國的那一天起,它的意義就被扭曲、殘缺,膚淺地在地化了。陌生化作為一種哲學,粗糲地簡化為一種技巧——陌生化語言,陌生化的終極意義——對抗人類慣常的經驗,重新喚起事物——無形地閹割了。遺憾的是,“以自身為目的,體驗事物之創造的方式”這個最為重要的藝術思想沒有在當代漢語詩歌中得到發揚光大,反而簡化為——以自身為鏡像,呈現由體驗所創造的事物。
當然,無庸置疑,中國的陌生化詩學過程難度是相當大的,不僅是因為反常、夸張、扭曲、變形、伸縮、顛倒的語言異化容易帶來晦澀、古奧、拗義,還因為它要面對的是幾千年的漢語詩歌傳統,語言和結構雙重負荷。海子、昌耀、周倫佑、臧棣、車前子、余怒等一批詩人首先在語言上進入陌生化狀態,受到詩壇的廣泛關注。海子使用意象的突兀與抒情的扭轉來實現陌生化;昌耀擅長對古漢語和句法的偏離“詩的榔頭”來實現其詩歌的陌生化;車前子從根本上摒棄了意象的意義和秩序,回避使用邏輯語言寫詩,甚至回避客觀的陳述和理性的闡釋,打碎重新組合漢語,以達到陌生化效果。臧棣一方面從傳統漢語詩歌和惠特曼那里汲取營養,另一方面,把陌生化漢語變得更加熟稔,以至于利用語言技巧基本上抹平了陌生化詩學的褶皺,進入一種新的詩學空間。不過,臧棣的這條路并非坦途,大眾并不能很融洽地與他的詩歌和平共處,原因之一,我想是臧棣的詩歌形式中欠缺某種類似于粘合劑的深刻而平實的東西,缺乏一種日常生活中新的元素落實到文本當中,所以臧棣90年代的詩歌,更多地作為一種技巧性文本得到人們的關注,大眾仍沒有買單的強烈欲望。倒是近年來的詩歌如《慧根叢書》等,把語言與生命的感受結合得澄明通透,熠熠生輝。
余怒在很大程度上與臧棣的遭遇相似。他曾經倍受爭議,眾說紛蕓,不乏“詩歌的敵人”、“語言的瘋子”、“反叛的先鋒詩人”,有人甚至把他視為當代漢語詩歌的復仇者,認為他對自朦朧詩以降幾十年來的經典漢語詩歌的權威性與合理性,格格對立,進行無端的挑戰,甚至破壞。究其原因,是后現代主義美學思想與解構主義的詩學理念的不斷嘗試,使其詩歌普遍給人以陌生的印象,不可讀、不可解,而這又最直接地體現在詩歌語言層面。其實,以往人們對余怒的評論,也大都著重于探討語言,余怒本人也進行過對語言的專門研究。他指出,語言依賴詞語間的各種關系而顯示意義,這些關系不是“因果關系”,而是可稱其為“人為關系”。所有用于人際交流的語言正是建立在這種“人為關系”之上。它是世俗生活的可靠保證,與人的精神世界很少關聯。(余怒,《感覺多向性的語義負載》,載《山花》1999年第4期。)在此基礎上,學界概括出余怒詩歌在語言上的兩個特征:“立方體”與“詩亂而詩意不亂”。在我看來,這兩件衣服不僅漂亮,而且相對比較合身。不過,遺憾的是,人們到現在也沒能清晰地梳理這兩件衣服的來龍去脈,沒能更加系統地厘清“平面”與“立體”、“亂”與“不亂”之間的深刻內涵,結果是,幾乎全軍潰敗地,迷失在一堆混亂的“立方體”當中。為什么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首先了解余怒的“意義”和“歧義”。簡言之,余怒詩歌的意義,不在余怒那里,而是在讀者那里,只有讀者才是有意義的意義生產者和實現者,作者至多不過能為與讀者的互動提供一個導言、一個場所、一沓散亂的歷史檔案、一堆尋求“最后因”的“材料因”。(參考《話語循環的語言學模型》,見《主與客》)評論家白鴉也認為,詩人對讀者的作用不是“給予與接受”的單向度的關系,而是相互作用的關系。詩人將文本體驗的選擇權歸還給讀者,就是將詩人所發現的“真相”呈現給讀者,讓讀者從自己的生活與道德出發,在“真相”中獲得關于他自己的回憶、共鳴或者其它自由體驗,這意味著詩人將不再獨占體驗的選擇權與對世界的命名權。(《界外》,第21頁,白鴉著)所以,我把余怒那種基于獨特的意義產生形式而創作的詩歌,稱為“關系交互”的詩歌,或者“開放”的詩歌。我要強調的是,詩歌作品產生、發展、建構、流動、互動、開放的過程,盡管語言的關系固然重要,意義實現完全憑借語言的構造,語言鑄就了主體,鑄就了“我”,但我們仍然需要處理主體的關系,必須延伸至一種更加現實的形式,才能使語言關系落到實處。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提出語言之后仍有待挖掘的空間,“語言從說話中解放出來,從而產生了一系列交往語言的符號,它們是與一種意義聯系在一起的一些名稱,人們通過這些名稱便可掌握神力(神衹、自然力)的秘密;它們還是數(公式、簡單的定律),現實的內在形式通過這些數而得以從偶然的感覺中抽象出來。”(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第464頁)——“現實的內在形式”就是斯賓格勒所提出的語言之后的真正“自我”。從這個角度切入余怒的詩歌,我們可以發現,從2005年創作的《枝葉》——形式的萌發期,2010年的創作《個人史》、《眾所周知的立方體》——形式的形成期,2012年創作《詩學》——形式的狂歡期,再到2013年創作《喘息》——形式的裂變期,其實就是主體處理現實的內部關系的演變脈絡,除了語言創作活動的體驗,他還呈現一種隱藏在語言關系內部的形式。詩集《主與客》中大量詩歌,如《鋼筋問題》、《漫談》、《致兒子》、《仿佛游泳》、《他媽的悲傷》等等,都把某種多元的、不確定的、流動的、多聲部的及無從考據的主題與“我”緊密聯系起來,超越了詞語和結構的陌生化,演變成一種不穩定的詩歌關系與生活關系。不管人們稱之為碎片化也好,多面體也好,余怒盡可能地把意義交給讀者,讀者可以根據自身會驗或者體會,重新想象詩歌中的語簇、句群,而不用擔心存在詩人預設或者預謀的某種意義,換句話說,詩歌中的文本(材料)、作者、讀者是平等的,這三者交互存在,頻繁地在現代生活、自我體驗和歷史時空中達成默契,它們相互補充,相互成就,相互闡釋,從而形成趨于開放的詩意空間。
詩歌需要什么關系
我們知道,不僅僅存在一個人對于一種世界的關系,世界對于人也會形成某種關系,人與生活中的事物之間也存在無數種關系,世界萬物俱有永恒的相互關系,關系因時、因勢、因情、因人、因物而變,僅靠場景輸出、二元對立、多元介入、過去完成時、現在完成時或者將來完成時的“時態”,等等,僅靠強有力的作者或者既定的文本,根本沒有辦法描述這些隱蔽在紛繁生活中的關系。詩歌中“可能性”,我認為也是一種關系的可能性,它預示關系的不穩定性,如同“河流在移動,黑鳥一定在飛” (華萊士·史蒂文斯,《觀察黑鳥的十三種方式》)中移動的河流與飛翔的黑鳥之間的關系。所以,如果說“可能性”仍然有效,那么它只是可能性的關系并由此引起的存在的意義。余怒在《體會與呈現:閱讀與寫作的方法論》中,大篇幅地闡述了這種關系,“詞語離開它既有的固定意義而獲得一種即時性,它與其他詞語的聯系也基于暫時的、不穩定的、互動的關系之上,它與系統的關系亦是如此……我所要做的更新是關于詞語與詞語、句子與句子、句群與句群之間的關系的更新,這種關系在那里,只是被我們的慣性思念和言說遮蔽著。”(《主與客》,第194頁)。
余怒的詩歌有什么“關系”?這是我要重點探討的問題。不妨從一些簡單的閱讀體會開始——
1、反對永恒不變的絕對精神,主張世界的可變性的價值的相對性;政治退場,意識形態退場,事物互不形容;
2、每首詩中總有一部分取景來源于現實生活,像《個人史》這樣的長詩,更是大量生活散片的聚合;
3、句群之間的關系不穩定,不完整,一旦出現穩定的傾向,立即打破、引導或者疏散;
4、上下文缺乏絕對的必然性;句子在詩中的關系平等,很少有所謂精神的神圣性或者修辭的附屬性;
5、打破邏各斯中心主義,幾乎任何一首詩都看不出中心意義,重視語言環境和話語交往的“交互涉關系”,立體的、網狀的、多聲部的復調敘事;
6.每首詩中都有人、事、物的碰撞,它們的形態碎片化,位置瞬間穿插變換,關系若即若離;
7.偶爾出現邏輯的合理性但現實的少概率的敘事,不拒絕荒誕、戲謔、自嘲;議論既不是敘事的補充,也并非用于起承轉合。
以上幾點結論雖不能完全概括余怒詩歌的特征,但契合其大部分新時期創作的詩歌。這些結論與余怒的寫作初衷是對應的,讀者若有興趣,可參考《在歷史中寫作》等幾篇詩論(詳見《主與客》)。我所要做的,就是在這些結論的基礎上,試圖能夠挖掘出某種新的關系。
《致兒子》這首詩中,開頭寫道:“有時我想爬樹,/和兒子一起,通過樹枝樹葉親近兒子。/兒子長大了,他更喜歡獨自爬樹,/邊爬邊自個兒跟自個兒說話。”在這里,詩歌提供了基本的背景,這時我們還讀不到確定的意義。接下來,“棒球迷愛棒球,喜歡圍觀的人愛在/別人身上找樂子。/有人去索馬里海域,對海盜產生興趣。/有人去南極,冷冷身子。”在這里,詩人提供了四組材料,每一組材料都沒有確切的因果關系,都需要交由讀者自己完成閱讀體驗。結尾“現實中很多智障兒。語言中我是。不像/大雁或土撥鼠,天上的索性去天上,地下的/索性去地下。”這幾句詩歌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與前文也沒有形成顯然的因果、條件、遞進等簡單的邏輯關系,其間存在多個語義溝壑,既可以填補,也可以挖掘延伸,甚至可以剔除,而不致于過分妨礙前文的意義。《致兒子》整首詩加上“我”的議論部分,意義的材料多達20個(組)。這些材料向度不同,屬性不一,關系微弱。我們只知道詩歌是“致兒子”,但致兒子什么,卻是個疑問,詩人并沒有說出,或者傳達出它們之間的關系。我曾經把這首詩給幾個朋友閱讀,結果大相徑庭,有人說讀到孤獨,有人說讀者溝通的難度,有人讀到期望,有人讀到絕望,有人甚至讀到信仰。他們都有經過自己確切的分析,都在詩歌中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實證。——這當然是歧義的表現,但詩歌的交互關系體現哪里呢?顯然,余怒把“與你說話,我很快活”中的“自我”,還原到了生活現場,與諸多事、物相互驗證,相互說明,實現平衡關系。“我”不是主宰者和支配者,也不是呼吁者與獻媚者;不是“文本”情感制成品與實現價值的工具,不是話語的傳聲筒與經驗的迷宮。——我更多的是意義生成的材料提供者,跟讀者一樣,是一個變量。
《詩學(37)》中,“讀完所有的書”、“無法描述茉莉”、“我快要死了”、“為鬼魂充電”、“在凌晨吞下所有的藥片”、“太陽升起時分辨穿透手掌的光線”、“我們很脆弱”,這些語義有多少日常生活的經驗?有多少虛構或者多少現場報道?單個敘述切片有多少意義?當這些句子聚合在一首詩中的時候,每個敘述切片的意義都豐富起來。知識(語言)對精神(茉莉)的描述疲乏,源于“我”的脆弱、焦慮、敏感,甚至徒有其表,需要幻想增強靈魂的能量,然而為靈魂充電(如倒上可口可樂),也顯得荒誕;墻角的茉莉仍有白色的孤獨。——總之,意義來源于詩歌中事物(句群)間的關系,關系來源于不同事物的相互存在,而詩歌中相互存在的關系,也面臨瞬時變化而引起的可能性。
余怒的這種詩歌寫作表明,自我與日常生活的關系是不穩定的,通過句子間關系相互印證,會發現原來所感知到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甚至顛覆了之前的關系。我認為,這種詩意應該是現實的日常生活中相互之間關系的變化帶來的意義。可以這樣說,對于朦朧派詩歌,其局限正是固化了關系,它提供一記高舉的拳頭,一片迎風的帆,或者其它什么東西。第三代詩人雖然意識到人與外界的關系之重要,也呈現了無數個性化的關系,但顯而易見,由于主體的強行介入支配,急于傾訴這種經過自我的體驗或者經驗所析出的關系,演變成某種“樣式”或者現場“行為”。那僅僅是一個靜止的形態,一種確定的關系,因而是封閉的。特別是當人們普遍意識到“意義”在變化中才有意義時,詩人不應當提供關系的產出品,而應該為讀者提供參與生產的空間及機會。余怒的詩歌,正是在不斷更新這種空間及機會之中,由于關系的變化而帶來的意義變化。我想,明白了這一點,就無須為他的語言而感到困頓,為他的混亂而潰亂,為他的“不可言說”的詩意感到迷茫,為他的“歧義”感到不知所措。我們只需要在余怒詩歌中呈現的“關系”變化中,編織自己的意義。編織這種“意義”,最好的辦法就是余怒所謂的“體會”,就是忘我的浸入,是不帶意思預設和解釋企圖的浸沒,“體會”即浸沒、交融、重合。(《主與客》,第186頁)
這么說,是不是意味著余怒的詩歌創作可以胡來了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仍要回到巴特那里尋找答案。在《一個解構主義的文本》中,巴特的無“意”,無所寄興,滿不在乎,激起了一些人的疑問,“那不成了胡話了嗎?”巴特對這種觀點的回應是,在他看來,胡話、癡話或者說戲謔語等行文載體,都是一種沒有中心意義的快節奏的狂熱的語言活動,一種純凈、超脫的語言烏托邦境界,沉溺于這種“無底的、無真諦的語言喜劇”便是對終極意義的否定的根本方式。它并不是一種虛無主義態度,而是面對縱橫交錯的語言、意義經緯織成的歷史文化潛意識網絡的清醒認識。(《一個解構主義文本》,第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因此,對于余怒詩歌的這個問題,我們還要一分為二來看,對于閱讀者,畢竟體會與感悟與自身生命不同,而且格格不入,與陌生化所帶來的感受是類似的;另一方面,對于詩人來說,這又是獨一無二的,感覺、體悟、經驗等融合成詩意的光束,照射現實的日常生活現場,其間有剎那的、偶然的、無意識選擇的、“胡來”的事物得以留存,但大多數還是與詩人生命向度相關的。即使如此,這還只能是余怒形式詩學的基礎,最重要的是,從某種程度來看,在詩歌面前,閱讀者與余怒、詩歌中的“我”及事物,是眾生平等的平行關系,是“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意義繳械不是投降,混亂不是低級,歧義不是目的,余怒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詩歌“作品”呈現更多交互的可能性。如果說對于個體生命存在的意義,21世紀還有點兒當代漢語詩歌什么事兒的話,那就是開辟、建立、參與并超越生活中隱蔽的復雜關系。
關系是余怒詩歌的核心,而秩序也決定著形式,秩序反映著詩歌的智慧和膽識。余怒詩歌的開頭部分,大都是現實的日常生活的一種狀態,或者一件事,或者一件物,或者我的一種狀態,我們不妨稱之為第一“句群”。很快,詩歌的第二“句群”打破了這種狀態的靜止平衡,出現極大的“歧義”,余怒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來實現:一種不相關的日常生活描述性句群,使句群之間立即產生鴻溝,強行把閱讀者的思維拉扯、跳轉到另一語義。一種是“我”的議論,在余怒的詩歌中,議論是非常重要的打破語義的手段,這種議論不是一本正經地按照既定的思維邏輯來就事論事,而是另一種超越常識的議論,它們有時與上一句群發生語義關系,大多數時候是議論著別的什么事情。實際上,這也給閱讀者的慣常思維造成了阻力或者障礙;一種仍是描述性的句群,但融入了戲謔、夸張、變形、荒誕、比喻等成分,因而是不可能的句群。然而,余怒又會在若干句群后,呈現與前面句群中的聯系,或者敘事上的聯系,或者議論的聯系。
比如《詩學(37)》中開頭寫道:“節能燈越來越亮,床和枕頭很軟/臥室里,有一只流浪狗,被我/收留,有時,它會反咬我一口。”——第一句群,日常生活的描述,帶有情節性的普通經驗的傳遞。緊接著,詩人寫到了雨,“下雨時,我適應那種濕漉漉;天氣/晴朗,我適應那種干燥。口干舌燥。”——這可視為第二句群,它沒有沿著第一句群的思路往下寫,敘述在夜晚的臥室里與狗的情節,而是轉到了談論天氣問題。繼而又在第三句群中寫到了對皮埃爾的閱讀,在第四句群中寫到“我”自己的詩歌。再如在《詩學(27)》中開頭寫道:“我想用詩,記錄下一切。”這也是個描述性的句子,緊接著出現了議論性的句群,“這是美好的想法,但也/反映了我的脆弱。//人人都以為詩歌是好東西,/對不起,我和我的某些器官也這樣認為。/那是一些天真的小器官,/比如:做做樣子的乳頭。”這第二個句群的議論,就是我剛才講到的那種帶點戲謔、詼諧,又奇怪的議論。《裝作一切正常》更是把這種手法運用到了極致。“清晨,很多東西被毀掉了。雪壓著屋頂。/通了一會兒電,我們身上才舒服了點。/她在往墻上貼硬幣,以此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將玻璃杯放在水里煮,直到它變成一坨玻璃塊。”這四句,幾乎沒有什么聯系,自說自話,亦真亦幻,作為拼貼藝術的一種,這首詩的意義只有在關系的秩序確立之后,才能清晰地體會。《時至今日》、《漫談》、《個人史》更是大量意義獨立的句群,依照秩序逐一呈現,顯露出生活的異域之美。限于篇幅,我不再做更詳細的論述。
余怒詩歌中A句群、B句群與C句群等等的秩序,對于每一個詩人、每一首詩來說,是惟一的,它決定著“體會”的情境。很顯然,在整個體會過程中,出現在讀者腦中的種種情境,是隨著文本縱的聚合(假如此時是A句群)次序展開的,當每次出現的其它句群(B—N句群),無論是內在或外在,讀者總是出于自己想象的需要、快感,而身不由已地去挖掘自己不同的情境。所以,A句群、B句群、C句群,直到N句群以及這些不同形態句群的穿插、排列、聚合,是詩歌“主體”通過偶然的感覺,抽象出來現實的內在形式,從而給予讀者一把可能性的鑰匙,對意思缺失的、未完成的、需要參與的文本進行“二度寫作”,它是動態的,也是互動的體驗。
更加開放的詩歌
直到今天,詩人們還在頻繁地討論修辭(包括結構、語言、語義、題旨)給詩歌帶來的種種可能,探索作品(作者、讀者、文本)在時代及歷史情境中的種種可能。這無疑是當代詩歌不斷發展的巨大推動力,然而,今天我們面臨的情境是,讀者不再是意義的進口者兼消費者,也不滿足于作為一個圍觀者,他不僅僅擁有與詩歌交互的權利,也擁有交互體驗的動力和能力。意義既不完全在作者那里,也不完全在讀者那里,意義更多地是在開放的交互關系中逐漸形成。甚至可以這樣說,詩歌的意義幾乎無法堅固,即使如同磐石一樣堅硬,它也會日積月累地發生微妙的變化,也會在不同的關系圖譜中,呈現不同的意義。對于詩歌而言,既不需要傳達什么類似數、律這樣的信息量,也不需要弘揚什么既定的道德和道義,更不需要向讀者展示——像博物館陳列的那樣——某種個性化形象。世界是一切關系的總和,詩歌以其絕對自由、多元開放、無限可能的形式空間,映照并讓渡這個世界的形式,重新挖掘世界的存在,呈現真相,缺乏互動的漢語詩歌只能讓讀者更加孤立,走向單極化,對意義冷漠無視,進而無助于人們更真實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就是當代詩歌亟需確立一種更加開放的詩歌形式的意義所在。其實,早在2010年,戈多就已經在其《歷史記憶原生態敘述策略的實驗文本:〈饑餓之年〉》一文中,提到余怒這種開放型詩歌創作的實驗,“針對《饑餓之年》文本所表現的混沌特性,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其文本內部自身指向的歧義性與復雜性,二是在于文體交叉性所構成的一種開放性的文本....余怒的長詩《饑餓之年》是一個開放型的長詩實驗文本。其個人經驗化的敘述策略每每都使讓眾多讀者望而卻步,主要是因為其中暗含著諸多的謎團與迷宮,更像不同人物的心靈囈語與鏡宮,雜沓相陳、互相交叉、相互觀照,但是其詭秘獨特的風格也正是令人入迷之處。”余怒也在《體會與呈現:閱讀與寫作的方法論》和《話語循環的語言學模型》中,也談到自己對以“思想性”為背景的“深度”——這種作者和讀者的意思相互期待、文本深度幻覺和共同價值幻想——的憂慮。余怒的詩歌精神,構成他不斷進行嘗試與挑戰的力量源泉,正如他的詩集《主與客》,不斷地更新“句群關系”而不僅僅以陌生化語言的方式,推動詩歌的創作,同時為閱讀者提供交互體驗,力圖恢復自我生命與日常生活中眾事物的關系——現實的內部形式。他采取的敘事倫理就是不裝逼,不妥協,不用高音喇叭,不裝高大上,或許這是因為他覺得當代漢語詩歌,還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