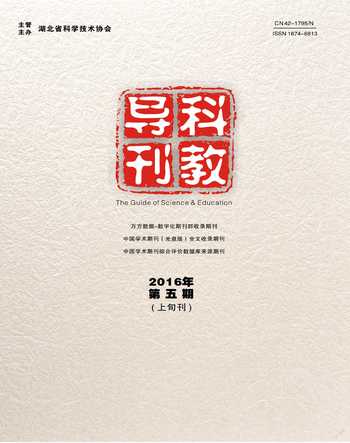從《帶燈》看賈平凹對當代鄉土中國的解讀
郝毅
摘 要 鄉土中國不僅是一個地域范疇,更是一個文化范疇。對鄉土中國進行充分表現的鄉土小說以其根植中國強大的生命力和表現力成為歷來作家關注的對象。賈平凹的小說《帶燈》就是以當代基層發展為背景,以一位女性干部的視角來表達其對當代鄉土中國的憂慮。
關鍵詞 鄉土小說 鄉土中國 基層視角 理想斷裂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6.05.064
Abstract Local China is not only a regional category, but also a cultural category. The local novels which have been fully expressed by the local Chinese have become the object of attention by the writers in their strong vitality and expressive power. Jia Pingwa's novel "the light"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grassroots, with a female cadres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s about contemporary Chinese local.
Key words local color fiction; Earthbound China; grassroots perspective; ideal fracture
1鄉土小說與鄉土中國
“鄉土小說”作為一種文學樣式,于19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并流行于美國,而伴隨著工業革命的進程不斷深化,鄉土小說以其特有的載體形式在各個國家進行著成功的嘗試,也因此具有了世界性母題的意義,推進著二十世紀文學發展的歷程。“鄉土小說”的重要特征在于“風俗畫描寫”和“地方特色”,這是對于鄉土小說的界限的劃分。對此有重要貢獻的美國小說家赫姆林·加蘭認為,“藝術的地方色彩是文學生命力的源泉”。不可否認,“地方特色”是對于作品個性的強調,也就是作家描寫的是獨具魅力的,有區別性特征的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風俗畫描寫”則更側重于審美體驗的層面。 就中國的鄉土小說而言,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始,作為鼻祖的魯迅引領了整個二十世紀鄉土文學的發展樣式。以《阿Q正傳》、《故鄉》、《社戲》等一系列經典作品為開端,鄉土小說在中國一出現便展現出一種驚世駭俗的成熟姿態,從一開始便作為一種文學載體,進行著文學的現代性嘗試并進而發掘時代中人的靈魂。從二十年代至今,鄉土小說一直擔負著對鄉土中國不斷闡釋的理想,其根源在于傳統中國的文化沿襲以及非常態化的發展歷程。一直以來,中國都是以農業為本的國家,不論時代風云如何變幻,現代社會如何陣痛式向前發展,農村、農民以其龐大基數和漫長歷史成為文學創作無法忽視的一個部分。二十年代的“新青年”用啟蒙的精神不斷的描繪在傳統壓抑中鄉土中國的沒落和罪惡,那種無情的揭露和批判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伴隨著三十年代不同立場的文藝思潮的碰撞,在工業化進程不斷吞噬人性的年代,被迫流浪他鄉的“異鄉人”開始追尋記憶中的故鄉,在《邊城》的夢境中陶醉于異于塵囂的牧歌情調。而伴隨著革命思想的復蘇,在時代感召下,作家對鄉土中國的情懷又發生了有別于前的變遷。四十年代的大眾化寫作,作家們踐行著新的鄉土中國在時代變革聲中不斷激昂的呼喚,《創業史》、《紅旗譜》等一大批作品的出現將傳統鄉土的固執和破敗推送至革命的風口浪尖。在這個新的鄉土中國時代里,趙樹理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進行著回歸民族和民間藝術的大膽創新,集體化創作不是表現個性而是將人民群眾成為表現的正宗。但隨著民族革命形勢的發展,政治革命也以無形滲透的方式逐漸成為文學表現的主流,鄉土中國的形象逐漸干癟缺乏生氣,意識形態的控制也抑止了文學發展的自然規律,因而失去了其獨立價值而流于政治傳聲筒。而至八十年代,文學顯示出重回“五四”的復興姿態,文化尋根喚醒了中國鄉村沉寂的靈魂。文學逐漸擺脫政治的束縛開始回歸本色。對于鄉土中國不是單純的表現,更多的是追問和求索。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后這樣一個可謂變革的時期,當經濟大潮沖擊著傳統的自然的操守,是毀滅還是重生,路在何方成為迫切需解決的問題。
鄉土中國是在中國的農村這片特定的土地上所繁衍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作為農耕文明的發祥地,中國的鄉土根植于獨特的華夏文明。它是靜止的,也是流動的。鄉土中國所涵蓋的區域千年不變,而文學思潮和政治運動的風波無不在這片舞臺上留下印記。對這種再熟悉不過的生活狀態,文學的描述,作家的解讀往往不是一成不變的。從魯迅等一代學人筆下的鄉村是如何的灰暗,農人的靈魂是如何的呆滯和麻木;到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新中國成立后村風起云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再到八九十年代人們在政治松綁的氛圍中對當代鄉村的回歸和重新審視。鄉土在中國作家的筆下往往帶有一種濃厚的人文情懷,不論是直指性的犀利目光還是溫情脈脈的歌頌贊揚,在這些作品的中都飽含著對這片土地的關注和愛戀之情。鄉土中國傳承著祖祖輩輩中國人的血脈,每一個作家深處都會和這種與生俱來的文化基因產生不自覺的共鳴。賈平凹的小說《帶燈》也是這種情感催生而出的作品,從大山深處走出的農村青年,從一開始對商州故事的精彩講述,到對農村百態的個性化解讀,都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說,《帶燈》是對這樣一種鄉土情懷的延續,描繪了秦嶺深處一個叫“櫻鎮”的鄉村,講述了當代農村生活中的緊扣“新農村”建設的各種矛盾事件,無不滲透著作家的憂慮和悲憫之情,成為新世紀以來,在土地和經濟發生激烈沖突的年代下對鄉土中國的又一次深入的思考。正如艾青的詩歌中所描繪的那樣,“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2透視當代鄉土中國的獨特視角
在不同時代作家的筆下,其與“鄉土中國”的位置關系,往往會發生書寫視角的變化。有站在啟蒙角度的俯視批判,有相互依偎的溫情懷想,也有并肩而立的英勇戰斗。這種多樣化的觀察視角也成就了鄉土中國豐富且復雜的形象。從視角的選取上通常可以看出作家在面對這樣一個書寫對象時的思考方式和關注角度。尤其對于人物選擇,作家更是十分慎重。在鄉土小說《秦腔》中,賈平凹把瘋子引生作為一個觀察世情的窗口。一個瘋子眼中的世界往往是混亂無序的,無意義的,作品也正是利用了這個主人公的特殊狀態將鄉土文化的挽歌情調引向了末路的終結。《帶燈》中采取的是比較傳統的第三人稱敘事模式,主人公則選擇了一位文學作品中出現較少的鄉鎮女干部作為主要對象。在作品草創期,作家深入農村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當代農村在新世紀發展的第一個十年中所形成的鄉土中國的風貌明顯區別于前,尤其是政治體制的積弊蔓延到基層政權這一敏感問題。一位女性知識青年親赴基層做鄉鎮干部,她美麗的性格和不俗的人格魅力和秦嶺山區秀麗的自然風光相得益彰,就在這個看似平靜的村鎮里,她目睹了也參與了對超生婦女強制流產的血腥,上訪村民的死纏爛打,貧困農民的悲苦結局以及經濟糾紛導致的極為嚴重的暴力事件。身在其中的帶燈懷疑著,也抗爭著。她也是滿心歡喜地想通過自己的努力為鄉村的發展造福祉,但各種矛盾積累,各種問題的解決并遠非她一人之力可及。如果說《秦腔》預示著鄉土文化必然走向消亡的必然,那《帶燈》就表達了作家面對鄉土中國在政治困境中依舊不斷探索出路的努力。
在對這一特殊視角的運用上,需要充分發揮作家對人物特殊身份和時代感的把握。五十年代,周立波在《山鄉巨變》中塑造了“縣里的工作組長”女干部鄧秀梅的形象。在新中國成立的初期,農業合作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作家就是通過描寫土生土長的基層領導者鄧秀梅政治方向堅定,處理人民內部問題有方,在與農民和生產勞動的關系中表現出了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帶燈》中恰巧也塑造了“帶燈”這么一位時代感頗強的基層女干部形象。兩部作品時隔半個多世紀,在相似身份的條件下,女干部帶燈則表現的是經過歲月變遷的農村在當代的特性。作為鄉鎮干部,鄧秀梅的工作是按照上級安排進行群眾工作,帶燈的任務是服從上級命令解決無法解決的上訪。從工作的針對性和政治宣傳的大環境下,鄧秀梅的生活是熱情的,親切的,充滿激情的,而帶燈生活則是破煩的,瑣碎的,無力抵抗的。帶燈所面對的櫻鎮,通了火車,蓋起了農貿市場,貧困戶有了低保,河灘上建起了沙場。應該說人們的日子總體上市日漸富足,而各種問題和體制漏洞百出,中國的社會改革到了無法回避的瓶頸期,帶燈的困境也就是當代鄉土中國的困境。
3理想與現實分裂下的鄉土中國
《帶燈》最具特色之處,便是對于當下鄉土中國各種現實矛盾的集中表現。哪怕實在秦嶺里的一個普通鄉鎮,有開放也有閉塞,有富有也有貧窮。金錢,也就是對利益的追求,成為了左右人性天平的砝碼。帶燈如果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民,生活其中也就是平凡一生,不會遍觀世態炎涼。其特別之處就在于有知識,有思想,把一切東西都想得太美好,否則不至于如此痛苦。作家在帶燈這里梳理了兩條思路,一條是主人公面對鄉鎮生活的不得不做卻日漸消磨的激情,另一條便是對靈魂之友元天亮傾吐的心事和愛慕之情。可以說小說中塑造了帶燈的雙重性格,兩條線索相互交織又相互分離,以現實為參照,帶燈浪漫式的理想構筑著當代鄉村最美的圖景。每日的工作是枯燥的委屈的而又充滿憐憫的,而她每日思索的卻是何時能從這種掙扎中得以擺脫。在小說的一開始,作者便定下基調,“帶燈”就是一只帶著一盞小燈的螢火蟲,她孤傲也孤獨,這盞小燈不足以照亮她的人生。久而久之,理想和現實徹底決裂,沒有任何希望的主人公不得已歸于消沉。“地獄不空,誓不為佛。”帶燈最后周身包圍著螢火如佛一樣乘船歸去,不禁有有一種濃厚的宗教意味。這正印證了傳統的鄉土思維,人的命運往往受神明的指引,而對神明的依戀是世人的一種解脫和期待。
《帶燈》表現的正是當代鄉土中國理想和現實的斷裂狀態。在以往鄉土小說對主題的表現上,大都以對社會的控訴,人性的追問以及改革浪潮為主流。在當代,現實性的鄉土作品在對政治理想批判的同時通常忽略了對制度的思考。帶燈所承受的斷裂并非人性的弱點,而是現實制度上的缺失。“它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當代鄉土的復雜性通過帶燈的形象折射而出。作家在設計帶燈結局時很有深意,帶燈并沒有走向生命的終結,這說明作家在內心深處對這一人物還是留有溫情,留有希望。帶燈最后是患了夜游癥,到了夜里一反常態如幽靈般游走,和瘋子張牙舞爪的交談。實際上夜游多發于幼兒和青少年時期,癥狀會隨病患年齡增長逐步消除。早已成年的帶燈患夜游癥在黑夜里摸索,更具有對鄉土中國的象征意味。黑夜里巡行的帶燈,用黑色的眼睛尋找光明,表現著在這片令人壓抑失望的土地上,仍有人不放棄對于希望的追求,一切的夢想似乎仍值得期待。正如作家一再強調,《帶燈》是一個隱喻。也由此進一步了解中國農村,尤其深入了鄉鎮政府,知道那里的生存狀態和生存者的精神狀態。
參考文獻
[1] 賈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
[2]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 賈平凹.帶燈.作家出版社,2013.
[4] 陳曉明.螢火蟲、幽靈化或如佛一樣——評賈平凹新作《帶燈》.當代作家評 論,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