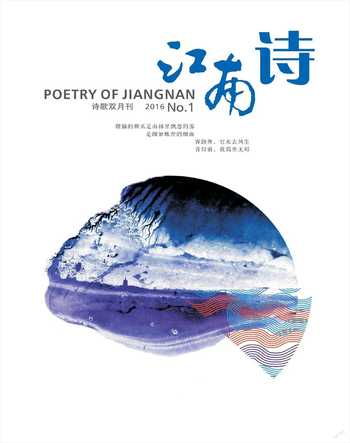美國桂冠詩人娜塔莎·特塞葦詩選
主持人語:
特塞葦是美國第19位桂冠詩人,普利策詩歌的得主。黑人與白人的混血身份為她提供了特殊的起點與視角。她執著地穿行于歷史的記憶,將個人經驗與殖民的歷史相互纏結,為生活于底層的無名者發聲,呼吁人們正視并改變他們被侮辱、受歧視的現狀。特塞葦的詩歌語言散發著超強的現實意味,斷裂、跳躍,口語化,透顯著蜇人的痛感。(汪劍釗)
娜塔莎·特塞葦(Natasha Trethewey),1966年生于密西西比,父親是白人,母親是黑人。2007年,她以詩集《蠻夷衛隊》(Native Guard)獲頒普利策詩歌獎。現任埃默里大學創意寫作教授,第19位美國桂冠詩人。她是1993年以來的首位非洲裔桂冠詩人,以及歷史上獲授此職的第二位南方人。她同時還在密西西比州桂冠詩人任上,是史上第一位國家級和州級的雙桂冠擁有者。
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斯·畢靈頓贊揚特塞葦是“一位杰出的詩人和歷史學家”,其詩“深入個人或群體、童年或百年前的歷史表層之下,探索我們皆須面對的人類斗爭。”她走出個人和家庭不幸的陰影,用詩歌探究歷史的真相,尋找救贖靈魂和改變現實的道路。她的作品在大學課堂被深入討論,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喚醒更多的人正視歷史與現實,從麻木不仁中覺醒。
娜塔莎·特塞葦的母親非常不幸,生為黑人,遭受歧視,在密州與白人結婚竟屬違法,離異后再嫁,1985年與第二任丈夫離婚,隨即被此人謀殺。母親被害時她19歲,正在讀大學一年級。《蠻夷衛隊》的靈感有很大一部分,來自苦命的媽媽格溫多琳·安·特恩布。母親死于非命之后多年,特塞葦才從深重的心靈創傷中稍微平復,寫了多首悼念母親的挽歌,其中就有《墓園藍調》。悲慘的遭遇和莫大的痛苦不僅沒有擊倒詩人,反而成就了詩人。她通過親身經歷和家庭、種族歷史,恢復和復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失去或“抹掉的”生活和聲音,經由她處理的傳統形式被賦予久遠。特塞葦在一次訪談中說,“我執著于保持不變——歷史記憶和歷史刪除。我特別有興趣于美洲和怎樣一個植根于殖民主義的歷史,那種語言和帝國主義、剝奪公民選舉權、人們被奴役的圖解,以及人民因為血統被分開的方式。”
特塞葦坦言,她在寫《蠻夷衛隊》時,并不知道她母親的影子會遍及整部詩集,她最初只是想寫那些黑人士兵不為人知的故事。她回到家鄉,隨著所有必需的歷史調查,“從自我向外看”——那種向外靠進入過去和歷史,帶她深入以前那種曾引導她的事物——一個為她母親創立一座紀念碑的希望愈來愈明確,因為她母親像那些黑人士兵,沒有標志,沒有紀念碑,無以在美國景觀上銘記她從前的存在——一個受侮辱和損害的黑人婦女形象。
以下詩歌依據休頓·米弗林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的英文版《蠻夷衛隊》(Native Guard)譯出。
譯者
照料以馬忤斯的晚餐[1]的
廚房女仆,或混血姑娘
——寫在迭戈·委拉斯開茲[2]之后,
加利福尼亞州。 1619
她是在她面前桌子上的容器
那朝我們傾斜的銅罐,那白色水罐
抓在她手里,那黑的一只有紅鑲邊
且上下倒置。彎腰,她是研缽
和研缽里休息的杵——仍然成角度——
以其使用姿勢。她是一疊碗
及旁邊的蒜頭,由墻上的釘子
懸掛的籃子,也是里面捆綁著的
白布,那前景里的抹布回想起她的手。
她是墻壁上的污漬,大小如她影子——
血液的顏色,拇指的形狀。她是耶穌
在餐桌上的回聲,鑲進她身后的情景:
他雪白的王冠,她的白帽子。她諦聽,倚靠
于她知曉之物。燈光落到她半邊臉上。
推測,1939
首先,痣在每只手上,
那是鍋裝錢——
但新年總是卷心菜,
和豇豆。現在如此,
另一個牢記的諺語,
她的掌心由于有指望而發癢,
她極其信賴預兆——金錢馬上就來。
但從哪來?她左眼跳
預示她會得偏財。
好吧——她厭煩了電梯開關,
那些密閉的艙室,白人的
側視。沒什么,只不過
要想一想,每次制訂計劃
那門滑動著關上。
從新政得到什么?
非常好,像美容學校,
或婦女時裝店——她愛那燙成
波浪形頭發、毛織品和薄紗的感覺,
不是這樣整天閑站著,
不是那電梯搖搖晃晃,上,然后下。
家務勞動
整個星期她打掃
別人的房屋,
她凝視自己的臉
在鍍銅的閃耀里——
鍋底,擦亮的
木頭,她放下蓋子的
馬桶——看起來像在說
姑娘,讓我們做一點兒改變。
但星期天早晨是她的——
給禮拜服上漿
并掛起,一張唱片旋轉在
控制臺上,整座房屋
舞蹈著。她戴著墨鏡
在陽光里清洗房間,
水桶,八角形肥皂。
清潔近于虔誠。
窗戶和門寬幅地擺動。
窗簾跳兩步舞
前進,后退,頸骨
碰撞在盆里,衣服的
唱詩班排隊鼓掌。
上帝離你更近……
她在地毯上打拍子,
用掃帚掃除蒲公英的孢子
一樣的灰塵,每個人
都有事情變得更美好的希望。
比目魚
嗨,她說,把這個戴你頭上。
她遞給我一頂帽子。
你快要像你爹爹一樣白了,
而且你將會一直這樣。
糖果阿姨把她的尼龍長襪
卷下到瘦骨嶙峋的腳踝上。
我也把白色膝長襪卷下來,
讓我的細腿懸掛著,
在水面上方兜著圈兒。
而小魚的銀背
在太陽光斑
與陰影之間,
翩翩飛掠。
你該這樣拿著魚竿
把釣魚線直直地甩出去。
現在,你把蟲子穿在鉤上,
甩出去,等著。
她坐下把煙色唾液
吐在咖啡杯里。
她覺得魚咬鉤時,蹲下來,
直向上猛拉魚竿,
卷著線圈,用力拉
那扭動并拼命抗拒的魚兒。
一條比目魚,她說,你可以看出
因為它一側是黑的。
另一側是白的,她說。
它重重地摔到地上。
我站在那兒,看著那魚兒啪嗒啪嗒地翻筋斗,
跳躍一次,就掉轉一側。
布料工廠
她每天的路途,盡管
后來她不會記得
有多么遠,講給孫子輩——
那樣更合適。
她能保守那些英里
的秘密,還有她的黑臉龐
和黑色的手,還有她黑腳的
粉紅腳底一個小小的麻煩。
她記得她為之服務過的
男人,而且經常地
她與白女人肩并肩
坐著,她們全都
俯身,推進機器的
轟鳴,她們的右腿
抵著踏板繃緊。
她緊閉的嘴唇在說
下班時
有色婦女慢慢地魚貫而出
讓手提包過檢查,
里面攤開,在老板的手上
一覽無余。
不過她笑了
當她記起她把積攢的被弄臟的衛生棉
塞滿一個袋子
放在她的手提包里
亞當的樣子
在一個白人男子的臉上,他的手
已全然知曉。
挽 歌
——獻給父親
我以為如今河里必定滿是
鮭魚。八月下旬,我想象那情景
正如那天早晨:毛毛雨用針
刺繡著水面,薄霧在岸上像一張網
安放在我們周圍——萬物潮濕
而閃亮。那天早晨,我們的連靴褲
笨拙而沉重,我們追蹤
水流,找到我們的地盤——
你逆流而上幾碼,到更遠
和更深處。你必定記得
河水怎樣漫過你的靴子滲入,
而你因為失敗變得沉重。
整天我一直轉身注視著,你
怎樣模仿導游的投擲,
然后投擲看不見的線,在我們之間
切割著天空;并且隨后,手持魚竿,你如何
嘗試——一次又一次——發現
那完美的弧線,一只昆蟲飛行
掠過河流的水面。也許
你回想起我甩線,以及我們
沒能卷起的兩條小鱒魚。
因為我不得不釋放它們,我承認,
我想到過去——操縱著
松了的魚鉤,魚兒翻滾
于我的手中,我放手之前
每一條都滑脫了。如今我可以告訴你
我曾試著抓住一切,為一首
我曾寫的挽歌記錄它——某天——
當那一刻來臨。你的女兒,
我曾是那么殘忍。即使我告訴你
我學會做人又有什么要緊?你一直投擲
你的釣線,而當它不再空空如也地
回來時,卻跟我的纏結在一起。有些晚上,
做著夢,我再次踏進曾經
載我們出去的小船,并注視后退著的岸——
我背對我知曉的我們被帶去的地方。
分類學
——寫在胡安·羅德里格斯·華雷斯
1715年在加州的一系列種族繪畫之后
1.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生產混血兒
畫布是鉛灰色天空
在他們身后,沉重
用文字、金色的字母題寫著
一個血統的等式——
這個加號這個等號這個——仿佛
一個與自然訂的合約,或者
一張博物館的人種學的、
精確的標簽。看
父親的手怎樣,在他的
王冠花邊的下方,
卷發垂在他女兒頭上;
她近乎白皙
就像他一樣的——品質。看見它
在她衣領的領針里
花邊框著她的臉。
一個嬰兒,她被負荷
在仆人左肩,
用一條吊帶
綁在他身上,那淺藍的布
捆扎在他喉嚨。
倘若父親,他的手
在她腦殼上,牧師們——
如同相士做的一樣——
難以推測
她的性格,東拉西扯,
易于辨認的,是光潔的身體,
她柔軟卷曲的頭發,
我們不能確信:他那轉向她的眼睛
那么溫和。
那母親,從側面
掃向他一瞥——
她頭上圍巾
像他的臉一樣雪白,
他涂粉的假發——用一只手
做的手勢
像字母C。看,
她似乎說,
我們都做了什么。
仆人,還是一個孩子,伸長
他的脖子,轉動他的臉,
仰望著他們大家。他是暗黑的,
正如歷史,那詞的起源
蠻夷:血的重量,
一個蒼白的女主人在他背后,
沉重年年。
2.西班牙人和黑人生產黑白混血兒
盡管,幾百年不再麻木不仁
那孩子表達的慍怒。
倘若有光在他內心,并沒有透過繪畫
照亮那留存的他臉龐的
側面——他拱凸的前額,雙眼
在濃重的眉毛下近乎閉合。
雖然在里面,孩子的父親站立
戴著斗篷和帽子。似乎是剛剛進來,
或正要離開。我們看見他
逗留,卷紙煙,近視——
他經過時,眼瞼對孩子
耷拉著。火爐上,
男孩的媽媽歪斜著,警覺地,
她的脖頸在脊柱上扭轉,紅色珠子
套在她的喉嚨像一條血項鏈,
她的面孔那么黑,她幾乎消失
于畫布中,黑暗的墻壁在她上面
我們看見給他們命名的字跡。
這些是我們應該做的嗎?
抹掉這在他們頭上的字跡,
放別的東西在這孩子的位置——
一張桌子,也許,在桌上男人會放
他的帽子,或一條小狗,并以他的觸摸
給予祝福——而這故事
改變了。那男孩是繪畫的一個重寫本——
色彩的圖層,歷史渲染他
中間存在者那種清晰的陰影
此前他什么都不是:空白的
畫布——在形象或字跡之前,在最后的筆觸
把他固定于他的位置之前。
3.西班牙人和女混血兒生產卡斯提佐人
在這個手勢里
怎么沒有看見
殖民地的
精神?
在母親的手臂中,
孩子,維系于
她的子宮——
混血兒
黑暗的發源地
(稱之為墨西哥)——
轉向父親,
觸到他
仿佛退回到西班牙,
那血統煉金術的
承諾——三個簡單步驟
達到純正:
從一個西班牙人和一個印第安人,
一個混血兒;
從一個混血兒和一個西班牙人,
一個卡斯提佐人;
從一個卡斯提佐人和一個西班牙人,
一個西班牙人。
我們在這里看見——
一代人離去——
近乎滑行
她母親小心地抓牢。
4.種族之書
稱之為混血兒的
目錄,或者
密碼之書:
不是西班牙人,不是白人,除了
向后回歸到白黑混血兒,(或者
保持你自己在不確定中),還有
摩爾人,狼,中國人,
黑人,白化病者,以及
那你不理解我、
我不理解你的人。
到殖民地的旅行指南,
每個交叉的出身記錄,
那是血型學的敗壞,
污點:玷污:丟臉的斑:
那么哪一個能是純正的,
那么哪一個不能是——應許之地的
黑色命運。它看起來多么像
一個黃段子:你如何稱呼
那在性的黑暗位置
之間的空間?
稱之為污點——像在
會陰里的一個人和會陰那另一個人——
不正當,不過仍然命名
之間是什么。在她的雙親
之間,那孩子,
向后回歸的白黑混血兒,
不能錯失他們的留存,
那畫進繪畫的三個相連的
他們的身體:她的名字
寫在種族之
書中——歸于一詞
她那類全在受奴役。
知 識
——寫在J.H.哈塞爾霍斯特1864年的粉筆畫后
無論她是誰,她這樣來到我們面前:
嘴唇微張,長發從桌上垂落
像罐里溢出的水,奶頭拉出來
檢查。也許預示著
她將成為目標:一個底座上的骨架,
一排架子上的骷髏。為做一個
理想的女性身體的研究,四個男人聚集在她周圍,。
她是年輕貌美的、被淹沒的——
一個美第奇的維納斯,從大海里升起,沉睡著。
仿佛我們由于褻瀆而誤解這件作品,
藝術家把她的遺體埋葬于光明的
金字塔中,一座科學的圣殿,解剖者
居其上作主持。服役于美——
而了解它——他舉起一片皮膚
在她胸部下面,就像一個人可能拉開床單。
我們無法看到他的一步步剖析,
一種改稱:瑪麗或凱瑟琳或伊麗莎白
給予人體、乳暈、陰戶。以他操作
儀器的試驗——解剖刀,鉗子——
就像一定是冰冷的房間一樣冰冷:所有的男人
穿著嵌入天鵝絨或毛皮的外套——柔軟如下面
她的陰阜。一個男人在吸煙,另一個
歪斜他的頭以便觀看。還有一個,
在桌頭邊,向下偷窺,仿佛
被迷住,他的拳頭在一堆書上。
在畫里這只是第一個切口,
一道精致的創傷:然而多么輕易
解剖者的刀片在我身上打開一個地方,
像窗簾拉上的一個房間,其中
每個博學的男人都是我的父親
而我再次聽見,他的言語——我研究
我的雜交繁育的孩子——用詞不當
分類學,動物學的語言。這兒,
他是他們全體:全神貫注的男人——
一個藝術家,體驗的收集者;他的頭腦
是無神論的角度,他的思想傾向于
我不能了解的東西;知識的信號員,
用指關節敲掉一堆書本;即使
解剖器——他手里的解剖刀像一只鋼筆
懸停在我上方,目標直取我的心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