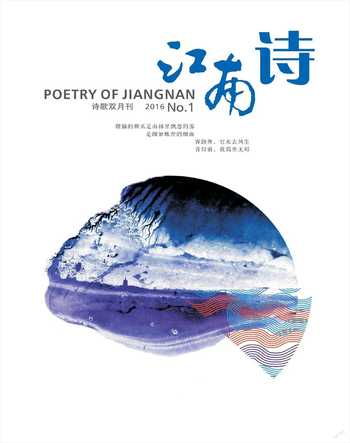有一個詩人住在西溪
梁曉明 程蔚東
主持人語:
作為詩人,程蔚東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別了,舒婷北島”曾引起巨大反響,作為浙江省作協原主席,他是《江南詩》創刊的主要推動者。隨著時間的推移,卸下公職的他在詩歌觀念上有了怎樣的變化,在重新寫作時如何進入詩歌?這是新鮮而令人感興趣的,這里刊出一篇特約訪談和他的一組近作,以供大家賞析。(謝魯渤)
梁曉明:程先生您好,您可還記得,最早接觸詩歌,讀的是誰的詩?
程蔚東:我的青年時代,現在常被說成知青年代,我從中學圖書館封存的書庫里偷來《活頁文選》,讀過古人的作品,后來能讀到李瑛的《紅花滿山》,《棗林村集》,再后來看到了賀敬之的《放歌集》等。讀到現代西方一些詩人的作品,是和舒婷北島顧城楊煉一些人的作品一起讀到的時候了。
梁曉明:怎么會接觸到詩歌?有什么機緣?
程蔚東:我的知青年代是一個文化匱乏的年代。年輕時不想太無聊,看到邊上有年輕人寫的詩,覺得自己也能寫,況且一張紙一支筆的條件就夠了。順便透露一下,我曾經很喜歡畫油畫,可準備全套工具紙質布質畫板材料以及備足所有顏料所需要的錢,在當時對我來說就是天文數字,我一聽就沒有辦法了。年輕人要上進,“文化大革命”了還想要文化,還聽說詩歌是文學皇冠上的明珠,呵呵,寫上了。
梁曉明:我們知道,您90年代成了中國電視劇界的編劇大腕。后來怎么寫電視劇了?
程蔚東:1979年我在【浙江日報】發表了整版的詩歌,在那個年代,這可是件大事,影響很大。又和朋友合作寫劇本,于是就被浙江電視臺看上了,說“發現了一個很瘦的人”,專門調進去擔任專業編劇。寫劇本是我的職業。《子夜》、《中國神火》、《中國商人》、《中國空姐》、《藏書人家》、《金色夜叉》、《你為誰辯護》等,都是在專業編劇的任上寫出來的。
梁曉明:聽大家說您的電視劇總是詩意盎然,這與你寫詩有關嗎?
程蔚東:電視劇居然也能出現詩意,是一種藝術追求的境界了,能呈現出詩意來,也是人生意味的悟道所致。這和作者寫不寫詩無關。我由寫詩入文學之門,詩歌又是一門語言的藝術。所以,我的電視劇文學本,有人說過讀劇本還可以讀到詩歌般的意境。也就是說,除了觀看,劇本還可以作為文本進行閱讀。大概在這個層面上,會寫詩有點作用。
梁曉明: PS北島、舒婷。如此標題的文章,當年在文匯報發出,影響很大,什么背景下?什么原因?導致您寫了這個文章?
程蔚東:上世紀80年代,北島舒婷的詩風成了當時詩歌的主流,我也跟著學了一陣,很想讓自己的詩有新的創造,但慢慢覺得自己和他們不一樣,氣質、學養、人生觀,包括對生活和詩歌的理解也很不一樣。于是我開始了被當時認為是“南方生活流”的詩歌寫作。文匯報發過我一些詩,問我現在的詩怎么不一樣了,我的回答就是,告別舒婷北島了。后來,文匯報發了我一組詩,再后來,舒婷不太寫了,北島不太寫了,我也不太寫了。
梁曉明:南方生活流,很多年輕人恐怕不了解了。請稍微介紹一下?
程蔚東:簡單說就是擯棄了繁復的意象堆積,也不再刻意營造什么空靈朦朧,走更加貼近普羅大眾的口語方式,當時這可是一種完全創新的寫法,一種更加接地氣的新的道路。內容上也注重有生活實感的展示。用一句話來說,可以說是“我們要從天上來到人間”。有一大批人用這種方法在寫。我現在看也不是什么新的東西啦,西方葉芝的《當你老了》,中國木心的《從前慢》,都用過了。
梁曉明:現在怎么看這個事件?以及這種寫作的道路?
程蔚東:其他都不重要了,唯一不變的是走自己的路。特別是創作,最為重要。
梁曉明:縱觀您以前的寫作,無論詩歌還是電視劇,您的內心總有一個大趨勢的判斷和感悟,也就是說,我們要從這些表面很大的題材下,去體味您的內心、思慮和考量。是這樣嗎?
程蔚東:一棵小樹離不開大地,一個人離不開他的周圍。這個周圍可以是你身邊的,也可以是你守望、觀望,甚至是你瞭望的。也就是說,這個周圍可以是小的,也可以是很大的,全面的,全國的,全世界,全人類的。就看你這個人,有沒有這樣一個宏觀的境界和格局。大中可見小。同樣,小中也可見大。
梁曉明:我讀你這期發表的這組詩歌,感覺和你以前很不一樣,無論從視角、抒發情感和認識的起點,等等,都有極大的不同。您是想再走一條新路?
程蔚東:沒有走新路的奢望了。主要是我恰好從崗位上退下來,以前在時代的急速前行中體味人生,退下來了,真有所不一樣。有人說人生風光不再,我看這個“風光不再”恰恰就是現在正常的日子。所謂的“人生風光”其實絕非風光,不過是一種職業擔當。此時,你應該有屬于自己的生活。你在打量世界,世界不再打量你。可是,當你退后幾步,當你真的再打量世界的時候,你反而感受到面前的這些,是真正屬于你了。一種個體的打量開始出現了。我由此突然想寫詩了,不好意思說一句很年輕的話,有一種幸福感。
梁曉明:個體打量。這個詞好。有關這個與這組詩歌有什么具體的聯系和感受嗎?
程蔚東:這其實與我入世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有關。有些人灰心,似乎退了位置都不會生活了。我不一樣,我自己開始打量世界,“打槍的不要,悄悄地進行”,嘿,反而很豐富。比如西溪的大片蘆葦,風中搖曳著身姿,多么珍貴,因為一年就這么一次。那些溪流中搖搖晃晃的船,像不像我們一輩子搖搖晃晃走過來的人生呢?這些都很有意思。經歷了大風大浪,現在我住在西溪,西溪的安靜,是安穩踏實的安靜。這些新寫的詩歌,就是這些心態的直接反應了。
梁曉明:能再具體的說說這些詩歌嗎?
程蔚東:當初寫詩,是覺得需要。無論人生,還是社會,都有需要。所以,寫作時,會考慮一些漂亮的言辭,包括當時的潮流,寫作的趨勢等很多社會的外在因素。現在寫作,特別這組詩歌的寫作,是直接、真實、平順、樸素的寫自己,自己當下的心態和感受。80年代我在【浙江日報】整版發表的詩歌,表現觀察到的世界。當時我還在長興鄉下,很激動啊。當年李小林(【收獲】主編,巴金女兒)編《東海》詩歌,很贊揚我這樣的句子“一背簍青草,一背簍理想,一背簍明天,一背簍歡笑”,這樣一類的思考方式,現在都已經發生了變化,完全過去了,徹底的不一樣了。“西溪的蘆葦,把一生飄揚開來”。我感覺這就像我現在的生活。
梁曉明:最后再請你談談詩歌和人到底應該有怎樣的關系?
程蔚東:沒什么關系,是一個整體。詩歌就是人。怎么樣的詩歌,就是怎么樣的一個人。李白的詩歌背后就是李白這樣的一個人。他的詩歌不會由杜甫寫出來。我們意識到的詩意往往是這個人身上的詩意。說到我個人,我前面說了一個人的打量,這個打量到的詩意實際在這個人身上,而不是風景或者別的。有同志告訴我,不少人喜歡這組詩,我就想我在西溪尋找到的是我現在的生命體悟,是不是有點意思或者還有些意義呢,那就發吧。從這個角度看,我感受到的《西溪》,是我。
2015年11月15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