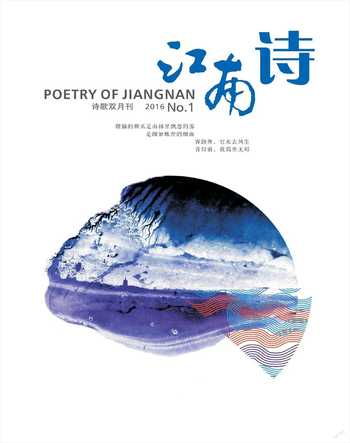水系:淺談潘維的詩歌
主持人語:
潘維是極具“江南性”和“江南風格”的一位詩人,1980年代他從浙北長興開始的詩歌創作,為我們展開了一幅斑斕而獨特的“江南液體地圖”。臺灣青年評論家吳麗宜的這篇論述,繞過“地域”瞄準“時間”,認為潘維詩中以“時間”擊敗“時間”,讓現代漢語找回時間的主導權,從而能描繪“時間中的江南”,描寫出屬于中國傳統固有的生命情狀。面對“線性時間”的困擾,詩人用“隱喻”、“偏離”、“陰性書寫”等手法,完成語言與想象中的江南建構。(沈葦)
在西方詩學的發展中,“時間”除了作為文學探索的內容外,它更決定了文學作品的形式。西方人對時間的理解主要隱藏在作品深層的結構里,亦即西方的文學作品的形式某種程度傳遞了對時間的態度。依照主題的理解、內容的分析來研究“時間”常常只在表象上打轉,雖然這也是不可缺少的部份。從古典主義的模仿論(imitation)到現代主義對歷史的不信任,以及后現代主義支離破碎的時間觀皆一再傳達出時間概念如何表現在作品的形式中。
究其本源,這與西方語言的線狀延伸特性(the linear nature of the signifier)息息相關,特別是聲符之構成語言實為時間線狀的現象。一旦人們開始相信歷史是不連貫的,只企圖抓住一個片刻透視人的一生,語言就成為最佳革命份子。現代主義作家服膺文字“造象”的功能,相信“語言即世界”。他們努力尋找精確的語言符號(如意象、象征),甚至在句子的結構上不斷松散主詞與受詞的線狀關系以挑戰時間的不可逆轉性。而一些后現代主義作家更極端地忽視文法,以“語法的切割”來達成串連性時間的消失。對語言的改造不只是美學上求新的需要,它意味著對時間與空間的質疑,對生命本質的探索。
中國當代詩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詩歌的滋養,特別是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對當代漢語詩歌起了決定性的影響。這種橫的移植也相對帶來漢詩歐化的疑慮。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認為現代漢詩基本上是西方詩的沿襲,非奠基在歷史之上。不管其立論點是否完全成立,現代漢詩的歐化卻是不爭的事實。除了西方詩歌技法的取用外,面對一個趨向西方語言線狀延伸特性的現代漢語,任何一個漢語詩人必須思考如何把“歐化”轉成必然之善,為現代漢詩找出一種新的可能性。詩人潘維就在現代漢詩歐化的歷程中以其創新、成熟的語言將漢詩推向“民族詩歌”的大道,掙脫中國詩歌歐化的緊箍。
潘維的詩能為現代漢詩寫上創新的一頁在于他處理了語言終極的問題,那就是時間:“環繞在我周圍的銅鏡 / 是語言、時間和迷惘的問題《看見生活》。因此他的語言雖從趨向歐化的現代漢語出發,也無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語言線狀時間的牽引,但詩人不僅企圖在詩歌內容上顛覆時間的不可倒轉性,更讓他趨近歐化的語言吊詭地分歧了時間,也就是以“時間”擊敗“時間”,最終超越了時間。讓現代漢語找回時間的主導權,從而能描繪“時間中的江南”,一個非單一的、非統合的中國之域,描寫出屬于中國傳統固有的生命情狀。
這個被時間干擾的詩人必然讓他的詩歌進入四季的時序,在詩歌主題與語言的形式上隨著“時間”而演變。詩人早期的詩歌是時間的序幕,迷漫早晨、春天的氣息:“一百只蝴蝶經過一個村莊 / 一百條道路在水里流淌”《春天一日》, ?“早晨在螞蟻的體內 / 在一滴汁液的火焰里,在時間 / 迷失的眼睛深處 / 就像一株卑微的雜草 / 把生命拉進了它翠綠的波紋里”《像早晨致敬》。這個時期,水鄉的泥土、樹木、花鳥、(雨)水……都是詩人的肉體與精神:“喂養我長大的狼奶 / 除了泥巴 /還有叢林那寧靜的溪流”《上工》。他 “與泥土相愛” ,他的 “眼睛也看到了整個天空”,詩人的水鄉世界在春天里寧靜地勃發。
詩人愛戀他的水鄉,安份地讓他青春的肉體進入線狀的時間里:“我進入時間豐腴的懷里 / 和鳥交上了朋友"《上工》。他偶而悲秋傷冬的情懷并不存在真正死亡的威脅感:“如果我死去 // 一個只有水的地方 / 花朵的眼珠們就會嘰嘰喳喳叫成 / 大森林—— / 憂傷、憂傷、憂傷、憂傷"《一個只有水的地方》。“水”與“花朵”是女子的指涉,死亡成了春天里一首調情的歌曲,沒有深切的悲傷。 水鄉景物按時序而生息:“雨水日子般落下來 / 我把它們捆好、扎緊、曬在麥場上 / 入冬之后就用它們來烤火”《第一首詩》,即使“生活有毒 / 但沒有發明別的糧食可吃 / 我仍用家鄉的尺寸為這年月量體裁衣”《傍晚》。一天天的生活是人間苦樂的重復,直線的終點意味著死亡,但詩人把時間藏在家鄉的空間里,在時間自然的推進中,他依舊像握了剪刀,剪貼時間的形狀。
由于與時間和諧共處,潘維此時期的詩歌雖然多以第一人稱口吻說出,但它的效果肯定偏向客觀的鄉鎮描寫,如同西方古典畫家遵從客觀法則來描繪事物的永恒狀態。所以潘維這類詩歌并無浪漫主義作家的激越,不是在對自然的冥想上得到自然升華、永恒的力量。也因此他的水鄉只蒙上江南一層很薄的薄紗,這個水鄉是一種青春式的水鄉,還未成為江南的專利品,直到《別把雨帶走》、《鼎甲橋鄉》等詩的出現,江南才更明確地在詩人的語言中顯影。
詩人對時間的態度反應在這些“春天”詩歌的語言形式上。與后來的詩歌相較,這些詩歌多簡短,說話者語調平緩,“時間平靜的如一塊雨中的巖石” 。詩中有明確、統一的主題、思緒引領著詞語,語言在現實中顯得自制。詩人未大量使用隱喻、象征、意象等技法來繁殖語詞、或企圖以語言建立新的時間秩序。他讓語言隨時間線狀展開。詩人與時間和平共處,時間決定了語言的風格、決定了詩歌的語調(tone),而語言也反應了詩人的時間觀。
《鼎甲橋鄉》是潘維"液體江南地圖"上的第一個鄉鎮。語言比之前的詩更趨向西方線狀語言的結構,八小節的長詩為長句所構成,有許多描述性的語句。以第一小節12行為例,除了第一行"夜晚,是水;白天也是水"運用明喻(simile)外,詩人不再使用明顯的語言符號。某些詞語甚至是西方的表達:“如果一位國王路過我們這座無名山鄉 / 我不會向他貢獻膠靴和傘 / 我打算呈上我的女仆—— 一位村姑”。“國王”與“女仆”為明顯的西方用語,然而《鼎甲橋鄉》卻可視為潘維“民族詩歌”的成名作。
在此之前的詩大多屬于主人翁與水鄉景物的交融,像一種獨白,《鼎甲橋鄉》卻進入現實的水鄉的風情,讓人物的生活、村莊的形貌從說話者的意識如水涌出,詩人似乎才真正的生活在“人間”,與鄉里人事有了親切的對話:“一位村姑 / 她會插秧、育蠶,并且梳頭”,“孩子們像化肥一樣撒落在 / 田野各處,有時,淋成落湯雞”,“我,冒天下之大不韙,引誘了鄉間 / 最出色的美人兒,并以不給生還者以希望的方式 / 我取她為妻”,“瑟瑟作響的樹葉翻閱本地人家史 / 一天,一位老人轉身進入墳墓……”。村里人物在太湖畔的村莊過著專屬于他們的"狹小生活",他們的村莊如同“一付犬嘴里的臟牙”,而“被咀嚼又吐出的房屋 / 缺肢少腿……”,可“一把木椅已安然度過半個世紀”,水鄉似乎保存在古老的封建歲月中。水鄉細節精準的描述使這首詩的語言雖偏向西方語言線狀結構,也有西式表達的干擾,但其內容的厚實仍讓此詩有了明確江南的記號。從語言的結構反射出此時詩人對時間抱持相對的信任感——“時間,對神靈來說,并不重要 / 對他的臣民也理應如此”。
然而時間注定干擾一個敏感的年輕詩人,水鄉如輪回的日子卻依舊是現實時間永不逆轉的消逝。即使在春天的喧囂里,詩人仍意識到永恒的不確定性:“道路有一付孤寂的面孔 / 只要你貼近它 / 就會有一條冰涼的車轍吱吱碾過你的頭頂 // 就會有更深的痛苦 / 產下蟲卵 // 就會有人拋棄我們 / 或者是我們遠離了村、酒、愛情”《 道路有一付孤寂的面孔》。“道路”意味著離去、改變,不斷重復的開頭詞語“就會”產生短促的節奏感,呼應了車轍的吱吱的聲音,生命彷佛往直線前進,而未知的終點更指涉時間的詭譎。生活在“人性”與“時間”下變動,詩人內心開始蒙上一條孤獨的黑紗。
“產下蟲卵”一方面巧妙地以詩歌技法表達出痛苦的繁多,一方面也直指田野,這是潘維詩歌修辭的一大特色。在他筆下,鄉野景物一一成為新奇、美麗的意象、象征:“我住在鋤頭的靈魂里 / 忘卻了陰謀與工作 ”《遠離人間,為麥種守靈》,“和木炭一樣 / 光線的火鉗把我鑷到那個地方 / 那里,季節暗藏在辣椒里 / 三角形、圓錐體在草木鳥獸的肉里生長”《在遙遠的北方》,“并用成百的少女引誘我 / 到那綠色的泥床上”《風吹著》,“用雨,我點燃倒影……”《別把雨帶走》。“靈魂”這個現代感十足的心靈字眼與農村里的堅硬鋤頭連接,無形的時間彩上辣椒的顏色,理性的數學圖案有了自然的血肉,肉欲像從泥上的青草長出,而雨水卻散發火的熱度。詩人以類似矛盾的語法(oxymoron)描寫水鄉景物,超越自然歌謠的詠嘆。在“春天”詩歌結束時,詩人寫下這些時而清新,時而憂傷的抒情詩,簡練、美麗、自然。
法國精神分析大師Jacques Lacan 以語言結構來分析統一主體的建立。他認為語言的成形是奠定在人、我的區分。脫離母親世界而確認個別主體后便進入所謂以父為中心的“符號的世界”(the symbolic world),語言的本質便注定是非真實的。 主、受詞語法嚴謹的西方語言傳達出時間的線狀現象,在父親的符號世界里,不可逆轉的時間隱藏死亡的威脅,因此回到母親的世界里可擺脫時間的威脅。女子在潘維的詩歌里一開始便是生命與美的代表:“因此,那赤裸、怕疼、缺血的少女來了 / 玻璃從她的肺里涌出 / 美麗在破曉”《絲綢之府》,“別把雨帶走,別帶走我的雨 / 它是少女的血肉做成的梯子”《別把雨帶走》。沉浸在(雨)水、女子等陰性的世界里反應出詩人潛意識里渴求時間永恒的妄念。
因此當單純的水鄉世界進入現實后,一種強大的幻滅感便排山倒海而來,詩人離開他的“春天”,進入他“夏、秋”的焦燥和凋萎。這是由人性的迷惘、生命的虛無與時間的恐懼所打造的牢籠,囚住詩人奔放的靈魂。
水鄉一方面保存古老封建的歲月,是詩人的活水,他自認“保存了最后一滴貴族的血” 。另一方面,古老水鄉卻成了時間虛無、消亡的最佳證據:“現在,一月的薄冰在加劇水鄉的衰老, / ——那皺紋里頹傷的城鎮 / 像醫院里的床單,已病得太久了。”《一月清晨》。“加劇”一詞強化時間入侵的速度,“醫院里的床單”指涉了死亡。詩人對水鄉產生一種矛盾的情愫(ambivalence),水原是生命的象征,然而這個夜晚和白天都是水的地方卻印著死亡的胎記。時間帶著死亡的面具,對這位熱愛封建俗世生活的詩人加上鐐銬:“多年來,只有雨和一座灰色的城鎮 / 還有時間——一付面具,或一付鐐銬” 《荷馬紀元》, 詩人的水鄉在生命(雨)與死亡(時間)兩頭拔河。
詩人恐懼時間的直線性:“——不存在巨大的人 / 只有審判不時從屋外跨進門來 / 失眠,黑色甲蟲,抽屜里的藥片 / 從骨子里我感到了宇宙的荒涼 // 乘坐一列把迷宮的一天拉直成厭倦的列車 / 衰老準確到站,像玻璃上的黑痣 / 我們無法用血重新擦洗真理”《一九九零年的褻瀆》。人性的審判背后更是時間的審判,如果時間只能是直線的,死亡肯定是終站;如果人性使真理變得荒謬,那真理在時間的凝視下更只是虛無、幻象。
對于一個認為“真正的生活不僅在人間,更在語言中”的詩人,語言將是他最佳的利器。他的師傅荷馬“第一個用瞎眼看見了美 / 并用骯臟的指頭再次描繪了美”《荷馬紀元》, 似乎只有詩歌,只有與語言能復活時間: “我,正闖入墓穴,找到了對話的超人”。詩人認為“奧德修的歷程是我內在的命運”,他將在他語言中捕捉時間。
博爾赫斯在《小徑分岔的花園》里試圖以迷宮來解構時間的直線性:“一個錯縱復雜、生生不息的迷宮,包羅過去和將來……時間有無數系列……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組成的網絡包含了所有可能性” 。如果將時間不斷地從直線岔開,不斷被歧路延宕,那么死亡可能緩慢到達。不同于傳統漢語以空間分解時間的直線性,如陳律詩歌中所展現的,潘維的語言趨向西方語言的線狀結構,然而詩人卻不停地分歧時間這條直線。當他開始陷入時間的恐懼后,他的語言開始有了變化,他的語言將反射出他對時間頑強抵抗。
一位江南水鄉的詩人肯定用江南的水圖來解構時間。首先他大量使用隱喻。這些隱喻除了是詩歌技法的巧用外,繁多的隱喻是不斷附加的事物,詞語不斷的繁殖,如河的支流不停從主干分離出去:“夢醒時,我放下夢里的剪刀 / 猶如一節神秘的車廂 / 被旅行點燃,停在顫抖中……一些死亡,一些疲憊,更多的燦爛 / 如一顆在森林中迷途的星 / 在玫瑰花上窺見了指南針”《 燈芯絨褲子萬歲》……“蝴蝶斑紋里的黑夜 / 飛上我的肩膀 / 像一條悲哀的扁擔 / 一頭挑著孤寂 / 另一頭挑著晚宴上的喧鬧” 《 蝴蝶斑紋里的黑夜》 。這些隱喻甚至是兩叁行的詩句,彷佛從原本的事物中分離出別的事物。前引的詩句里,“蝴蝶斑紋”原是描述黑夜的主要意象,然而“扁擔”的比喻卻喧賓奪主,以三行的份量將蝴蝶飛舞的動作暫時打斷。當一首詩里有一連串的喻,當語言繁殖語言,時間便跟著分岔出的語言交錯而行。潘維的時間是一個江南的水系,他以“分歧的時間”抵抗“直線的時間”。
再者,潘維的某些詩常出現“偏離”(digression)的現象。在后設小說的敘事方式中,Laurence Sterne 的 Tristram Shandy 處理了時間的問題。主人翁在偏離和前進的移動中擺蕩(digressive and progressive movements),他認為偏離是陽光,是閱讀的靈魂。他迷失在偏離中,在這些片斷的、不連貫的事物敘述中,時間是分離的,死神也就迷了路。潘維的一些詩里,詩人的敘事方式常虛、實夾雜,在寫實的景物與明確的時間下,忽然分歧出一段虛構的、想象的事物,有時甚至關聯不強。這也是潘維的語言可以不斷繁殖的秘密。詩人并不完全著重在詩歌的整體感、敘述的邏輯性,只讓語言不斷朝語言自身演繹。
以《絲綢之府》為例,從少女的描寫開始,雖不乏比喻的使用,但也可視為景物的寫實,到了第四段忽然轉了彎:“死者的骨灰在水面上漂浮 / 魚鱗的音量擰得很大 / 一直將叮當的鉆機送入礦底 / 為什么那些文件,比旗幟還燙手的鉛字 / 要搗成雪天的紙漿”。一種想象的偏離勝于寫實的統合,即便可以以廣義的內在邏輯解釋,但效果仍是想象的偏離。《在那時》是三段“在那時”的時間各自發展,第二小節甚至以虛構開始:“那時失寵的樂師在街頭演奏莫扎特 / 五月不斷地敲門”。《江南水鄉》雖以純寫實場景開始,卻在第二小節立刻陷入歷史的江南、陰性的江南,場景拉至古代的歲月,從現實的時間分離出,而寫實時間仍在進行。在最后二節,時間返回——“朱漆大門像一部巨書的封面、漫渙的字跡 / 隱約呈現‘春秋……”,江南在“剝落的時間”中腐敗,在中國式的“春秋”里輪回。
而這種偏離更具體表現在《太湖龍鏡》的形式中。此作品由二十首詩所組成,每首27行。每首詩有類似的結構,詩人彷佛隨興抓住一個季節(并不依照時序)、某一天、早晨、黃昏或黎明的某一時段,就以該時間寫實的水鄉景物描寫穿插在詩歌中,或在詩的開頭,或在詩的中后段部份:“是的,今天的木船單調、乏味,載著一只水兔”,“中午,/丑得毫無根據。空虛一遍遍刷著 / 光線、鑰匙、泥濘和農夫的炊具。”“立秋,昆蟲產卵。河流的孩子們 /仍在發燒:這些船只,它們的額頭是鐵制的。”等等。 這些寫實的片斷外便是詩人精密想象的馳騁,不論是陰暗的思緒、狂燥的情感、現實的冷酷,或生命的虛無與體悟。然則這些想象也不以詩的進展循序獲得所謂一番折騰后的神悟(epiphany)。感悟或磨難隨時出現,又可在下一首詩消解。在詩的意義連接上,寫實片段與想象段落的聯結上并不緊密,像從太湖獨立流出的支流,或者說只是各支流匯入太湖。以第十一首為例:“我想通宵跟耗子談論家俱擺放的問題。/我畫了一張草圖:秋天的浴衣 / 懸掛在電線上,有腳爪和雙翅,如含恨的楓葉。/ 如果我醉了,我就是一瓶酒,/就讓眼鏡蛇去毒害火熱的生活。/ 還需一位鼓手,鼓點的麥芒直指農業大廈。/ 一滴水,太湖之水,當她閃耀,/難道你不下跪,稱她皇后。”太湖意象的展開與前幾句的思緒并非毫無相關,但并不綿密。少了整體感的限制,詩人的語言便可以到處叢生,讓詩在語言中展開,讓語言帶領著時間到處重新開始,讓死神找不到路。
對時間的困惑是對現實生活的迷惘,對生命意義的質疑。此階段的詩可說是詩人對前期水鄉烏托邦式生命形態的反動、批斗。詩人陷入現實的泥淖: “與現實相觸的那瞬間 / 我的肌體崩裂,粉碎在人群中”《鐵皮鼓》,他與世界的關系像“建立在一瓶膠水”,還可能“過了使用期限”。“我,也許是薄冰吱嘎的叫喚 /和畫中人換了個位置,走進畫框”《框里的歲月》。詩人似乎在現實里使用過期的時間,與現實脫節,他的“孤獨太冷,需要一盆炭火”《雉城》。詩人對人性感到沮喪,“懂得社會以來,一切就都染上了鼠疫”《生命中流行鼠疫》 ;他“驚訝于幼女轉瞬進化為婦女的加速度”《冷漠》 ;他懷疑“從誕生到死亡,是媚俗軍隊擴編的過程”。甚至他迷戀的雨水都“尸體般躺在了地上”《冬之祭》。詩人的靈魂老去:“即便通過花粉授精 / 或交換青春的辦法 / 我也無法把瘋狂再次推上馬背” 《輪回》。江南水鄉是“一股寒氣 / 混雜著一個沒落世紀的腐朽體溫”,詩人似乎已“聞不到溫暖與愛的消息”《江南水鄉》。這位“悲劇的哈姆雷特”或者只能帶著“一個青澀的吻 / 和一位非法少女”,“轉化為一條紫色巨龍”,埋藏在太湖里,成為水鄉的帝王,以“雨水的墓碑”“點燃你”。在冷酷的現實面前,試圖從水鄉的風情里找回江南古老的、陰性的力量。《遺言》
這種對水鄉強烈的矛盾情愫(ambivalence)迸發了《太湖龍鏡》這首長詩,這是詩人作品的“秋天”之歌。由于矛盾,這首詩與其以“神悟”的最終救贖來解讀,不如以二元或多元“永遠的對話”來理解。詩中段落之間連接不強,它是變動的、不統合的,如水的習性,類似法國女性主義者所推崇的“陰性書寫”(feminine writing)。
經過現實的摧殘后,詩中的人物是生了現代病的人,“奇異的思想簡直就像剛吸完大麻……那連童貞也無法治愈的蒼白;”詩人的城鎮已成為“一件不合時宜的衣服”,他的“家鄉已被擊斃”,而“一個時代貨架般 / 撤空……”。美麗的水鄉景物褪去了顏色:“稻子仍在種植、收割,只是少了幾筐。/網仍在撒,只是魚鱗不再閃亮”,“氣候更換著面具像收集蝴蝶標本,/ 但每張臉都主婦般平庸。中午,/ 得毫無根據。”“……腐敗的草 /像遺產繼承人一樣在臨終的病榻旁東倒西歪。/ 沿蒼蠅的軌跡,可以找到人類孤獨的根源。”水鄉的明亮和蔚藍已不復見。
詩人孤獨、空乏:“我的孤獨像一張蛙皮,在焦灼、欲望、期待的 /分子運動中,正逐漸干裂,如炭火中的唇。”他像“等待戈多”那樣等待著,等待著虛無:“現在,我到了一家劇院。我仿佛在等待誰?”這位保皇派連欲望都腐爛:“……當抽屜一只只打開,/ 蘋果一只只爛掉,而星空凋謝”。世界彷佛被上天遺棄:“這些星星,每一顆都有股鮮魚味,/ 在谷倉之頂,它們玩著紙牌,通宵不眠,/毫不理會一扇木門在吱嗄作響。”詩人筆下的黑夜指涉了現實的威脅、心靈的陰暗,宛如超現實畫家畫中驚恐的世界:“你,站在檢票臺上,恰似一條變態的吸血蟲……獅子也出現了/ 壓著你的眼簾。那皮毛,那骨骼,那重量,/如火焰脫軌般瘋狂,超越夢承受的極限。”這些“兇兆”連夢都承受不住,壓著人,使人難以呼吸。
除了現實生活的迷亂外,一切的不安更多來自生命的虛無、時間的荒謬。詩人質疑生命的價值:“我,為什么要從一粒精子和一粒卵子的 /破裂聲里遙遠的趕來?……”,他知道“無論我多晚出生,總掙脫不了塵埃的造訪。”而“生命柳鞭般易折。/ 沙漏控制著一切,一切皆是必然。”詩人明白不管你如何機靈,“你無法捉住 / 呼吸中的那個時間販子,他逃稅般狡猾,”。在時間的統治下,人們比驚恐亂竄的耗子更猥瑣:“一只驚恐竄過短墻的老鼠,/ 它冷酷的側影充滿嘲諷,似乎 /在蔑視你的心臟。”,在時間的面前,心跳只是一段卑下的節奏。
然而詩人似乎不愿輕易就范,“只要將生與死換個位置,我們便能出死入生”,他想逆轉時間,他要打破單一的形而上世界(the metaphysical world)的束縛:“但我首先要將天堂、人間、地獄放進一只桶里,/ 再撒上胡椒,釀出桶醇酒。”最好的方式是回到“符號的世界”建立之前的樂園,那是沒有時間的母親世界,因此在第十二首中,詩人陷入一連串的陰性意象——山鬼、玫瑰、月光、潮汐、奶水、乳房、蛇、繼母、禿頭歌女等。似乎在這鬼魅的陰性氣息中,時間可以柔軟、可以彎曲。
在這個“永遠的對話”中,一切都是變動的,雖然象征生命的雨、水也有消亡的時候:“而雨珠蹦跳在欄桿上,像一個個 / 嬰孩,被迅速蒸熟、售出,”但水鄉仍是詩人精神的樂園。詩人要以語言創造生活,以詩歌握住時間:“為此,我選中了南方……一種紫狐的氣味,一條玉器的反光之路 / 一粒私通的種子,一滴夢的淡血,/ 一片氣象萬千、機關算盡的繁榮,/一股散出泥土的電流:情欲的噴泉。”這塊狐媚、淫亂、夢幻的陰性樂園激發如電流的強大生命力。水是詩人永恒的泉源:“一滴水,太湖之水,當她閃耀,/ 難道你不下跪,稱她皇后。”他要“以水為材料,矗起一座金字塔……至此,命運加在我身上的咒語之光結束了。”水鄉也是詩人幻像中的神靈:“那神,并不鮮紅,而是藍、紫、綠三色交替顯現。”詩人指出藍為水,綠是田野,而紫乃南方神秘的靈魂,詩人在此完成他的“情感教育”。他自覺是水:“我覺得,我是水,寂靜的淡水”,這滴水穿越時空,“……到過千年之外的秋天,在垂暮的光團中,/ 一位智者的肉體變幻著平原的黃土。” 這滴水是流動的生命形態,詩人超越自我的肉體,經驗人世無限生死,這便是他渴望的永恒。詩歌的秘密、時間的密碼藏在變動的黑暗與光明、生與死對話狀態中。
《太湖龍鏡》在現實的水鄉與永恒水鄉的對話中糾纏地展開,詩人細節性的描寫讓江南水鄉清析呈現,他繪制了他“血管里的液體江南地圖”,而語言如江南水系漫延,多條時間紛流,詩人在歐化的現代漢詩中標上中國的記號。
在與時間的對峙中,真正的解脫更來自對時間完完全全的超越。當我們進入“沒有時間”狀態,我們將不用沿著時間的支流逃亡,也無需與時間對話。詩人經歷《太湖龍鏡》的生、死糾纏后,開始進入“文化”的時間,一種“不朽”的狀態。 為此,詩人必須脫離時間這個對手設計的單向命題,他選擇從死亡出生,而非遵循生息至死滅的定律。詩人進入了他詩歌的“冬季”,他將從冬日的衰亡中找到“不朽”的聚寶盆。
在陰性文化屬性的江南水鄉里,“女子”自然是潘維詩歌永遠的隱喻。雖有各時期的差異,潘維筆下女子常是美、生命與愛的化身,即便在一些水鄉女子寫實的描寫上亦如此。詩人的女子不同于傳統文人的描述,她們肉感、豐美,她們的“子宮不時掉下一些刺”《絲綢之府》 ;她們有物質性,詩人聽見“女孩子一個個掉落,摔得粉碎《春天不在》”。在《給一位女孩》中,女子讓詩人垂涎欲滴:“我喜歡一個黑巧克力一樣融化的女孩。/ 我的旅途皮膚會黏著她的甜味”。詩人用“青苔”巧妙地描寫女子肌膚的觸感:“我喜歡青苔經過她的身體,/那撫摸,滲著舊時代的冰涼;/ 那苦澀,像旋律,使青的旋律變紅。” 詩人以視覺、聽覺、味覺、觸覺等感官來描繪出女子肉體之美。雖然女子也指涉情欲,但詩人的女子更像西方漫游在林間的女神,他讓她的女子在水鄉的世界里以極具肉感的身體存在,并且成為精神上美的女神:“我喜歡她有一個在早晨出生的名字 / 在風鈴將露水擦亮之時,/ 驚訝喊出了她……”。 詩人以“早晨”道出了純潔、無暇,一種精神上的歸屬更勝于情欲的想象。
詩人筆下的女子最后肯定成了詩人對抗時間的女神。他進入歷史、文化中,從死去的時間出發。在《隋朝石棺內的女孩》,石棺內的女孩是詩人的繆斯,也是詩人本身:“我夢見在一個水氣恍惚的地方 / 一位青年凝視著繆斯的剪影”。潘維的繆斯神統領的詩歌王國是女性浪漫柔美、純潔至善的永恒樂園。在這里,詩人將實踐他的美學,并接受他注定的命運:“在我出生時,星象就顯示出靈異的安排,/ 我注定要用墓穴里的一分一秒 /完成一項巨大的工程:千年的等待;/ 用一個女孩天賦的潔凈和全部的來生。”這位繆斯女神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引領他發現時間中的江南”,詩人面對時間,由死亡超脫時間,進入“沒有時間”的時間。死亡只是美的序曲:“而我奶香馥郁的肉體卻在不停的掙脫鎖鏈, / 現在,只剩下幾根細小的骨頭,/ 像從一把從七弦琴上拆下來的顫音”。細小的尸骨顫動悠美的琴聲,美是生命的密碼,穿過“千年”,游走“來生”。
因此,詩人將從冬日的衰落,從一個千年的墓碑找到生的定義。“在蘇堤一帶被寒冷梳理”的冬日里,美與愛復活了蘇小小:“或許,他有足夠的福分、才華,/ 能夠穿透厚達千年的墓碑,/ 用民間風俗,大紅大綠的娶妳,/ 把風流玉質娶進春夏秋冬。”《蘇小小墓前》。時間已不再成為阻礙,與美交合,詩人找到進入永恒的鑰匙。在《梅花酒》中,詩人也于“瑞雪初降”的冬日見到了“死去多年”的“湘夫人”,又一次詩人進入中國文化江南系統里,超脫現實的生與死,給美一個批注。
在現實的定義下,“美,乃為亡國弒君之地”,然而美卻是引導靈魂的幡:“她說:你的靈魂十分單薄,如殘花敗柳 / 需要一面錦幡引領你上升。/ 她說:那可以是一片不斷凱旋的水,也許是一把梳子,用以梳理封建的美。”詩人也在那些亡國后主之列,他也自愿舍棄現實而臣服于美,“以換取漢語修辭”。相對短暫的“人間亡朝”,詩人認為詩歌是一種"高貴的天命",它是永恒不死的。一旦進入歷史、文化系統,那些美的化身的女子——“蘇小小、綠珠、柳如是”和“湘夫人”便吊詭地從死中開始生長——一種沒有死亡的死亡:“但唯有你的死亡永遠新鮮,不停發育。”當詩人想獻上一瓶以時間釀造的“梅花酒”,當他想與美超越時空地對飲,詩人也進入了“沒有時間”的時間,徹底解決了他所恐懼的時間,因為他相信“唯有愛情與美才有資格教育生死”。
在詩人“冬季”的詩歌里,詩人的語言又進入單一線狀的語言狀態,詩思嚴密、邏輯,他收起《太湖龍鏡》的紛雜,彷佛理性地與人交談,對像是不朽的美。不同于早期詩歌里詩人天性流瀉式的獨白,詩人更自覺地處理語言的問題。他有系統地處理文化議題,他更需要一種趨向線狀延伸特質的語言結構。詩人無須岔開時間,因為他找到徹底超越它的方式。
在東西文化交流里,語言是最根本的問題。如果潘維的詩歌是自覺地從語言、時間中展開,以語言、想象建構他的江南,那原是中國式的時間、存有(Being)觀和多元、非單一的主體哲學思維要求了潘維詩歌的語言,這些形式也與當代西方的后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某些觀念不謀而合。在西方語言的滲透下,詩人以他豐富、成熟的語言繪制了“液體江南地圖”,他成功地以中國的顏料為這張地圖上了色。
2006年6月于宜蘭
作者簡介:
吳麗宜,臺灣宜蘭中華國中英文教師,臺灣師范大學外文研究所畢業,現居宜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