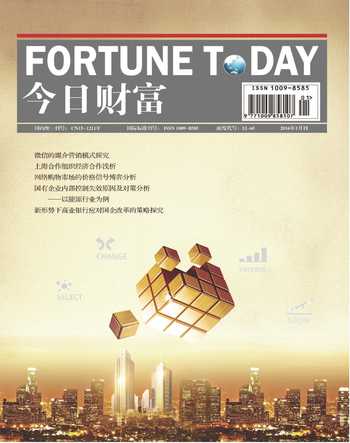司法中利益衡量的法域條件研究
從中外利益衡量理論和實踐的演進來看,利益衡量理論最早是由民事法律領域的法學家提出并使之完善的。民法學界對利益衡量理論研究地最早也最為成熟。就亞洲范圍而言,以加藤一郎、星野英一、梁慧星為代表的學者皆為民法學專家。在當代日本和中國,民事法律領域所涉的利益衡量相關問題研究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并且許多學者有意維持這種現狀。對此一些學者和實務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司法中的利益衡量除了可以應用在民事法律領域之外,也可以適用于其他部門法領域。
一、刑事司法中的利益衡量
隨著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的頒布更加明確了保護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立法和司法精神,例如把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內容首次明確地寫入新刑事訴訟法的總則,給今后的司法工作提出了保障人權的總方針,這旨在平衡公權力和私權利的利益沖突問題。在司法實踐中體現為刑事訴訟辯護率正在逐年上升,辯護人積極搜集證據,力爭證明被告人無罪或罪輕。另一方面,辯護人運用專業法律知識對檢察機關提出的證明材料發表辯方意見,例如司法機關對于證據的搜集和審查依賴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案件的全面供述,以“口供為王”的工作方式時有發生,但在具體實務中我們會發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總傾向于作有利于自己行為的供述,欲逃避法律的懲罰。這給偵查機關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帶來了一定的阻力。對于采用密偵技術手段獲取的證據的證明能力問題也廣受爭議,對于處在合法邊緣地帶的司法問題,辯護人可以在司法程序中重點予以說明,以維護被告人的合法利益。
從司法成本看,證明責任的分配標準是根據雙方的取證能力而考量的。這主要是基于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對司法過程的全局性影響而設定的優選規則。作為代表國家利益的公訴機關具有強大的偵查能力和技術手段,較易獲得證明案件的事實材料。而作為被控訴一方的被告人的法律意識和證明能力在強大的偵查機關面前顯得相當弱小。現代司法理念明確地回答了在新形勢下的司法工作任何有效懲治犯罪保護公共利益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證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問題。
從司法判決的形成過程看,在客觀事實證據材料確實充分的情況下,法官通常能夠基于法律規范,運用邏輯推理徑行作出判決,但當證據材料不能夠充分有效證明案件事實情況,甚至連案件定性都無法明確的情況下,法官就會運用一定的主觀判斷,運用法律思維與客觀案件事實相結合來判斷案情,其實質是司法中的利益衡量。
除上述情勢之外,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通過公訴機關對被告人懲罰,以此司法程序來追究其責任。但隨著公民個人意識的提高,自我權益維護意識的不斷增強,被害方可以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就犯罪行為造成的侵害向被告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經濟賠償,在法庭上還可以提出量刑的意見等積極行為,保證了實現自己利益的有效途徑。
在社會急劇發展的當代,司法中不斷涌現新的利益關系問題。這些利益來自于社會日常生活,例如新醫療技術應用于臨床實驗導致醫療事故的問題,實施安樂死行為的界定問題,使司法工作面臨新的考驗。假如,對損害后果的責任人一概予以定罪并責令其賠償會阻礙行為人生產創造的積極性,但對潛在的犯罪行為現象聽之任之,則會造成社會利益嚴重受損,破壞社會發展秩序。
二、行政司法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理論是在對概念法學的批判中不斷發展。概念法學所主張的法律邏輯圓滿論、法律萬能論在當今時代來看確實不合時宜。利益衡量卻能夠引導法律人在法律與社會事實之間來回穿梭,確切地把握社會沖突現象所反映的實質社會問題。使司法實踐中,注重了對社會沖突的分析,由此轉化成法律思維,為解決案件中具體的利益矛盾提出了科學的法律方法。這種社會利益沖突的根源性探究,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平衡問題是行政審判活動的核心。
利益衡量的邏輯起點——利益的識別,在行政審判中,也應遵循這一司法程序中的方法。在行政審判中利益識別的方法是對案件材料中所體現的相互沖突的利益進行準確的界定,由于行政審判有其自身的特點,它將涉及到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沖突平衡、調整問題,所以在行政審判中,法官要對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否存在沖突進行明確的界定,并且進一步地探析與公共利益是否存在沖突進行明確的界定,并且進一步地探析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各自的具體內容。公共利益的外延涉及面很廣,在理論上很難通過下定義的方法窮盡其全部內涵,若不能結合到具體個案公共利益的法律概念描繪是不會明晰的。個人基于其利益與行政機關的利益沖突,請求法院確認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要求行政機關彌補或賠償因行使其行政權給個人利益造成的侵害行為或停止侵權行政行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公共利益是行政行為的價值導向與核心。例如根據《物權法》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對于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等不動產可以實行征收措施。因此,對于何為公共利益的界定已成為解決此類行政訴訟案件面臨的先決條件。隨著宏觀經濟的發展,公共利益的內涵也在不斷地擴張。在深化改革的初期,法學術語中的公共利益往往僅包括市政工程,動拆遷中的供公眾使用的土地及其地上設施,公辦醫療,教育機構等土地的開發建設。而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向前推進,公共利益的內涵急劇膨脹,不但延用了以往傳統內容,也擴張到了促進就業,工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城市土地規劃與利用,自然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等新的因素,它們皆應歸入當代公共利益范疇。與公共利益相對的是個人利益的實現。作為原告,基于其個人利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是以實現其個人利益為歸宿的。在當今日新月異的社會中,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界定,確立二者的聯系與平衡點是行政訴訟應當運用的法律方法。在司法過程中有法律明文規定的情況下,選擇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價值取向比較明確。法官依照法律規范的直接指引做出公正的判決即可。這種立法精神和司法導向在我國物權法中也得到了體現。個人利益應讓位于公共利益,司法機關在辦理案件過程中應優先考慮公共利益的保護。但在進入到司法領域的案情總是有一些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并且呈大量涌現的態勢,此時,法官應根據案件的實際可操作性和相關法律規定作為評判導向選擇優先保護的利益。
在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確實存在違法之處的情況下,法院怎樣平衡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以及最終為何不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都體現了司法中利益衡量的價值目標。所以考量這些因素,法院經過利益衡量作出上述判決是符合社會利益的。
三、民事司法中的利益衡量
1.利益衡量與民事程序法的運行
利益衡量作為司法過程中存在的一個客觀因素在民事訴訟程序全過程中,無論是實體上還是程序中都體現著法官的利益衡量。認定事實工作是法官在司法過程中的首要任務,在這一過程中要支出相應的成本為代價,但相關費用很可能會超出爭議標的物的金額。這樣就造成了案件中爭議的金額與搜集材料、查明事實產生的成本利益往往不成比例狀況的出現。例如被告搬場公司在為客戶搬家過程中不慎將其明代紅木家具一件受損,原告訴至法院請求賠償30000元,因原告無法準確證明其受損家具的具體價值,在審理過程中法官遂要求對該紅木家具真實價值進行專家機構鑒定,專家機構鑒定等相關費用支出為40300元,在本案中若法官能夠運用利益衡量的方法,通過相關途徑結合相關材料效果應當要優于鑒定。
在民事訴訟法的修改過程中,公益訴訟的問題是討論的熱點難點問題,它不僅引起了立法者、法學家及社會公眾、媒體的廣泛關注,也直接涉及到司法者的利益衡量的運用。在法治體系尚未充分健全,市民社會矛盾此起彼伏的當代,如何擴大社會利益的保護,完善公民權利的實現途徑,不僅是立法者更是司法者應當思索和實際中如何操作的有待探討的一個課題。利益衡量無疑是連接社會利益的擴大性保護和拓展公民權利實現方式的橋梁。研究者和實踐者可以設想在公益訴訟中,公民自覺或不自覺地濫用其訴訟權利或根本就沒有真正的訴訟利益而起訴,無益于社會利益的保護,破壞了法律的嚴肅性的現象,反而會損害法治建設乃至整個社會的法治理念基礎。法院應審查起訴人的訴訟權利是否符合訴訟的要求,以及有無濫用訴訟權利情況的存在,否則應當不予受理。
2.利益衡量與民事實體法律漏洞填補
利益衡量雖然不是法律漏洞填補的方法但它對后者有重要意義。民事法律中所涵蓋的基本原則是民事法律在調整社會關系中的基本價值的體現。特別是法律規范未對具體案件的情形作出規定或法律規定與民法的基本原則,基本價值產生沖突的情況下,司法者應當運用利益衡量方法對案件作出裁判,從法律漏洞填補的角度體現法律的基本價值,例如在一起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中,原告甲訴被告C公司要求其賠償50,000元,并要求賠償精神損失費6000元。案件起因于甲欲在C公司經營的泳池游泳,C公司為健身、美容、休閑大型國際會所,甲系C公司長期會員,不慎在泳池臺階處滑倒,經某市瑞金醫院診斷為左膝關節骨折,花去醫療費、交通費,以及誤工費用等巨額費用,遂提出上述訴求,一審法院審理后認為,原告甲摔傷系意外事件,被告公司在其經營場所也有醒目標志,提醒消費者注意安全事項。
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對事件的發生及其結果均無過錯。但由于原告甲與被告C公司之間存在合同關系,C公司在案件事實上與甲有緊密的關聯性,遂案件當事人應按照公平原則分擔民事責任,判決C公司給付甲人民幣17000元,對原告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不予支持。本案件體現了法官在民事審判中運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實現公平責任原則的司法理念。類似民事案件下加害人均無過錯,在雙方形成合同關系后,與此相關的要求過錯的民法通則第132條已不能適用,若加害人履行了其應盡的合同義務但能預見到損害發生而不采取相應措施加以預防則應認為是有過錯的,應承擔侵權責任。若在現有條件下不能預見到損害的發生及其損害后果,則認為是無過錯,可適用公平責任原則以體現雙方利益保護在司法中的考量。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當加害人和受害人對損害結果的發生均無過錯時,司法者對加害人不加以考慮其承擔責任的形式和范圍,則對受害人而言是顯失公平的,為體現法律公平、正義的價值,法官必須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來實現法律的救濟功能,維護雙方當事人的利益,使利益對比得到平衡。
就公平責任的理論適用而言,其本身僅是一種在損害結果發生時特殊情況下的分擔損失的救濟措施,不具有可歸責性,即使有免責事由的存在也不影響公平責任的承擔,司法理念酌情考量了這種救濟措施,精神損害賠償只能是在加害人有故意或過錯的情況下才適用,在公平責任原則中并不能得到運用,故精神損害賠償請求在類似案件中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此外,司法者在司法過程中還應當注意到民事領域的誠實信用原則,和法治原則,公序良俗原則都可以與利益衡量結合在一起,樹立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例如民法是私法,其中包含大量的鼓勵意思自治的私主體活動精神,在進入到司法領域后,司法者不能用形而上學的片面眼光來審視案件,而應當從案情的性質與發展的高度考量案情,如果民事案件涉及到犯罪行為,則應及時移送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如果意思自治犧牲了社會利益,或以損害國家利益公共秩序為代價則在司法過程中應對這此行為加以否定和制裁。即合理解決私法自治與公共政策、公序良俗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
作者簡介:湯曉江(1979-7),男,上海市人,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教育院2013級法學理論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哲學,法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