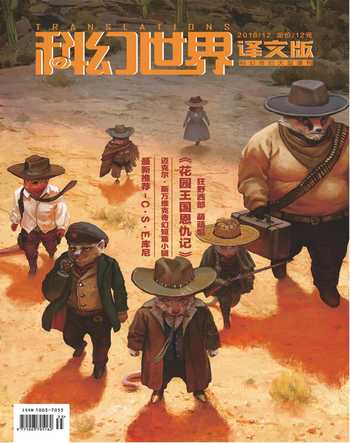Edge of the World 世界邊緣
唐娜、小豬和拉斯去看世界邊緣的那天熱得很。中午的時候,三人坐在加油站的人行道邊,分享一罐可口可樂,看偌大的“星”式運輸機從托德納巴①空軍基地一架架升起,轟隆隆地爬上空中。它們經過時,天空隨之隆隆作響。波斯灣剛出了點事,駐扎在“暮光酋長國”中的一半美軍都處于戒備狀態。
“我家老頭子說,只要用上‘大家伙,最先完蛋的就是基地。”小豬道,“條約不會允許我們守衛它。一枚炸彈飛來,然后就‘噗——”他輕聲模仿核爆炸的聲音,“——灰飛煙滅。”他穿著迷彩褲和卡其T恤,上面的印花是“管他們是好是壞,統統干掉,讓上帝分辨好人壞人去吧”。他摘下眼鏡,在T恤上擦擦。唐娜發現沒了眼鏡,他的神情顯得懈怠、空洞,戴上眼鏡后又重新鮮活起來。眼鏡在他臉上,簡直跟面具差不多。
“你才沒這運氣呢。”唐娜道,“不管是不是世界末日,周一早上卡蘇吉夫人照樣要收作業的。”
“對啊,你說她怎么這樣?”小豬道,“口音那么怪!什么都要你背!行行好吧,我說,誰在乎阿克羅尼翁是不是美岑圖斯王朝的一部分?”
“你應該在乎,笨蛋。”拉斯道,“學校開的課里,就本地史還算行。” 唐娜認識的男孩里數拉斯最聰明,雖說他經常不及格,都快被勒令退學了。“老天,那晚我翻開《史詩選》,原以為又是老掉牙的廢話,結果一直讀到天亮。一秒鐘也沒合眼就去上學了,不過總算從頭到尾讀了個遍。全世界就屬咱們這兒最古怪,歷史上盡是龍和魔法和稀奇的怪獸。你們沒發現嗎?十八世紀,英國公使館有三個成員被惡魔吃了!這是寫在歷史書里的!”
唐娜完全搞不懂拉斯。他倆第一次見面是在美國學校的舞會上,兩人的伴兒都不合適,只算在那兒消磨時間。拉斯想把手伸進她褲子里,她狠狠給了他一拳,險些打斷他的鼻梁,血順著下巴往下淌。直到現在,她仍舊記得他吃驚的大笑聲。從那以后他們就成了朋友。只不過友誼總有局限性,她正等著他主動突破,希望他能趕在她父親調換駐地之前行動。
在日本時她認識一個姑娘,她用剃刀在自己手掌心刻了男朋友的名字。當時唐娜萬分不解,這種事怎么做得出來?她那位朋友聳聳肩說:“只要能讓他注意我。”唐娜一直不理解,直到拉斯出現。
“奇怪的國家。”拉斯的表情像在做夢,“據說在邊緣之外,天上全是惡魔和蛇之類的玩意兒。他們說如果一直盯著看,你會發瘋。”
三人面面相覷。
“好吧,見鬼,”小豬說,“咱們還等什么?”
世界邊緣位于鐵軌背后。他們騎著自行車穿過美國飛地,進入當地老街。這里的街道十分狹窄,路邊的院子里塞滿破爛的卡車和銹跡斑斑的巴士,甚至還有游艇,船身壓扁,好塞進架子里。車庫門仿佛一張張黑色大嘴,嘶嘶地吐出電焊的火花,被鍛造金屬的敲打聲震得不住跳動。鐵路與工業街交匯處有一叢低矮的杏樹。他們把自行車藏在這里,步行跨過鐵路。
時間改變了靠近邊緣的這部分城市。高塔中的弓箭手不見了,他們防衛的威脅一直不曾出現;有著上千扇窗戶的薔薇石英宮殿不見了,在過去,這座宮殿的所有窗戶沒有一扇是朝向邊緣的;城垛也不見了,從前有盲眼樂師在上面吹奏樂器、迎接黎明,如今它們只存在于卡蘇吉夫人的課本里。現在這里是一排陰沉沉的老舊工廠,下層的窗戶或者用煤渣磚堵死,或者砌上磚頭。磚石夠不著的窗戶則交替刷成一個個灰色和淺藍色的方塊。
蒸汽汽笛拉響,工人拖著步子,魚貫回到工廠。他們穿著斜紋棉布褲和白襯衣,都是棕色人種,是從敘利亞、黎巴嫩引進的勞工,專做托德納巴當地人不肯碰的工作。裝卸碼頭旁立了一個籃筐,破破爛爛的籃網孤苦伶仃地隨風飄蕩。
防風柵欄有一塊塌了。他們手腳并用爬了過去。
三人穿過一片空地,工廠大樓里傳來響亮的哀鳴。前方又一處廠房抬高嗓門,哐——哐——哐的聲音仿佛頭痛一般緊緊抓著人不放,節奏感十足。工廠紛紛從中午的困頓中蘇醒,重新開工。唐娜問:“他們為什么沿著世界邊緣建這些東西?”
“好把化學廢料從邊緣倒下去。”拉斯解釋道,“俄羅斯保護國倒是在這兒修過涵洞,但工廠是在涵洞被埃米爾①國有化之前建起來的。”
工廠背后有一堵齊胸高的混凝土墻,邊角粗糙,水泥被緩慢侵蝕,顯出坑坑洼洼的樣子。墻腳長了一團團野草。這堵墻之外便是空空蕩蕩,只剩下天空。
小豬帶頭跑過去,朝世界邊緣之外啐了一口。“嘿,還記得尼克松訪問時說的話嗎?這么高,掉下去可不得了。什么人吶!”
唐娜趴在墻上。薄霧將天空染成灰蒙蒙一片,又在目光的焦點處增強成臟兮兮的棕色,仿佛在她的視界中心塞了一個盲區。她往下看,眼睛老想抓住地面,但看到的卻還是天空。遠處飄著幾片絲絲縷縷的云,僅此而已,并沒有蛇盤曲在空中。她本該失望,可說實話,她原本就沒抱什么期望。她見過的自然奇觀都是同樣沒勁兒,無論瀑布、間歇噴泉還是壯美的遠景,都少不了電線、欄桿和停車場,雖然明信片上并沒有這些東西。拉斯全神貫注盯著前方,活像凝眸的老鷹。他的下巴緩緩動著,唐娜真想知道他看見了什么。
“嘿,瞧我發現了什么!”小豬一聲歡呼,“有梯子下去!”
兩人來到他身邊。樓梯是混凝土和鋼鐵做的,公共機構中常見的式樣。它沿著絕壁盤旋而下,延伸向無限遠之外一個并不存在的“下方”,最終消失在模糊的藍色中。小豬仿佛被自己嚇住了,他悄聲問:“你們說底下有什么?”
拉斯說:“想知道的話,只有一個法子,不是嗎?”
拉斯一馬當先,接著是小豬,最后是唐娜。樓梯在他們腳下發出沉悶的聲響。巖石上滿是涂鴉,噴涂的字母已經磨損。潦草的黃、黑、紅色字母重重疊疊,被時間和風雨侵蝕,無法辨認。鐵護欄上也有許多單詞、箭頭和三角形。有用記號筆寫的,也有用小刀或指甲刻進漆料里的:尤爾根·本·沙依斯柯普夫。克魯小丑樂隊。打倒撒旦美帝國主義。十七級臺階過后就是第一處樓梯轉角平臺。上面臟兮兮的,有棕色碎玻璃、剝落的水泥、煙屁股和浸透水的半溶紙盒。樓梯往反方向折過去,他們跟著往下走。
小豬問:“你們吃過河豚嗎?”不等對方回答他便接著說道,“那是日本一種有毒的魚,烹調必須非常小心,廚師得有專門的執照。就算這樣,每年也要死好幾個人。據說是很棒的美味呢。”
拉斯道:“哪有什么東西能好吃到這份上。”
“不是味道。”小豬熱情洋溢,“是毒。是這樣的,適當的烹調過后,還會有一點點留在魚片里,你會吃到閾值內的劑量。你的嘴唇和手指尖會變冷,變麻木。這樣你才知道吃的是真貨。你才知道自己真正活在生死邊緣。”
拉斯道:“我早就活在生死邊緣了。”見小豬哈哈大笑,拉斯仿佛有點吃驚。
一輪胖嘟嘟的月亮飄在空中,顏色蒼白,仿佛融化在藍色水里的冰盤,它蹦蹦跳跳跟著他們一路往下走。地上散落著套了泡沫塑料的蘇打水罐子、踩扁的萬寶路煙盒和碳化的火花塞,三人隨腳把它們踢開。在一處轉角平臺上,一輛壓扁的購物車擋住去路。小豬只得用力把它掀到護欄外,目送它落入深淵。他沉吟道:“這兒的垃圾還真多。”平臺上有股淡淡的尿味兒。
“再往下會好些。”拉斯說,“咱們還在靠近頂上的地方,下班以后誰都能過來大喝特喝。”三人繼續前行。遠遠地能看見工廠的管道向空中排出棕色液體,液體流出管道時先是變寬,接著緩緩消散成七彩水霧。距離給這些排放物增添了美感。
唐娜不安地問:“我們準備走多遠?”
小豬嗤道:“妹子,別慫。”拉斯沒吭聲。
越往下走,樓梯就越破敗,養護狀況也更糟。護欄上經常缺了一段段鋼管,有些地方油漆剝落,那些將樓梯固定在石頭上的螺釘則變成了胡桃大小的一團團鐵銹。
沿途的石穴里藏著有袋目哺乳動物,爪子像針那么尖,見有人經過就發出啾啾的警告聲。填滿黃土的縫隙中長出一簇簇野草和飛蛾一樣白的龍膽草。
幾個鐘頭過去,唐娜的腳、腿肚子和腰越來越酸,但她絕不肯發牢騷。漸漸地,她不再看旁邊和天空,只管抬手、抓住欄桿、把身體往前拽。她盯著自己的雙腳在視線中出沒,覺得全身汗涔涔的,好不凄慘。
她家里還有篇作文才寫了一半,那是關于1810年3月的“三日事件”:拿破侖親自命令法國占領軍朝邊緣外的虛空連續開炮,希望制造一場威力無窮的暴風雨,傾瀉在他的敵人頭上。到頭來,法軍制造出的僅僅是一片火藥形成的煙霧。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范圍控制天氣的失敗嘗試。唐娜覺得今天的下行同樣徒勞,只是無休無止、令人疲憊的運動,不會有任何結果。就像她的生活。每次父親更換駐地,她都決心要作出改變:這次她一定要成為另一個人,無論付出什么代價,哪怕——不,尤其是——要偽裝成違背自己本性的形象。去年在德國,她跟一個開阿爾法羅密歐汽車的當地男孩約會。她沒用手幫他擼,而是用了嘴。當時她想:從今往后一切都會不一樣了。然而并沒有。
永遠沒有任何改變。
“當心!”拉斯道,“這兒缺了幾級臺階。”他一躍而下,運動鞋落在樓梯平臺上,發出空洞的碰撞聲。小豬跟著跳了下去。
唐娜猶豫了。總共缺了五級臺階,往下二十英尺,樓梯才又折回來出現在她下方。這里的巖壁向外突起,如果腳下打滑,她很可能不會落在樓梯上。
兩側的巖石似乎正在離她遠去,她突然意識到,她之所以還能存在于這個世界,靠的只是腳下的這一點點物質,幾乎不足以讓她的雙腳站立其上。她的四周是一片虛無的天空,這片天空又延伸向無限遠處,深不見底,空無一物。她可以張開雙臂落入它懷中,墜落下去,永遠觸不到底。那時她會怎樣呢?會饑渴而死嗎?或者下落的速度會不會變得太快,擠跑她肺里的氧氣,讓她在無垠的空中窒息而死?
“來啊,唐娜!”小豬朝她喊。“別慫!”
她聲音顫抖:“拉斯——”
但拉斯沒有看她。他朝下方皺著眉,迫不及待想繼續走。“別逼迫女士。”他說,“我們自己接著走就行。”
憤怒、委屈、絕望——種種情感交織在一起,讓唐娜喘不上氣來。她心跳飛快,深吸一口氣,縱身一躍。天空和巖石在她頭頂旋轉。有那么一剎那,她在空中飄蕩、下落,完全無法控制自己,腦中只有一個驚恐的念頭:她要死了。但就在這時,她重重地落在樓梯平臺上,痛得要命。她真擔心自己擰了腳脖子。小豬摟住她的肩膀,用手指頂著她的腦袋。“我就知道你能行,膽小鬼。”
唐娜一掌拍開他的胳膊。“好吧,機靈鬼,你準備怎么把咱們弄回去?”
笑容從小豬臉上褪去。他張開嘴又閉上,猛一抬頭,滿臉慌亂。雜技演員倒是可以縱躍過去、抓住梯級、翻身而上,完全沒問題。“我——我意思是,我——”
“別操心這個,”拉斯不耐煩地說,“會有法子的。”他繼續往下走去。
唐娜意識到,拉斯不太正常。他一心想沿著梯級向下走,仿佛著魔了一般。就好像那次他把他父親的左輪手槍帶來學校,還說他早餐前剛玩過俄羅斯輪盤。他驕傲極了:“三次!”
此刻他臉上是相同的瘋狂表情。她不知道自己怎樣才能幫他,那一次不知道,現在也毫無頭緒。
拉斯走路的動作像個機器人,一言不發,不知疲倦,既不加速也不放慢腳步。唐娜跟在后面,憂心忡忡地沉默著。小豬則在兩人之間來回跑,跟寵物獅子狗一樣嘰嘰喳喳。唐娜覺得這畫面實在恰如其分,幾乎像是寓言:他倆在一起,卻又各自孤獨,兩人之間的距離充滿噪音。她琢磨著這距離、這沉默。太陽已經落到巖壁背后,午后的熾熱不再銳利。
鋼制樓梯變成了被水泥包裹的磚塊,全靠釘進石頭的小型支撐物撐著。有一處拐角平臺上堆著櫻桃的莖和核,上方的護欄被鳥屎染成了白色。小豬趴在扶手上說:“嘿,底下有海鷗,到處飛。”
“哪兒?”拉斯也趴到扶手上,然后輕蔑地說,“那是鴿子。過去伽佐蒂斯人放出來練步槍射擊的。”
小豬轉身跟上拉斯,繼續往下走。唐娜瞄到一眼小豬的眼睛:霧蒙蒙的,充滿無助和絕望。她只在他眼里見過一次這樣的恐懼,那是好幾個月之前,她上學路上去了他家,那時埃米爾剛剛遇刺。
起居室拉著窗簾,從屋外晨光里走進來的唐娜覺得屋里陰沉得不自然。電視機閃爍的藍光落在架子上,隱約照亮好些陶瓷小像:德雷斯頓的擠奶女工,尚蒂伊的陶瓷工人,梅森的巴哥犬——金鏈子從幾只狗的大下巴上穿過,把它們串成一串。還有代夫特的赤裸仙女在跳舞。
小豬的母親穿一件軟趴趴的晨衣,頭發沒梳,一手端了杯油膩膩的咖啡,坐在那兒看葬禮直播。唐娜沒想到她這么早就起床了。大家都說她酗酒很厲害,哪怕按照軍嫂的標準也是完全失控。
“瞧他們。”小豬的母親說。屏幕上是莊嚴的隊列,有駱駝,有凱迪拉克,還有一身傳統長袍、裹頭巾戴墨鏡的各路酋長。歐洲使節也紛紛攜眷出席,夫人們都穿著很有品位的灰色衣裙,巴黎流行的式樣。
小豬在廚房里大聲問:“你把我的午飯放哪兒了?”
埃米爾最小的兒子才四歲,父親的棺材從面前經過時,他行了一個額手禮。“孩子真可憐。瞧瞧他媽,哭得好像心都要碎了——”
唐娜說:“他們太傷心了——”
“別跟她說話!”冰箱門砰地關上,櫥柜門砰地打開。“媽!我那該死的午飯在哪兒?”
她好不容易才把目光轉向他,她的下巴繃緊了。“你跟我講話少來這套,年輕人。”
“好啊!”小豬吼道。“好,我就不帶午飯去學校!反正你也不在乎!”
他轉身拉住唐娜的手腕,把她拽出門去。在他拉她手之前的那個瞬間,唐娜突然覺得四周仿佛一片沉寂,她只看見小豬眼中那片迷茫的無助。跟她今天瞥見的神情一模一樣。
護欄變成了木頭材質,半數的木頭欄桿底部已經接近腐爛,偶爾還缺了幾根,多半被之前來過的人擰掉、扔下了世界邊緣。唐娜膝蓋突然一軟,踉蹌著差點撞上石頭。“我得歇歇,”她真恨自己,“再多一步我都走不動了。”
小豬立刻癱倒在樓梯平臺上。拉斯遲疑片刻,也走到兩人身邊。三人坐在平臺上,腿越過邊緣懸在空中,胳膊抱緊欄桿,盯著面前的虛空。
小豬在一堆破爛中間找到一個百事可樂的易拉罐,商標用的是飄逸的阿拉伯字母。他左手拿易拉罐,右手用自己的刀子在上面戳洞,一次又一次,咯咯笑著,活像神經錯亂的變態罪犯。他開開心心地說:“消滅你們!”說完這話,完全沒有過度,他又問:“我們怎么爬回去啊?”見他神情如此凄惶,唐娜咬住嘴唇才沒哈哈大笑。
拉斯說:“聽著,我就只想再往下走一點點。”
小豬似乎有些煩躁:“為什么?”
“再下去一些,好躲開這些垃圾。”他指指煙頭和棕色的碎玻璃。現在這些東西比上面少些了,但依然存在。“再一點就行,伙計們,成嗎?”他的聲音繃得緊緊的,在那之下還有一絲難以察覺的哀求。唐娜拿那雙眼睛毫無辦法。真希望只有他倆在,她好問問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拉斯指望在底下找到什么呢?唐娜懷疑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覺得只要自己下得夠深,就永遠不必回去了?她記得有一次,在亨里曼先生的代數課上,氣氛突然緊張起來。她抬頭去看教室另一頭的拉斯,只見他正全神貫注地把數學課本一頁頁撕下來,又一頁頁扔到地上。為這事兒他被停學五天。唐娜一直沒弄清他為什么要那樣做。但他的行為里包含著某種美麗的傲慢。拉斯生錯了時代。他真該生為中世紀的王子,比如美第奇家族的人。
唐娜說:“好吧。”小豬當然也只好答應。
又下了七段樓梯,現代的樓梯走到了盡頭。最后一段樓梯很短,總共只八級臺階。樓梯的護欄被整個扯下來,扔在梯級上。他們小心翼翼地在扶手和欄桿之間落腳,好容易走到底,卻發現最后的樓梯平臺后面還有臺階,就刻在石頭里,是一道道彎曲的凹陷,歷經千年的雨水和踩踏,已經極不平整,幾乎無法通過。
小豬呻吟道:“兄弟,你不會指望我們走那玩意兒吧。”
拉斯說:“沒人咨詢你的意見。”
他們手腳并用,頭上腳下地倒著爬下古老的臺階。風乍起,威力不小,將他們時而推向這一側,時而推向另一側。有幾次唐娜嚇得要命,覺得自己準會僵在原地,再也沒法行動。但石頭臺階最終變寬,成為一道寬闊、平整的巖脊,靠巖壁一側還有好些山洞。
巖壁被苔蘚染成白綠色,看得出古時候花了不少工夫打磨、雕琢,只有洞口處保持了自然的模樣,沒做修飾。每個山洞之間都有大腿豐滿的女人——也許是女神,也可能是惡魔或者神廟的舞者。女人們手持一圈圈葡萄藤,中間纏繞的是周期變化的月亮:從新月變成四分之一個上弦月,再到滿月,接著又是四分之一個下弦月,最后變暗。小豬氣喘吁吁,臉上汗淋淋、紅撲撲的,但他還是那么喜歡咋咋呼呼。“我說,這些鬼東西都是什么呀?”
“這里以前是個寺廟。”拉斯道。他順著巖脊往前走,神不守舍,嘴角帶著一絲奇異的笑意。“我讀到過。”一扇青綠色的轎車車門擋住了他的去路,不知是被誰扔下世界邊緣,又被風向變幻的大風刮到了這里。他們已經下得很深了,車門是這里唯一的垃圾。“來搭把手。”
他和小豬抬起車門,前后晃動三次,最后將它高高拋下巖石外沿。三人都趴在地上看它下墜。它一圈圈翻轉,越來越小,最后竟仿佛閃爍起來。它仍在下墜,終于落到目力可及的范圍之外,成為深淵中一粒不斷移動的塵埃。唐娜翻過身,腦袋從巖石邊縮回來,躺著往上看。巖壁似乎在緩緩向前翻滾,整個世界都朝她壓下來,冷酷無情,令人眩暈。
小豬提議:“咱們去洞里瞧瞧。”
所有山洞都空空如也。它們只向石頭里鑿進去三十英尺深,但全都精雕細琢:拱形天花板上雕刻著成千幅仿鑲嵌裝飾的圖案,墻上飾有浮雕的柱子。柱子之間的墻面上鑿出長長的擱板,但上面的東西一件也沒留下,哪怕陶瓷碎片或者半截骨頭都沒有。小豬用他的輕便手電筒照過每一處陰暗的凹陷。“有人在我們之前來過,東西都被拿走了。”
“多半是負責記錄歷史的人。”拉斯伸手撫摸一張石頭擱板,它的深度和高度正好放一排三磅裝的咖啡罐。“這是他們存放頭骨的地方。當某個僧侶的精神高度發展、不再需要物理存在支撐自己的時候,他的同伴就會把他骨頭上的肉刮干凈,把他的頭骨供奉起來。他們把蠟灌進他眼窩里,趁熱塞進蛋白石,讓自己睡覺的地方永遠處于這位前輩微微閃爍的目光下。”
三人走出山洞時已是黃昏,天空由藍色褪成紫色,第一批星星出現在天幕背后。唐娜低頭看著月亮。它像餐盤一樣大,又圓又亮。溝紋、干涸的海、山脈,全都異常清晰。中間的某個地方就是靜海基地,尼爾·阿姆斯特丹插下美國國旗的地方。
“老天,已經這么晚了。”唐娜道,“我們得趕緊往回走,否則我媽會大發脾氣的。”
小豬提醒她:“該怎么上去我們還沒想出法子呢。”然后:“多半只能留在這兒,學著吃貓頭鷹,在巖壁上斜著種糧食,開創我們自己的文明。唯一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兩性之間數目失衡。不過這也是可以解決的。”他摟住唐娜的肩膀,伸手去抓她胸部,“你會為咱賣力干的,對吧唐娜?”
她憤怒地推開他:“嘴巴放干凈!你這些幼稚的言行我受夠了。”
“嘿,別激動,開個玩笑嘛。”驚慌的神情又回到小豬眼里。這種驚慌緣自意識到自己并不能掌控全局、永遠不可能掌控全局,并且所謂的掌控根本不存在。他勉強擠出笑容,想安撫對方。
“一點也不好笑。”憤怒讓她臉色煞白、渾身發抖。小豬攪了她的好事。她本可以跟拉斯聊聊,弄清他到底為什么這么不快樂,讓他終于可以真正注意到自己。可偏偏小豬在這里,她的機會全毀了。“我受夠你了。不成熟,滿嘴臟話,舉止下流。”
小豬漲紅了臉,結結巴巴地想說什么。
拉斯從兜里掏出裹在錫箔紙里的大麻,還有當地產的錫制煙斗。珊瑚雕的斗缽,當地乞討的孩子賣兩毛九分錢的那種東西。“有人想嗨一把嗎?”
“你個混蛋!”小豬笑了,“你不是說抽完了嗎?”
拉斯聳聳肩,“騙你的。”他仔細點燃大麻,吸一口之后遞給唐娜。她接過煙斗,手碰到他的手指,感到一陣冰涼。她的目光從煙斗上方投向他的臉。他閉著眼,臉很瘦,有種禁欲修道者的氣質。透過藍色煙霧,那張面孔顯得十分蒼白,仿佛基督的臉。在那個瞬間,她熱烈地愛上了他,渴望為了他的幸福而犧牲自己。嘴唇間的煙斗柄很熱,幾乎有些發燙。她深吸一口。
煙刺激著喉嚨,接著涌進肺里,打著旋兒收緊,最后沖上她的腦袋,往里面填滿嗡嗡作響的和聲:空氣、天空、她身后的巖石,全都在嗡嗡震顫。在致幻的快感中,她的頭骨像氣球一樣撐大了。她不得不睜開眼睛、然后又張開嘴。她岔了氣,痙攣似的咳嗽起來。她沒想到自己肺里竟能容納這么多煙,這些煙正一縷縷噴出,散入宇宙。
“嘿,當心!”小豬從她手里奪過煙斗。她的手指似乎離自己很遠,皮膚上有星星點點的刺痛,仿佛她肉體的黑暗中亮起微小的恒星。“你把葉子弄撒了!”傍晚的光線里充溢著能量,天空涌入她眼中。她盯著漸漸暗下去的空氣。月亮從她腳下升起,群星仿佛童話書插圖中一般親密、友好。她感到心平氣和,遠離俗世的憂慮。“跟我們講講那座寺廟,拉斯。”十年前央求父親講故事時,她用的或許就是這種口氣。
“對啊,跟我們講講那座寺廟唄,拉斯大師。”小豬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不過隱隱地有種挖苦的意味。小豬總在奉承拉斯,但兩人的關系有時也有些緊張,這類含譏帶諷的小小挑戰并不少見。典型的次一等雄性的嫉妒心,靈長目心理學入門課上的經典案例。
“它很老,”拉斯說,“出現在現有的一切教派之前,甚至在瑣羅亞斯德教教徒橫穿海峽之前。當地的神秘主義者宣布棄絕世界,到世界邊緣的絕壁生活。他們鑿了往下的樓梯,而且一旦下去,就再也不上來。”
小豬質疑道:“那他們吃什么?”
“他們用意志讓食物出現。沒騙你們,真的!這是他們創世神話的一部分:太初有混沌與欲望。世界被欲望,或者說意志帶出了混沌。他們所說的混沌就是未成形的物質。那之后的敘述有點亂,畢竟它不算真正的宗教,更像是一種魔法體系。他們相信世界尚未完成,而且由于某些復雜的原因,世界永遠不可能完成。因為這個緣故,世界邊緣之外仍然殘留著過去的混沌的痕跡。只要某個人對此有足夠強烈的欲望,同時遠離俗世中的一切,他就能接入這股力量。從前,那些神秘主義者下到這里,在月光下冥想、創造奇跡。
“別忘了,它不是類似西藏密宗那種精致的宗教,更像原始的泛靈論,一種強迫宇宙滿足自己需要的方法。那些圣人到這兒底下來,然后,他們會用意愿得到想要的東西,比如財富:嵌紅寶石的掐絲銀杯、大堆的月亮寶石、比大馬士革鋼更銳利的精靈骨匕首,等等。可是,他們不應該追求這些東西。所以得到以后,他們就把這些東西全部扔向邊緣下面。巖壁上一路都有這種寺廟。離世界越遠,靈性就越高級。”
“那些僧侶后來怎樣了?”
“有個國王——是叫阿薩扎嗎?我忘了。這人貪財如命,于是想了個主意:派稅吏下去,搜刮僧侶們弄出來的一切。他多半是這么想的,嘿,反正僧侶自己也不要,對吧。這么干是極大的褻瀆。僧侶們氣壞了。領頭的神秘主義者、所有重量級的精神領袖,全都聚集起來開了個大會。誰也不知道這是怎么做到的。有一本經典說他們可以在巖壁上橫著走,如履平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不重要。總之,有天夜里,他們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僧侶,大家同時冥想。他們一起吟誦,說,阿薩扎單單死去還不夠,因為他犯了褻瀆之罪,必須承受前所未有的悲慘命運。他必須被撤銷,被反轉,消減成比亙古以來的一切都更微不足道之物。他們還祈禱再也不會有阿薩扎這樣的國王,祈禱他的生命和歷史都被撤銷,讓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么一個國王。
“就這樣,阿薩扎不存在了。
“可是,他們對湮滅的渴望太強烈了。阿薩扎不再存在,當他的歷史和家人都不再存在,但僧侶們卻依然感到怨恨。而這時阿薩扎已經變成從未存在過,于是,僧侶們不知道自己的怨恨從何而來。因為不知道原因,他們的仇恨就指向了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對于毀滅的愿望。于是,就在那一晚,他們也不再存在了。”說到這里,拉斯沉默下來。
最后小豬問:“這種瞎話你也信?”他沒得到回答,就又說,“全都是假的,伙計!明白嗎?沒有魔法,從來都沒有。”唐娜看出他真的生氣了:他尊敬的某個人竟然似乎相信魔法。小豬漲紅了臉,每次不知所措時他都這樣。
“沒錯,全是鬼扯,”拉斯語氣苦澀,“一切都是鬼扯。”
煙斗又在他們手中過了一圈。唐娜仰面躺著,目光投向遠方。“如果我能有一個愿望,猜我想要什么?”
“大奶子?”
她太疲憊,心中一片空白的感覺又太舒服,于是很容易地無視了小豬。“我會希望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小豬問。唐娜懶洋洋的,沒興趣跟他解釋。她揮手把問題擋開。可小豬堅持不懈:“什么怎么回事?”
“一切。我是說,一直都是這樣,我發現自己在跟別人講話,卻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不知道他們在玩什么把戲,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要這樣或者那樣做。我希望自己知道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月亮飄在她面前,又大又胖,像獅鷲的蛋一樣圓,閃著力量的光。她能感到那力量沖刷著自己:混沌已然衰敗,但它的輻射卻如背景般在空中擴散。即便此刻,當混沌已經一遍遍被耗盡,仿佛一枚被不斷撫弄的硬幣,磨損得十分厲害,已經到了不存在的邊緣——但那里依然存在著力量,足以夷平行星。
她盯著那肥碩的月亮,感到無數個可能的世界在流動;在那個充滿魔法的冰冷銀盤里,她感受到了拉斯口中的原始修道士。雖然不可見,但他們依舊存在著。那些人的心靈她完全不懂,但她卻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要說確切、實在,這力量的不比唐老鴨更實在,卻并不因此就減少了威力。她陷入了清醒的幻夢,在這夢里,天空充滿力量,而且都能為她所用。僧侶空手坐在自己的祈愿缽前,和她只有一線之隔,只隔著虛無縹緲的、由絲絲縷縷的時間與現實形成的一張紙。在一個長如永恒的剎那,所有的可能性在她兩側雁翅排開,全都同樣真實恰當,沒有誰比誰更為真實。然后,她的大腦移回此刻,世界重又活動起來。
“我嘛,”小豬道,“我只希望知道該怎么爬過那段缺失的樓梯。”
三人沉默片刻。唐娜突然意識到,這正是完美的機會,她可以知道究竟是什么事讓拉斯這么不快樂。如果她提問時小心措辭,如果問對了問題,或者如果她僅僅是撞了大運,也許他會對她吐露一切。她清了清嗓子:“拉斯,你的愿望呢?”
拉斯用最最陰郁的聲音回答道:“我希望自己不曾生下來。”
她轉頭想問他為什么,可他不見了。
“嘿,”唐娜說,“拉斯去哪兒了?”
小豬一臉古怪地看著她:“拉斯是誰?”
回去的路很漫長。兩人一同扛著那段木頭護欄,小豬時不時冒出一句:“嘿,我這主意簡直棒極了對吧?這東西正好當梯子。”
“對,棒極了。”唐娜總是這么回答,因為如果她不應聲他就會生氣。每次她哭起來他也會生氣,但這事兒她實在沒辦法。她甚至沒法解釋自己為什么要哭,因為世上的所有人里——包括他所有的朋友、熟人、老師、甚至他父母——只有她還記得拉斯曾經存在過。
最可怕的是她對他并沒有任何具體的記憶,只大致知道他在的時候是什么感覺,此外還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渴望和失落。
她連他的長相也不記得了。
出發時小豬問她:“你想走前面還是后面?”
她回答說:“后面。如果我走前面,你會一路盯著我的屁股看。”當時他貨真價實地紅了臉。沒了拉斯,小豬不必再硬撐著,仿佛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安靜,一點也不粗魯。他甚至沒講臟話。
然而這并不能讓唐娜開心,因為只要在他身邊,她就自動洞悉了關于他的一切:他之所以虛張聲勢,是因為缺乏安全感,以及內心沒有滿足的渴望;他每晚自慰,而且總是帶著自我厭惡;他鄙視自己的父母,卻又徒勞地想從他們身上找到一絲絲愛的跡象;他對待她的方式是出于以上所有這些,以及一些別的原因。
她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慈悲的上帝啊,她祈禱,等我到了頂上,愿我不再有這樣的理解力吧。或者,別讓上面的情形也這樣痛苦,別讓知識這樣令人傷痛,別讓最最無辜的話語下面隱藏著如此可怕的秘密。
他們扛著沉甸甸的木頭往上走,走上返回世界的路。
責任編輯:李克勤
- 地出自鄧薩尼勛爵的《奇譚路》。后文多處地名都出自這部著名的奇幻作品。
- 斯林國家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