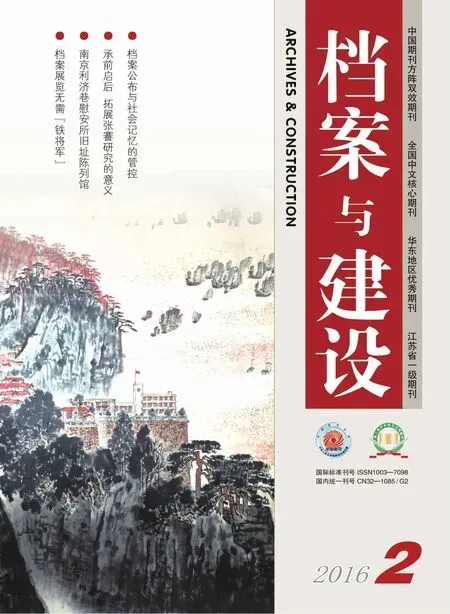張謇眼中的日本
周至碩(海門市張謇研究會,江蘇海門,226100)
?
張謇眼中的日本
周至碩
(海門市張謇研究會,江蘇海門,226100)
19 24 年4 月,日本的青年會到南通參觀,張謇在歡迎演說中指出:“日本決不能鯨吞中國,強為之,轉足自斃。”歷史的發展完全印證了張謇的預言。張謇何出此言?張謇心目中的日本是怎么樣的呢?這對今天我們認識日本大有參考價值。
一
光緒二十九年(1903),日本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開幕,日本駐南京領事天野托徐乃昌轉送一份請帖給張謇。其時,張謇在南通的自治事業剛剛起步,很想看看日本在明治維新后是怎樣迅速崛起的,另外張謇對日本早就十分關注,十分警惕,于是欣然接受邀請,東游日本。
張謇東游日本回國后,整理了一本《癸卯東游日記》,對日本的國內治理作了一個比方:“日人治國若治圃,又若點綴盆供,寸石點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國若烹小鮮’,日人知烹小鮮之精意矣。”[1]
在日本的70天中,張謇歷經20個大中城市,參觀教育機關35處,農工商機關30處,考察日本教育、實業的歷史、現實,虛心學習,取人之長,為吾所用。

張謇考察日本的《癸卯東游日記》
五月初四,張謇到博覽會農林館參觀,了解到日本開發北海道的歷史,感慨萬千:“北海道開墾圖最詳,與通海墾牧公司規畫同者,墓地有定,廛市、道路皆寬平;不同者,田不盡方,河渠因勢為曲折。其不同之最有關系而大者,北海道故有大林,而我墾牧公司地止荒灘;北海道無堤,而我之墾牧公司地非堤不可。伊達邦成、黑田清隆之致力于北海道也最有名,然竭其經營之理想,勞其攘剔之精神而已。國家以全力圖之,何施不可?寧若我墾牧公司之初建也,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謗之人,有抵拒撓亂者之人……”[2]
張謇看到日本政府全力支持開發北海道的政策,內心的觸動很大,啟發很大。因此十年之后,張謇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之時,受權主持擬定了《國有荒地承墾條例》《邊荒承墾條例》《國有荒地承墾細則》《森林法》《森林法實行細則》《造林獎勵條例》《植棉制糖牧羊獎勵條例》《獎勵農牧產案》,實行獎勵制度,設立獎勵基金,激勵國民開荒造田、植樹造林、種棉、制糖、養羊,資助農牧民改良樹種、棉種、甘蔗品種和綿羊品種,促進農牧業發展。
張謇認為日本的教育也很成功。1903年的端午節這天,張謇參觀了大阪市小學創立30年紀念會。會場設在大阪城市的陸軍練軍場,張謇在日記里記述了紀念會現場:“時風雨大作。至十點鐘,學童奏洋喇叭,軍樂繼作。日太子與妃乘雙馬車自東北隅至,周北西南三面徑去……學童之集者四萬人,風雨交作而學生行列不亂,三十年之成效也。”[3]張謇十分佩服大阪市小學創辦30年的成就。張謇更多的是參觀了其它各類學校,特別是農村小學,了解日本學校教學的內容、方法,以至學生的伙食、桌椅的尺寸等等。張謇回國后,更加堅定“父教育,母實業”的信念,在南通地方大張旗鼓,興辦國民普及教育、職業教育。凡小學350余所,紡織、醫學、農業、女工等職業學校10余所,還籌備創辦了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吳淞水產學校、吳淞商船學校和中國公學,支持興辦三江師范學堂、上海復旦公學、上海商科大學等多所學校。
張謇還參觀了日本的銀行、造幣、港口、航運、制鹽、紡織、農場等各行各業,每到一處,都與國情相比較,都與南通地方自治相對照。以后的20年里,張謇在南通等地創辦了紗廠、鐵廠、油廠、酒廠、陶瓷廠、印刷廠、墾牧公司、輪步公司、漁業公司、銀行等30多個企業,以及醫院、公園、體育場、養老院、殘廢院、育嬰堂等16家公益慈善機構,還有1910年在江寧府倡導舉辦南洋勸業會等等,這些舉措都與他東游日本有關。
張謇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國內建設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張謇與日本人直接接觸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他在十余年后《歡迎日本青年會來通參觀演說》中說:“東游時曾為師范校聘教習數名,鄙人與日人為友自此始。”[4]其時有好多位日本人被張謇聘請,派到通州各學校、工廠去擔任教師和技師,這批人是1903年春天日本教科書案件的受害者。張謇在東游日記里記錄:“嗟乎,日人謀教育三十年,春間教科書獄發,牽連校長、教諭等近百人,今察其工商業中私德之腐潰又如此,以是見教育真實普及之難,而人民性質遷貿于開通,有期然而然之勢。然以不信不義之國人,而冀商業前途之發達,是則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之行矣。聞半年來,中人受誑于日人者復有數事,其甚細者,值僅五圓。”[5]那時候,這些因教科書而涉案的校長、教授有的被定罪,有的停職閑居。張謇感到,在日本讓教科書把歷史的真實面目告訴后人很難,而誠實地面對歷史、面對現實,是實業發展的關鍵所在。之后,他聘請這些有良知的日本精英到中國,在南通的地方自治中發揮不少作用。
張謇在日本考察的70天里,留存《東游紀行二十六首》。張謇途徑馬關春帆樓,揮筆抒懷:“是誰亟續貴和篇,遺恨長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須記取,春帆樓上馬關前。”[6]春帆樓是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署之所,是華夏子民的傷心之所,集聚了國人的奇恥大辱,張謇認為這里是(中國)游人第一須記取的地方。8年之前,張謇得知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悲憤之情奔涌于筆:“和約十款,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由此可見,張謇訪問日本的發端和目的在于“師夷制夷”,圖強雪恥。

張謇修葺的曹公祠(1919年)
二
張謇對日本的認識是比較深刻、全面的,他對日本政府的侵略擴張外交深惡痛絕。
早在光緒八年(1882),朝鮮兵變內亂,日本借題發揮,干涉朝鮮內政,企圖顛覆朝鮮,進而以之為侵華跳板。清政府決定派淮軍首領吳長慶帶兵赴朝平亂。而29歲的張謇正是吳長慶軍幕的機要文書,深得器重。入朝平亂中,作為主要幕僚的張謇“理畫前敵軍事”,參與重大決策。由于張謇深諳中、朝、日三方形勢,因此,在平亂中立下奇功。張謇的突出貢獻在朝鮮影響很大。黃炎培在《朝鮮》一書中,記述了韓京的吳武壯祠。祠中的“去思碑”刻勒了吳長慶赴朝平亂的歷史。“朝鮮壬午之變,中國政府調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率登州兵以七月度韓鎮懾,亂既定,韓人倚若長城。居三年,移駐金州,旋卒于軍,謚曰‘武壯’……附光緒八年隨征將士賓吏題名:首列幕賓,優貢江蘇通州張謇;第五名,訓導江蘇海門廳周家祿;第十名,舉人江蘇泰興縣朱銘盤。皆以文學著稱者。第二十一名,為營務處同知河南項城縣袁世凱。”這方去思碑是由金允植、沈履澤書寫。金允植,朝鮮領選使,即引領吳長慶部隊入朝的朝鮮使者。
光緒八年八月十八日(1882年9月29日),入朝平亂的慶軍凱捷回朝,途經天津休整,張謇撰寫了《朝鮮善后六策》,全文2500字。該文在海外漂泊132年,于2014年10月由韓國回歸中國南通。六策內容為“通人心以固國脈”“破資格以用人才”“嚴澄敘以課吏治”“謀生聚以足財用”“改行陣以練兵卒”“謹防圉以固邊陲”。[7]張謇感到,朝鮮的叛亂雖平,但日本的賊心未死,后患依舊,因此提出善后六策,以壯大朝鮮國力,抵御日寇侵略。張謇把《朝鮮善后六策》分呈中朝兩國政府。然而,清廷樞臣斥之“多事”,朝鮮政府也未“善后”,致使12年后的1894年7月23日,日本軍隊攻占漢城王宮,挾持國王李熙,成立傀儡政府。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戰,偷襲豐島海面的清軍運兵船,制造“高升”號事件,引爆中日甲午海戰。
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張謇一再警示清朝政府,警惕日本的狼子野心。1894年7月12日,張謇撰寫《代某公條陳朝鮮事宜疏》,認為中朝唇齒相依,唇亡則齒寒,因此提出八條援護朝鮮的建議。這八條建議御敵于前,中國完全有援朝抗日獲得勝利的可能。但是清政府的“主和派”貽誤戰機,渙散軍心,招致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一敗涂地。
甲午戰爭后,救亡圖存成了張謇最強烈的愿望。
三
晚清以來,中日之間的軍事摩擦與戰爭,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猖狂的罪惡,給兩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和痛苦。和平是兩國人民最強烈最根本的愿望,為了這一愿望的實現,張謇作了不懈努力。
張謇認為,中日可和,但一味“求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怎樣才可能實現中日和平?張謇在《馬關條約》簽訂后所擬的《條陳立國自強疏》中闡述得比較全面,提出練陸軍、治海軍、造鐵路、分設槍炮廠、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多派游歷人員等建議。自強方能立國,自強方能贏得與鄰邦和平。的確,發展才是硬道理。張謇奏請光緒皇帝:“時時存必戰之心,事事圖能戰之實,自然有可和之時機,無輕和之后悔。是以戰為和者,千古中外不易之長策。”[8]
為了“存必戰之心”“圖能戰之實”“有可和之時機”,張謇做了大量的實實在在的事情。1919年他在南通狼山為明代抗倭英雄曹頂修葺曹公祠,并撰寫《重修曹公祠碑》及曹公祠聯語。碑文回顧日本在明初侵擾我沿海七省的歷史,以及戚繼光等民族英雄抗擊倭寇的事跡,特別生動地描述了曹頂在南通重創倭寇的業績以及在單家店壯烈犧牲的情景,期望“縣之人能以重頂者自重如頂,淵其智,岳其氣,一夫而萬夫,一世而十世,其可也,何有于國仇。”[9]張謇題寫的曹公祠聯語有二:“匹夫猶恥國非國,百世以為公可公”“北郭留名單家店,南山增氣曹公墳”。
在南通城南,有個埋葬當年被曹頂殲滅的倭寇的倭子墳,張謇在墳上建了一座京觀亭。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張謇重修曹公祠,建筑京觀亭,是為了強化記憶,呼吁國人牢記歷史,不忘過去。張謇做得更多的在于教導國人勿忘國恥,振興中華,自強自立,為國分憂。

張謇在倭子墳上修建的京觀亭(1919年)
1923年5月9日,南通學生集會紀念“五九國恥日”。“國恥日”源于1915年5月9日袁世凱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條”要求,全國教育聯合會把5月9日定為“國恥日”。張謇在集會上發表了《五九日國恥紀念會演說》。他分析了喪權辱國“二十一條”簽訂的原因:“民國四年今日之辱國條件,吾人無暇責日人之強梁,要亦當時吾國時局不振,自執政以迄四民,均擾攘如亂絲,日人乃得以乘間抵隙,肆其無理之要求也。國民如能團結精神,培養實力,如個人之調和血氣,則國恥何從而生?”[10]張謇說:“征之歷史,以善雪恥著稱者,莫如越王勾踐。愿諸生志勾踐之所志,將來畢業后,為農者必蘄為良農,為工者必蘄為良工,為商者必蘄為良商,以今日聯合集會之精神,貫注于永久。”[11]張謇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復興壯大民族,向往堅守和平。
同時,張謇利用中日民間團體互訪等機會,表達中日可和的觀點。1910年6月,日本實業團訪問江蘇,張謇作為江蘇咨議局長發表了招待頌詞。6月20日的《申報》刊登了張謇《招待日本實業團頌詞》。張謇說:“敝局為政治機關,所包者廣,原不盡以實業為限,然國民以政治之接觸,往往影響于實業前途。今日歡聚一堂,以政界之承迎,可知國際和平于發展實業之道,兩國交受其福。”
1924年4月,日本青年會到南通參觀,張謇發表了歡迎演說,他指出:“日本政府對國民之政策,誠為盡善,惜其對華之侵略政策,則未免太拙耳。鄙人嘗謂:中日親善則兩利,否則兩不利。日本決不能鯨吞中國,強為之,轉足自斃。曷能同舟共濟,合力以捍御歐美耶?果親善也,則兩國前途,必燦爛光明;如其否也,前途殆不可思議。”[12]
中日和平是張謇的夙愿,他積極守望,努力爭取。他深知和平需要維護,而最好的維護辦法是讓祖國強大起來,強大是抵御外族侵略的最有力的盾牌。因此,張謇竭盡全力,經營南通自治,以之示范全國。
參考文獻
[1][2][3][4][5][6]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8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第538、540、540、579、554、389頁。
[7]張季直:《朝鮮善后六策》。
[8]《張謇全集》第1冊,第12頁。
[9]《張謇全集》第6冊,第514頁。
[10][11][12]《張謇全集》第4冊,第553、554、579-5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