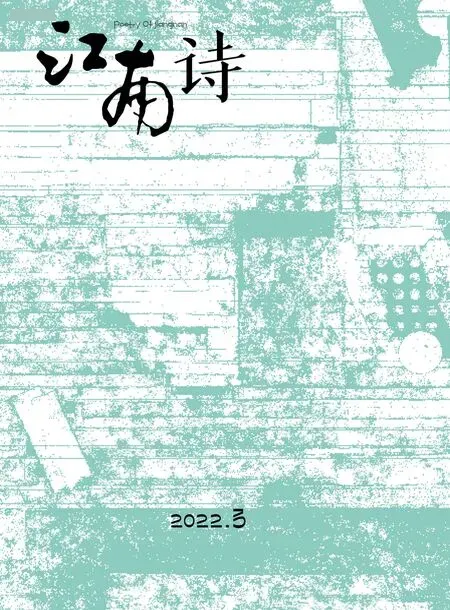在跨界之中散懷抱
◎汗漫 Han Man / 冷焰 Leng Yan
?
在跨界之中散懷抱
◎汗漫 Han Man / 冷焰 Leng Yan
一支筆,一根自救的浮木
在異鄉、在紙上,復原故鄉
冷 焰 :我們先談談地域的跨界吧。我記得,我們認識是1985年春,在鄧州,我們組織了一個《星島》詩社,當時你在縣委組織部工作。那時你經常來我家玩,第一蹭飯,呵呵,第二談詩,惠特曼、桑戈爾等等。后來,我去鄭州一家報社,你去了南陽一所高校。再后來,2000年吧,你去了上海,見面的機會就不多了。談談地理上的這一跨越,從中原故鄉到南方上海,從小城市到大都市,對你寫作和生活的影響。
汗 漫:我們彼此見證對方的青春,哈哈。1984年,大學畢業在鄧州工作,在范仲淹寫《岳陽樓記》的這座城市里,我的寫作和職業生涯開始起步,形態、表情都很有詩人氣質哈哈,長頭發,寡言,在縣委大院是一個另類的人,不合時宜,很迷茫。1989年到南陽一家高校,認識了妻子,生子,詩歌寫作初有收獲,在九十年代詩壇有了動靜,2000年參加了詩刊社的第十六屆“青春詩會”,算是一個標志。到上海,是2000年秋,當時妻子在上海讀碩士研究生。我經過面試、筆試和考察,也來到目前所在的這家中央企業工作,從辦公室文秘做起,到目前的管理崗位,一路走來,似乎從一個“詩歌的人”變成了一個“散文的人”——顯著標志是,頭發剪短了,煙戒了。
移居上海,標志我進入了中年,生理、心理都發生了變化。比如,漸漸適應南方人熱愛的米飯和糖,漸漸聽懂鳥叫一樣的滬語和蘇州評彈,漸漸在南方地理、人文兩個層面的游歷中完整了對古老中國的認知。但我也漸漸認識到自己的孤單——回到河南,河南已經把我當成上海人;在上海,上海把我當成一個外地人,或者叫做“新上海人”——這是上海發明的一個稱呼,北京、西安好像都沒有發明一個“新北京人”“新西安人”的說法。這是上海的狡黠,對那些闖進這座城市的異鄉人,既接納又微微保持一點距離、一絲優越感。但在上海,我也享受到一種小城市里所沒有的自由度和人際關系上的疏離、寬松,這有利于寫作。我慢慢喜歡上這座城市,并因此對河南、對南陽懷有一種背叛感和愧意。
這些年的寫作緩解了孤寂,并獲得精神同類的回應。通過寫作,澄清個人生活中渾濁的部分,使內心得以安定。蘇東坡說得好:“吾心安處是故鄉。”
冷 焰 :你這些年的寫作,不論散文還是詩歌,盡管題材已經轉換為你當下的個人生活,側重于南方經驗的傳達,但我仍然能夠看到你的中原背景。或許拉開與故鄉的距離,反而更有助于辨認自我?地理空間的轉換,更有利于生成出表達的復雜性和沖擊力?
汗 漫:是的。我覺得,在劇變中的當下,每個人的故鄉都只能暗藏于個人的身體和記憶。現實中的家鄉已經不是“故鄉”,與童年、少年時代的風物、情感,已經完全脫節、悖離。你回到故鄉,人們“笑問客從何處來”——我們都成了客人。所以,一個人最后的鄉土,就是自己的骨頭和血肉。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與故鄉之間的時空距離,是有益的,像看一幅油畫,太近了只能看見色彩顆粒。在異鄉,一個人才能完整地擁有故鄉,在紙上復原、重構一個故鄉。所以,移居或旅行,就是跨來跨去,對一個人內心的豐富與整合都有意義——這可能也是我為自己背離故鄉所尋找的托詞。慚愧。
三十多年的寫作史,我已經遠離了最初“成名成家”的浮躁欲望、“進入文學史”的野心、雄心,而感恩于寫作所帶給我的福祉:我能夠用自己的筆作為一座還鄉的棧橋,而不至于無所歸依。
我喜歡兩個關于詩歌的定義:米沃什說,詩是見證;希內說,詩是糾正。可以說,寫作就是見證生活、糾正內心。我們這些能夠寫作的人,與一般人相比是幸福的——寫作在幫助我們辨認自我、重構生活。語言給予我的已經夠多了,而我回報語言的卻那么少。很慚愧。
散文是寫作者的個人史,是散懷抱
冷 焰 :我注意到你移居上海后,散文的寫作量大了,而詩歌也還在持續地寫,這兩種文體之間跨來跨去的“動力學原理”是什么?你更愿意把自己的身份確定為“詩人”還是“散文家”?
汗 漫:我用詩歌語言的標準對待自己的散文寫作,力求精準、獨到,所以寫得不快、不多。這些年來,散文寫作的量稍稍多于詩歌,可能因為散文是一種自傳性的文體、中年文體。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生活的延展,很多個人經驗無法在詩歌中保存下來——詩歌是一種減法性、蒸餾性的寫作,會過濾掉許多蕪雜的情節、細節;而散文需要這些情節、細節中的蕪雜,以便還原生活的本相。布羅茨基在談到詩歌和散文這兩種文體時也說:一旦遇到三個人以上相處的問題,詩歌就不方便處理,只好借助于散文(大意如此)。
我喜歡布羅茨基。他把散文當成一首長篇敘事詩來寫,所以他的散文依舊充滿了詩歌的準確性、自由度和感染力。《文明的孩子》、《小于一》、《理智與悲傷》,他這三部散文集,從九十年代開始到2015年之間陸續翻譯為漢語并出版,成為我的散文寫作標高。要謝謝布羅茨基,也要謝謝他的翻譯者黃燦然、劉文飛。正是布羅茨基、曼德爾施塔姆、葉芝、博爾赫斯等等詩人身份的散文家——還有本雅明和羅蘭·巴特,他們本質上也是詩人——持續以漢語的面孔來到我們面前,使中國九十年代以來的散文文體有了“革命的資源和動力”——這是異域詩人對漢語的貢獻,也是中國詩人紛紛在散文中“揭竿而起”的背景和后盾。
可以說,這些年來,好散文大都出自詩人手中,比如周濤、鄒靜之、于堅、沈葦、陳東東、黑陶、雷平陽、龐培等等。他們也在越界、跨界,姿勢很漂亮,動靜很大。但他們本質上依舊是詩人——詩人的使命就是發現,祛除種種的遮蔽,建立全新的表達。我希望自己的寫作實驗,能夠為恢復漢語的活力做出一點貢獻,不論詩歌還是散文。至于我是詩人還是散文家,或者叫做“詩人散文家”,我并不在意呵呵。
冷 焰 :你剛才提到了作家本雅明和羅蘭·巴特,這也是我所喜歡的兩個思想者。在你關于上海的散文,例如在《人民文學》發表、兩度獲得年度“人民文學獎”的《一枚釘子在寧夏路上奔跑》、《婦科病區,或一種藝術》和《直起身來,看見船帆和大海》等作品中,我也看到了本雅明們的詩性和思辨力,為我認識你的生活、認識上海,提供了一個獨到的視角。談談你的散文觀以及上海對于你散文的意義。
汗 漫:散文就是寫作者的個人史。怎么樣寫作不是問題,怎么樣生活是一個問題——這像一個散文觀嗎?哈哈。的確,散文與其他文體相比,更加真實地反照出寫作者的處境和心境,無法虛構或假設。與小說、詩歌相比,散文可供作者隱藏自我的樹林太小——這是俄羅斯詩人吉皮烏斯一段話的大意。
我所在的這家科研機構,含有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研發中心和上市公司,已有近六十年歷史,1949年前是國民黨的中央工業研究院,解放后一直隸屬于國家部委直接管理,有三位中國工程院院士和一批五十年代從海外歸來的科學家,歷史積淀深,恩怨是非多——我辦公室所在的、英國人建設的一座近百年歷史的保護建筑的地下室內,文革期間,第一任院長在這里含冤自盡。在這家已經轉制為中央企業的單位里工作,個人命運與周圍的人、事、物、情,都必然發生各種摩擦、糾葛。你所提到的那三篇散文,之所以影響比較大,都是因為真實地呈現了我的個人情感、上海生活——我沒有把自己藏在一片樹林里。
冷 焰 :我能夠感受到你在這些散文表達中袒露自我、審視內心的勇氣,感受到你生活中的陰影和疼痛。上海,居不易。在一個單位中得以生存而又堅守內心的原則,更不易。我能理解,你是在用寫作為生活消毒、免疫。
汗 漫:謝謝你的理解。我喜歡蔡文姬的父親、東漢文學家和書法家蔡邕在《書論》中說的一句話:“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散懷抱”,三個字,真好。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重負和隱疾,需要我們以各種形式來散懷抱,喝酒,唱歌,旅行,等等。寫作也是散懷抱。散文更要散,散懷抱,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正是蔡邕,在書法中首創了“飛白”手法——飛動的白,如天風吹海,讓大海散懷抱。
但寫作不是個人日記。所有從“我”開始的寫作,都應該擁有抵達“我們”的能力,從具象凌空而起抵達抽象,這樣的寫作才有意義,有表達價值,有克服時間、空間而得以流傳的可能性。凡杰出的個人經驗表達,都必然能成為觀察一個時代、一類人的氣象云圖。布羅茨基的《小于一》是這樣,本雅明的《柏林童年》是這樣,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也是這樣。
一個人的生活,就是一個不斷寫作、修改中的散文文本。我中年以后的生活、命運與上海有關,散文寫作也必然與這座城市發生關系。但我的上海,與土生土長于這座城市里的本土作家的上海,肯定不同。所以我的寫作應該有自己的價值,它必須誠實、從心、獨到,而非陳陳相因、無病呻吟、言不及義。
一首詩豈能放棄抒情的責任和能力
冷 焰 :你的職業生涯和文字生涯之間、上海與內心世界之間,有一種緊張但不脫節的關系,雙向彼此滋養和輸氧,這也需要一種能力。法國駐中國大使館官員、詩人圣瓊·佩斯,美國一家保險公司經理、詩人史蒂文斯,都是在職業之外業余寫作。對你而言,業余寫作,可能有利于制止一種游離于現實生活的懸浮狀態出現,保持與現實的摩擦關系,對寫作的及物性、張力都是有益的吧?
汗 漫:你說的對,業余寫作是一種有誠意的寫作。寫作與下棋、打牌一樣,是生活的一部分——下棋、打牌也是一種精神勞動,是與內心同在的一種方式。我沒有寫作的優越感。在單位里就是一個經營管理人員,寫公文、開會、說閑話、出差。用本名養活筆名,反過來,筆名也在暗暗盯著本名,使自己不至于在現實中變形得丑陋不堪,持守一個人的基本道義立場。單位里知道我筆名的人不多。個別知道我在寫作的同事問我筆名含義,我說就是狼狽、尷尬、羞愧的意思,大汗淋漓、汗流滿面嘛,大家就一同哈哈大笑。
“汗漫”這個筆名,你知道,還是我在鄧州工作時期取的,來自清朝李漁的《涼州》一詩的啟發:“似此才稱汗漫游,今人忽到古涼州。笛中幾句關山曲,四季吹來總是秋。”“汗漫”,開闊、浩大、自由之意——我覺得,這就應該是詩歌的境界,散懷抱。寫作,就是汗漫游。我以“汗漫”筆名,也以“汗漫”為人生觀。
冷 焰 :我注意到2000年以后、也就是你移居上海以后,詩歌也有很大變化,從最初的意象繁復的抒情性寫作,到現在的意象與細節、書面語與口語、形而下的現實體驗與形而上的沉思——一種綜合性或者說整合性的寫作,似乎開始一種轉型。這與你進入中年、進入上海以及不斷深入的散文寫作,也就是說,與你的種種跨界,有關嗎?
汗 漫:可能與散文寫作實驗有關,敘述性、戲劇性、口語化的因素,開始逐步進入我的詩歌。我希望自己擁有綜合性、整合性的寫作能力。
你知道,在九十年代中國詩壇,我被戴上兩頂帽子:一是鄉土詩人,二是意象詩人。這與我一個時期內以鄉土為背景的詩歌作品比較多、意象創造比較用力用心有關系。這兩頂帽子,是評論者為概括的方便而制作的。我不想戴,因為一個詩人的大腦應該具有抗寒能力,不需要借助任何帽子來取暖或標志自己哈哈。只要有“詩人”這一個稱謂就足夠了。現在,詩壇上的各種帽子滿天飛,多余,而且可疑。我提醒自己:必須開闊、切膚入心、誠實獨到地寫作,跨越題材、手法的藩籬和輿論的喧嘩。
冷 焰 :這些年,詩歌界的種種主義之爭漸漸消失,詩人們回到文本、潛心寫作,是件好事。你則始終處于各種是非、紛爭、圈子之外,沉靜寫作,作品保持了一種抒情品質和人文情懷,很難得。
汗 漫:九十年代,各種探索、流派、命名,眾聲喧嘩,開門立戶。但不論怎樣寫,零度抒情、客觀性寫作也好,口語、敘述性寫作也好,民間寫作、知識分子寫作也好,都必須有一個“我”在場——有“我”在,豈能與“情感”無關?連法庭上的控辯與陳詞都有“憤怒”、“仇恨”在場,一首詩豈能放棄抒情的責任與能力?但我反對并警惕于一切虛偽、泛濫、夸飾、陳俗的情感表達。
《詩經》所決定的抒情傳統,源遠流長,貫通于漢語詩人的血液和呼吸,不管承認與否、察覺與否。詩歌的先鋒意識就是求變求新,但萬變不離其宗——詩歌的抒情本質,沒有變。
等待準確的詞出現在某個位置上
冷 焰 :你最近迷上了街拍?看你總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晃蕩,照片的角度挺別致,讓我想起一批詩人攝影家,比如王寅、于堅等等。記得日本攝影家森山大道說:拿起照相機,我就像雷達張開了器官。
汗 漫:拿起手機我也有雷達開始工作的感覺。我是2015年春開始迷上了手機拍攝,手機像素不高,但許多瞬間捕獲的畫面,讓我驚喜——就像神來之筆啊。現在,周末無事,我會沿著上海一些街道邊走邊拍。在拍照的過程中,加深了對桑塔格、本雅明、巴特、波德里亞關于攝影的種種觀點的理解。的確,攝影就是一種自畫像,被拍攝的對象、畫面,無不暴露出拍攝者的心境和處境——也像散文寫作,藏不住自我。
街拍,使我的觀察方式有了變化。以往大而化之、熟視無睹的事物,在用手機鏡頭逼近的過程中,會有新發現。攝影教會我觀察細節、調整視角,也教會我耐心等待。我曾經在福州路一個弄堂里站了二十分鐘,直到一個抱著鮮花的姑娘掠過弄堂口,按下鏡頭——無限的歡喜!等待一個合適的人出現在空白的位置上,就像年輕時代約會,等待戀人出現在街頭拐角的那個位置上,無限歡喜。也像寫作,等待一個準確的詞出現在詩歌的某個位置上,從而產生力量。也像數學作業——大學數學專業的訓練,對我最大的啟示就是:必須找到唯一、準確的答案,但這依賴于想象力和推理能力,在因果之間建立有根據的聯系——在平面幾何中,只能依靠想象力而增加輔助線,才能破解一道難題。
冷 焰 :文學、數學、攝影學,萬象歸一。手機攝影對你的習作和生活有什么影響?
汗 漫:手機拍攝對我的寫作有啟發、有推動。不久前,我在汾陽路上晃蕩了半天,拍下了一個刺青店、一棵街頭的綠樹、街頭花園里的普希金銅像。回家,扔下手機,寫出一首詩。攝影,大約也是一種寫作,特別像詩歌的寫作——都是通過營造畫面和意味來感染閱讀者。與森山大道、王寅等人的攝影相比,我是亂拍,但有自己的感受蘊含其中,也是好的。街拍,使我發現了“另一個我”的存在,很有意思。
以“簡樸和陌生”為座右銘
冷 焰 :希望你的詩、散文和照片都越來越好,像你的筆名“汗漫”一樣,開闊、自由、獨到。最后,談談你的寫作、出書計劃,哈哈,想知道你準備怎么再跨越一步、兩步。
汗 漫:慚愧,寫作這么多年,只出版了三本書:詩集《片段的春天》,1993年;散文集《漫游的燈盞》,2003年;詩集《水之書》,2009年。
2003年以來寫的散文,算了算,大約有60萬字吧,可以出四本散文隨筆集,初定名為《南方云集》、《一個人的詞語實驗室》、《紙盆地》、《春甕秋瓶》。我也不著急出版,總覺得這些文字還可以修改得更好一些,避免遺憾。
2014年以來詩歌寫得多了,100多首了,還需要打磨,之后再出一本詩集。
冷 焰 :用里爾克的話說,“是時候了”,我們都好好地為自己的內心而生活、寫作吧。期待讀到你更多、更新的跨界之作——跨入新境界。
汗 漫:謝謝你陪我談了這么多,讓我有機會對自己的寫作和生活進行一次回眸。跨界無止境,我們都在跨——現在,咱們都準備開始跨入晚年了。墨西哥詩人帕斯談到阿根廷詩人博爾赫斯的詩歌時說,“他為兩種相反的至高境界服務:簡樸和陌生”——簡樸和陌生,似乎也可以作為晚年生活和寫作的左右銘,與你共勉。
江南詩評
主持人語:
很難用“江南性”來概述葉輝的詩風,其1990年代以來的寫作,量少質優,卓爾不群,構成了對“數量化生產”的反諷,同時因“遠離風尚”的某種“退避”,而將自我的世界擴展到遠方。他的詩,具有純粹的、洞徹的、通靈的、凝神靜氣的品質和力量。何言宏說葉輝的詩“沉迷日常”又“超然觀察”,寫作成為“個體存在論意義上的精神探究”,這是一個敏銳而內行的發現。“我們不妨就用葉輝的詩來喚醒自我,找回自我。”這是詩評家作為顯在的讀者為潛在的讀者說出的一句肺腑之言。(沈葦)
冷 焰 :應《江南詩》詩刊之約,很高興與你這位老朋友做一個訪談,主題是“跨界”。我覺得這個主題很有意思,非常切合你:在教育背景上,你大學讀的是數學專業,工作后與數學毫無關系;在地理空間上,你從故鄉中原移居上海16年了;在個人身份上,你的職業是一家中央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業余寫作成績也不小;在文體上,你因為詩歌寫作而獲得《詩刊》“新世紀(2000年—2009年)十佳青年詩人獎”,因為散文而兩度獲得“人民文學獎”,從而佐證了你的詩人、散文家這樣一種雙重身份。近來又在微信中看你迷上了街拍,呵呵,“手機攝影家”大概又成為你的新追求?所以,你是一個跨界的人、多側面的人,我們又是多年老友,應該對“跨界”這一話題有話可談。
汗 漫:關于跨界這一主題,我想了想,自己大學畢業這些年來,的確是一個跨來跨去的人,無論是地域、職業、寫作文體,還是精神處境,一直在跨界、臨界——界,就是鴻溝、障礙、沖突、疑難。可以說,與職業作家相比,或與那些距離文壇比較近的從業者相比,我是一個在俗世中沉浮的人,寫作、或者說一支筆,就是一根自救的浮木。我的面目可能不那么純粹、雅致,但在世俗生活中反抗庸俗,難度可能更大一些吧,這也許有利于在文字中表現出相應的難度和張力。
捷克小說家克里瑪說:語言和生活經驗不能相脫節,你很難在一種輕松自由的環境中去表達嚴酷的現實。他青年時代當過救護員、郵差、勘測員等職業來謀生,堅持寫作,并在文字中形成一個嶙峋、冷峻的東歐觀察者的形象。我感覺,這些年自己的寫作如果有一些收獲的話,它們恰恰生成于我與文壇保持距離、與人間煙火痛切相關的個人生活,不完美但真實、粗糲。我喜歡陶淵明“心遠地自偏”這句話——選擇一個“偏僻的位置”,有助于一個人的內心走得幽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