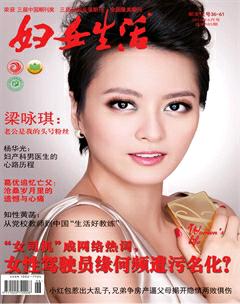張作霖與日本的恩怨糾纏
被日本扶植成為“東北王”,又在皇姑屯被關東軍炸死,這些與日本錯綜復雜、糾葛不清的恩怨,正是張作霖一直飽受爭議的原因之一。
1980年出版的《張作霖》一書在當時被認為是第一本“較為系統、詳細的張作霖傳記”,而在這本書的《前言》中,作者東北師范大學的常城教授如此描述自己記述張作霖一生的目的:“使人們特別是青年同志們具體了解舊中國軍閥黑暗統治的一個側面。”
書中記錄了1912年1月,當時是奉天巡防營前路統領的張作霖訪問日本駐奉總領事落合的情景。在會面時,張作霖表達了與日本合作的愿望。他對落合說:“我深知日本在滿洲有許多特權,日本如果對我有所吩咐,我一定盡力而為。”
在知名歷史博主薩沙的《民國最成功的馬匪張作霖》一文中,薩沙透露了這樣的細節:張作霖在各種場合表達親日立場,多次鎮壓東北的抗日運動,在經濟上也有諸多妥協。作為回報,日本在1916年通過朝鮮銀行奉天支行貸款給張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張作霖在沈陽窮途末路,只剩1萬多人,甚至已經考慮放棄東北逃亡。日軍偷偷出兵助攻,派了1萬人防御沈陽,又派遣一個師團突擊正全力攻擊沈陽的郭松齡軍團的后路,而這也直接促使張作霖日后與日本簽訂了《日張密約》。
“對張作霖這樣的反動軍閥,既不能稱之為‘豪杰之士,也不能看作反日的‘英雄。他的一生,是反動的一生,禍國殃民的一生。”在《張作霖》一書中,常城如此總結道。
許多學者對這種觀點并不認同。歷史學者丁雍年于1982年5月在《求是學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對張作霖的評價亦應實事求是》的文章,文中補充了一些張作霖對日本交涉的細節,證明張作霖“是不甘心當漢奸出賣東北的”——1927年10月15日,日本逼張作霖簽訂關于五條鐵路的密約,張作霖僅僅批了個“閱”字敷衍了事。在利用日本掌握東北后,張作霖對日本也一直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這讓日本方面很不高興。日本參謀部中國部部長松井石根曾背地里議論他:“這個家伙難弄得很,始終不聽話。”
“一直對日軍保有一種土匪式憤恨”——這是薩沙關于張作霖內心對日本真實態度的描述。如此結論來自于張作霖當時同日本的一次針鋒相對——與日軍同盟時,張作霖的軍營駐扎在距沈陽100多公里外的新民府。他手下的兵在逛沈陽的日本妓院時與日本兵斗毆,寡不敵眾被打死了兩人。張作霖大怒,找到日本方面要求殺人償命。日本軍官依照慣例,一人賠償了500兩銀子。張作霖拿了1000兩銀子回去后,召集手下上街打死三名日本兵。他的士兵都是剛被收編的土匪,當即沖上街頭,找了三個日本兵毆打致死。當日本軍官怒氣沖沖地前來質問時,張作霖甩出1500兩銀子說,這是“按照你們的慣例”。
臺灣“中央研究院”學者梁敬 描述:“日本對張作霖,怨悅交并。張作霖對于日本,雖甚富友誼,然日本欲其出賣國家,則非張作霖所能忍受。”戴振毅在《試論張作霖與日本人的關系》一文中記錄的另一件事也足以說明這一點——日本派公使芳澤與張作霖商談“解決蒙滿諸懸案”問題,在交談中張作霖頻頻推脫裝糊涂,芳澤恫嚇說濟南死了13個日本僑民,張作霖需要對此負一切責任。根據周大侖《張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親歷記》中回憶,張作霖當時勃然大怒,立即由座上站起來,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煙袋猛力地向下一摔,磕成兩段,聲色俱厲地對芳澤說:“此事一無報告,二未調查,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種叫我子子孫孫們抬不起頭來的事情。”怒罵日本公使后的第16天,1928年6月4日凌晨5點30分,張作霖被關東軍炸死在皇姑屯。
張作霖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英國學者加文·麥柯馬克在《張作霖在東北》一書中的說法或許可以作為答案之一:“張作霖比一個純粹的傀儡還多些什么,但卻比一個民族主義者少些什么。”
(摘自2016年第2期《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