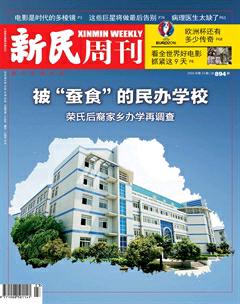那才是真正的墮落
黃夏
墮落的本質,就是逆著自己的天性生活。
《卡羅爾》折戟今年奧斯卡。有評論說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戀合法之后,此類電影就失去了話題性,奧斯卡當然不愿意多提它了。殊不知最高法院乃美國政府中唯一不代表民意的機構,而奧斯卡那班平均年齡奔七的老爺爺更不會先鋒開明到為其加冕,他們永遠只會把獎頒給如《聚焦》這樣略嫌沉悶但準確體現美國主流價值觀的影片。
事實上,美國的主流價值觀一直十分保守。早在1928年,被譽為女同性戀小說開山鼻祖的《孤寂深淵》便因“淫穢”同時在英美被禁,英國后來在1949年開禁,而美國直至1975年才解禁。1951年,《卡羅爾》原著作者帕特里夏·海史密斯在幾經周折之后,終于順利出版了這部作品(易名《鹽的代價》)。《卡羅爾》之所以比《孤寂深淵》幸運,主要在于作者在處理有關情節(jié)時不似后者那樣“真實、坦承、無畏”,而是以各種曖昧筆法調和之,同時還柔化了同性戀和女權主義的權力伸張,使之不至于太過鋒芒畢露。
這種筆法上的柔軟也營造了一種極具心理張力的敘事氛圍。因為作家首先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即在一個多數人對同性戀比較反感的年代,如何讓兩個女人在不過分暴露自己的同時,又能成功地讓對方嗅出自己的好感。為此,海史密斯塑造了一對性格迥異的主人公,初出茅廬的特芮絲和老練腹黑的卡羅爾,讓她們因應著各自的特質,在逐愛的危險游戲中編織起一張明爭暗斗的權力之網。沒錯兒,這是一場激烈交鋒而不形之于表面的博弈,雙方在收獲滿滿的愛情之前,付出的是辛勞的汗水、心計和勇氣。
于是,我們看到,稚拙如特芮絲這樣的姑娘,也會有將自己豁出去、將燙山芋丟給對方的“急智”。她初訪卡羅爾家,喝卡羅爾煮的牛奶,“就像喝下童話里會變身的藥水一般,也像毫不起疑的戰(zhàn)士喝下致命的毒酒一樣”,是死是活,就全憑可心的人兒看著辦吧。而卡羅爾呢,則從煮牛奶起便手指發(fā)顫、心焦如焚,但仍能坐懷不亂按兵不動。她把這個燙手山芋重新扔回給特芮絲,不但不作一點表示,反而氣定神閑地引介她的另一女性好友艾比,如執(zhí)狗尾巴草挑逗喵星人那樣地挑逗著特芮絲。
如果說,《卡羅爾》前半部主要是情人間欲擒故縱的愛情博弈,充滿機心和懸念,那么后半部則主要聚焦于刀刀見血的“道德”圍攻,文本上的表現力雖遜于前半部但仍有可圈可點處。海史密斯在處理道德問題上可謂運足了功夫,她成功地證明了“同性戀不道德”這樣的觀點本身就是不道德。譬如,將同性戀者強迫納入異性戀婚姻的軌道只能給卡羅爾及其丈夫帶來不幸,丈夫后來利用卡羅爾和特芮絲的愛情來訛詐妻子更表明了某些異性戀者的偽善。而包括特芮絲男友理查德在內的男人們如此仇視女同性戀,則暗含著男性認為占有女性乃其天賦權力的古老成見。并且,他們在與女伴的交流中,又大多以“自己的行為能否制造出小孩”這樣狹隘的標準來衡量兩性關系的和諧愉悅。
不過,《卡羅爾》真正令人動容的力量并不在于作者為同性戀和女權主義發(fā)聲,而是為一個遠遠超越上述兩者、為作為一個“人”的尊嚴所必需的那些東西搖旗吶喊。當人們指責卡羅爾將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時,海史密斯借她之口說:“如果我繼續(xù)這樣下去,持續(xù)受到監(jiān)視,持續(xù)被人攻訐,永遠無法長時間擁有一個人,到頭來我對其他人的認識都只是停留在表面,那樣的情況才是真正的墮落。或者說墮落的本質,就是逆著自己的天性生活。”
放在今天,我們或許可以用“意志”進一步取代“天性”,來決定自己的生活,而這正是人之為人最起碼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