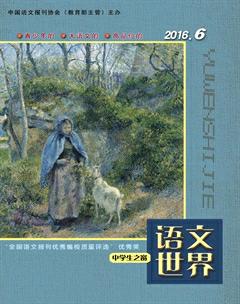用文學溫暖世界
李嘯聞
筱敏的散文是哲學散文,但每一篇又都只像一塊哲學的碎片。她并不信仰任何一種哲學,于是掰開克羅齊表現主義的一角,截下柏格森生命之流的一段,或者沉浸在弗洛伊德潛意識的睡夢里,或者干脆棲居在海德格爾的詩意中……而在這些殘折的哲學邊沿,分明擁簇著嶄新的思考之芽,吐露著頑強的黏著之力,抱合成一種立體的、抽象的、個性的哲學。筱敏的散文本非探究哲學的,但又產生著一種能使人默許的終極意義的力量,無意中又令人會意,懷疑的坐標正指向答案,在沉重的懺悔中獲得釋懷。
我們總抱怨說現在的生活太累,于是拒絕有分量的東西——比如思考的文字。但我們所累的卻不是沉重,而是忙碌于擁擠;不是思考,而是輕浮與煩躁。我們不愿思考似乎無解的問題,比如誰在奴役我們;我們不愿正視曾經遭受的苦難,比如誰發動了戰爭;我們不愿計算一生到底有多少需求;我們不愿寬恕他人的過失……筱敏的散文先是用溫柔的文字輕輕扳過我們扭到一邊的頭,說:“看哪,你看哪,這就是你自己!”然后又用鏗鏘的詞章沉沉叩問我們麻木的心靈:“來吧,開始做,現在就開始做!”先自省,再改過。思考吧,哪怕沒有答案;前行吧,哪怕沒有道路;行動吧,哪怕沒有終點……
我相信最堅韌的人應該到用文字譜寫生命的人中去找,因為他們用來面對世界的工具是最脆弱無力的東西。筱敏知道文字本身什么也不能做,但她對自己的文字苛刻到殘忍。在她筆下,舒展的美景中,生命痛苦地縮成一團;喧鬧的人群里,心靈孤獨地死寂一片;個體遭遇的是清醒,群體面對的是混沌;英雄的宿命是死亡,懦夫的皈依是安樂。她是如此善造古希臘的悲劇,她讓最美麗最柔弱最純潔最崇高的靈物被摧殘被凌辱被玷污被踐踏;她是如此善于在生命的高音區,在那根最細最緊的弦上風疾電掣般撥動華美的樂章!她是個用反色來彩繪世界、用落差來尋找平衡的人,她達到了:她寫《捕蝶者》,用死亡來呼喚對生命的敬畏;她寫《人牲》,用祭壇上的血污清洗的心靈更純澈,她用疼痛讓人們恢復知覺,她用黑暗讓人們發現光亮,她用冷風讓人們回憶溫暖,但她又總是優雅而憂郁的。雖然文章的骨骼里有一股丈夫的魄力,但精韻中還是散發著獨屬女子的悲憫。這悲憫,是對人類生存的寬容,如大地一般繼續貢獻著她的肌體與乳汁,等待著人類覺醒那個無期的許諾。康德在乎的是心靈與星空,而與女子相牽連的應該是心靈與大地吧。
也許每一個寫作的人對自己的文字都不能有太多期待,這是一生的致力和執著與最終效果的悖論。但每個讀過筱敏的散文的人,至少可以記得被我們自己空洞的目光遺漏的角落中的弱者,譬如乞人、鞋匠、搬運工……下次見到他們不再鄙夷,最好還能微笑一下,他們會感到很溫暖。于是世上的溫暖就這樣一點一點地積存下來了,世界就這樣一點一點地變得溫馨了。
(選摘自《文藝報》2007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