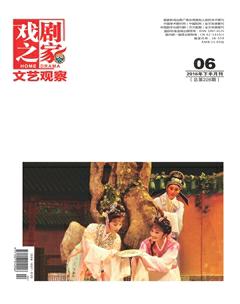廚房水槽間的理想與幻滅:淺析阿諾德·韋斯克三部曲中的創傷書寫
馮鶴
【摘 要】阿諾德·韋斯克的代表作“韋斯克三部曲”是對戰亂生活的自傳性書寫。本文從“卡恩夫婦的創傷防御”“貝蒂假想的創傷隱喻”和“艾達夫婦的創傷逃避”三個層面入手,對韋斯克三部曲中主人公的心理創傷進行解讀。 【關鍵詞】韋斯克三部曲;創傷;理想;幻滅中圖分類號:I10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6-0014-02作為新現實主義戲劇浪潮的代表人物,阿諾德·韋斯克筆耕不輟,其作品廣受海外讀者歡迎,然而近十年才引起英國本國戲劇界的充分認可。韋斯克的成名作“韋斯克三部曲”的首場演出便因其注重寫實的特點而與《憤怒的回顧》一同被冠以“廚房水槽劇”的稱號。”[1]“廚房水槽劇”素來以激進現實主義描寫工人階級的灰暗生活著稱。三部曲的時間跨度長達二十三年,以倫敦東區猶太工人階級卡恩一家為代表,深刻反映了英國工人階級群體所經歷的戰爭歷程。“韋斯克直言三部曲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傳作品,除了《我在談耶路撒冷》中憤世嫉俗的多布森外,所有人都是他生活中的真實存在。”[2]三部曲是三段理想幻滅的歷程,展現了卡恩一家深受戰爭創傷的折磨。弗洛伊德認為:“一種經驗如果在短期內,使心靈受到最高程度的刺激,以致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這種經驗稱為創傷。”[3]本文從創傷的角度對三部曲進行具體解讀。一、卡恩夫婦的創傷防御三部曲的首部劇《大麥雞湯》記述了1936年法西斯軍隊進入倫敦東部猶太人居住區,卡恩一家積極加入政治斗爭但遭受理想破滅的歷程[4]。卡恩夫婦應對戰爭創傷的過程中,分別采用了壓抑和投射的防御機制。“防御機制是自我用來降低本我和超我之間沖突的一種無意識方法,是個體處理沖突和壓力的手段。”[5]哈利·卡恩在超我的控制下,將本我的戰斗熱情壓抑下去,從而避免其對戰爭的焦慮。小說伊始,哈利與薩拉的對話火藥味十足,作家萬德從性別的角度對卡恩夫婦的關系進行了闡述,她指出“三部曲是《憤怒的回顧》中男女關系的反轉,但無論哪一方更強都是以另一方的沉默為代價。”[6]正如《大麥雞湯》開場部分,薩拉對哈利咄咄逼人的態度:薩拉:海米來了嗎?哈利:我不知道。薩拉:他一問三不知!你沒有問他嗎?他沒有說嗎?他知道游行吧?哈利: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也沒有和他討論過。我帶去了孩子,沒別的,嘿,薩拉,你應該讀讀厄普頓·辛克萊的書,關于肉罐頭產業,這是開眼界的……[7]13哈利的壓抑作為一種防御機制,被壓抑的記憶具有創傷性質,盡管被隱藏,仍然產生影響。他閱讀厄普頓·辛克萊的書籍,對針砭時弊的作品產生共鳴,可見哈利人格中的本我與妻子薩拉為理想奮斗的熱情一致,但是人格中“超我”在心理斗爭中占上風,哈利提醒薩拉游行時不要傷人并教導兒子羅尼愛他人。劇中多次出現哈利閱讀的場景,一方面說明哈利熱愛書籍,另一方面說明他試圖通過書本將自己與戰火紛飛的外界隔絕開來。戰爭的焦慮被哈利壓抑在心底,放棄抗爭而過行尸走肉的生活。妻子薩拉與哈利相反,她全力投身于政治斗爭,通過投射的防御機制使自己免于戰爭創傷。高昂的政治理想是薩拉得以存活的動力,她瘋狂地抓住政治理想這根救命稻草來填補空虛的心靈。她說“她要強迫自己要有所在乎,什么都不在乎就會死亡。”[7]76表面上,她把內心的戰爭恐慌和焦慮投射到拯救全社會的政治斗爭中,實則是利他性質的妥協。哈利·卡恩極力抑制自己對戰爭的熱情,在妻子兒女紛紛加入游行時變得冷漠決絕。在《大麥雞湯》結尾處,薩拉對生活的感覺只剩下挨冷受凍、同胞死傷,二人的防御機制在混亂的戰爭中于事無補。由此可見,作者對他人遭受戰爭創傷的痛苦感同身受,對戰亂中人民悲慘遭遇的深切同情。二、“貝蒂假想的創傷隱喻”三部曲第二部劇《根》中,出生于諾福克鄉村的主人公貝蒂從倫敦回鄉探望家人,與男友羅尼約定兩周后在家中會合。雖然爽約的羅尼從未在場,卻勝似在場,因其女友貝蒂回鄉后,時刻重復羅尼的言行,用羅尼“先進的思想”教化自己“落后的家人”。貝蒂兒時的創傷使她迷失自我,只有徹底擺脫羅尼的影響,才能找回自己的身份。《根》中韋斯克用大量筆觸描寫貝蒂所提出的假想,假想的場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使其心靈創傷和自我發現的愿望得以充分展現。貝蒂假設“河流兩側分別有兩個小屋,其中一側的兩個小屋里分別有一個小女孩和一個聰明人,另一側是另外兩個男人。”[7]139四個小屋暗喻貝蒂的現實生活,小女孩和聰明人是貝蒂自己性格的兩面,而另一側的兩個男人分別是貝蒂的家人和男友羅尼。“貝蒂穿過河流是現實中她去倫敦,是試圖與羅尼結婚的象征,但是她被無情拒絕,絕望中她重返聰明人的小屋,回歸了獨立的自我。”[8]貝蒂向家人提出假想,并詢問誰應該為夢中小女孩的困境負責時,父母和姐姐的回應是一片漠然。可見貝蒂的家人無力或忽略了對貝蒂心靈的關注,在心靈遭遇創傷的情況下,貝蒂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成為羅尼的復制品。另外,當羅尼的家人討論政治理想,突然轉向貝蒂尋求看法時,一問三不知的貝蒂陷入瘋狂的痛苦,從此也可看出貝蒂兒時缺失關愛的心靈創傷。現實中的貝蒂成功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從其發聲的實際意義上看,貝蒂未能找回自己的身份。貝蒂雖然在劇末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象征被政治改變的身份與無政治意義的家庭身份之間的妥協。但貝蒂的發聲與她家人具有同樣的特征,貝蒂沿用了母親的表達方式。此外,“貝蒂的發聲是從集體主義中抽離進入極端個人主義的行為,使整個三部曲陷入令人窒息的絕望。”[9]由此可見,貝蒂心靈創傷的治愈,象征卡恩一家集體主義的政治理想的幻滅,貝蒂的自我發現把政治理想帶入戲劇化的僵局之中。甚至有評論家認為韋斯克在他的左翼分子群體中,既沒有堅定的集體主義信念也不信奉工人階級[10]。韋斯克通過賦予貝蒂假想深刻的創傷隱喻,傳達出貝蒂創傷的治愈與政治理想幻夢之間的必然聯系,暗示了三部曲中理想走向幻滅的必然性。三、艾達夫婦的創傷逃避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劇《我在談論耶路撒冷》,記述了艾達、戴夫夫婦二人歸隱諾福克鄉村的歷程。艾達和戴夫都曾親赴戰場,目睹了戰爭的殘酷與荒謬,產生了逃避創傷、歸隱鄉野的愿望。然而二人的努力以失敗告終,無奈重返倫敦。艾達與母親薩拉一樣,把不切實際的政治理想作為人生目標,熱衷于游行反抗,但她花了數年等待男友從戰場回來,身心俱疲。戰爭創傷使艾達對生活心灰意冷,選擇逃避現實的道路。戴夫是一個悲哀的和平主義者,無奈之下被卷入殘酷的戰爭。劇中三個法西斯逃兵逃到了戴夫的隊伍,為了攻克寡婦和孤兒們壘成的高山,法西斯損失慘重。蒙蒂希望更多的法西斯士兵死亡,而戴夫則認為“當一個士兵被命名為法西斯,射殺他并不會有快感,而是惡心。”[7]22戴夫不會從消滅敵人的行為中獲取快感,這是他厭惡戰爭的心理和其悲天憫人的情懷,也是戰爭在他內心深處留下的巨大創傷。然而,艾達和戴夫歸隱行動的失敗儼然是更大的諷刺,他們終歸無法擺脫抹殺他們特性的工廠。劇名《我在談論耶路撒冷》本身是一種諷刺,弟弟羅尼一再強調自己談論的是耶路撒冷,并用圣經中美好場景來比喻姐姐艾達即將體驗的鄉下生活,戴夫會像摩西一樣使以色列變得強大,但這一切都成了泡影,艾達和戴夫的生活與想象大相徑庭。作者通過戴夫的話語揭露自己對戰爭本質的認識,他痛恨法西斯的同時卻對法西斯士兵的命運寄予同情,提醒人們戰爭的本質是人類同胞之間的自相殘殺。四、結語“韋斯克三部曲被部分評論家視為一系列說教式戲劇,然而三部曲的確蘊含了普適的主題和契科夫式的藏于話語內部的精神內涵。”[11]通過描繪劇中人物種種努力的失敗,韋斯克對底層人民的戰爭創傷寄予了深切同情,同時對戰爭的本質進行了深刻反思與批判。小說以高昂的政治理想開始,卻以逃避現實的失敗告終。由以上論述可知,《大麥雞湯》、《根》和《我在談論耶路撒冷》三個題目本身都是人物經歷理想幻滅的戰爭創傷的象征。三部曲作為韋斯克自傳性的戲劇,是他親身經歷的再現,作品的藝術價值之余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參考文獻:[1]Lacey, Stephen.Brithish Realist Theartre:The New Wave in Its Context 1956-1965[M].London:Routledge,1995.[2]Rothberg, Abaham.Waiting for Wesker[J]. The Antioch Review,1964.[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4]許小凡.自相矛盾的現實主義[D].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2012.[5]Imtiaz Jehan,et al.Ego Defense Mechanisms In Pakistani Medical Students:Across Sectional Analysis[M].BMC Psychiatry,2010.12-19. [6]Wandor, Michelene. Post-War British Drama: Look Back in Gender[M]. London:Routledge,2001.[7]Wesker, Arnold.The Wesker Trilogy[M].England:Penguin Plays, 1964.[8]Stevens, Mary.Wesker‘s The Wesker Trilogy[J].Colorado:University of Colorado,2002.[9]Rebellato, Dan.1956 and All That: 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ish Drama[M].London:Routledge,1999.[10]Sinfield, Alan.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Posstwar Britain[M].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1]Adler, Thomas P.The Wesker Trilogy Revisited: Games to Compensate For The Inadequacy of Word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79.作者簡介:馮 鶴,大連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