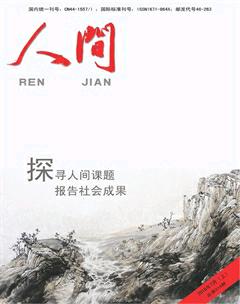從《懷麓堂詩話》看李東陽“詩歌音律”觀
劉明哥(云南民族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
從《懷麓堂詩話》看李東陽“詩歌音律”觀
劉明哥
(云南民族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詩與音樂有著天然而密不可分的關系,李東陽繼承前人的詩歌理論,著眼于詩歌藝術本身,注重詩歌的內在審美特征,其《懷麓堂詩話》凝結了他的詩學理論,其中詩歌音律貫穿了他詩學觀的主線。
關鍵詞:懷麓堂詩話;“詩歌音律”觀
一、詩與樂律
李東陽在《懷麓堂詩話》當中所涉及樂律的條目主要講了兩個方面,一是音樂之聲、二是樂之節奏。
(一)音樂之聲。
李東陽認為“聲”是詩歌音樂性的突出表現,通過“以聲論詩”形式,強調詩歌的音樂性,突出音樂性為詩之所以為詩的本質所在。《懷麓堂詩話》云:
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為最優,蓋可以兼眾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為宮,韓退之之詩為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于詩,不過心口相語,然不敢以示人。聞潘言,始自信以為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于自然者,固不約而同也。[1]
可知,李東陽非常認可詩有五聲且宮聲為最優的觀點的。所謂“五聲”即宮、商、角、征、羽等五音。《漢書·律歷志第一·上》亦有記載:“宮,中也,據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2]五聲之中,宮聲最為鏗鏘有力,能兼眾聲,故有正聲之稱,李東陽對發現詩歌中“聲”頗為自負,李東陽的“以聲論詩”說源于此。李東陽還進一步認為“聲”應該包括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懷麓堂詩話》云:“今之歌詩者,其聲調有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之異,聽之者不問而知其為吳為越也”。[3]
因此,李東陽對詩歌之“聲”的重視,主要是突出詩歌的音樂美,實際上是對音樂作為詩歌本質屬性的強調。
(二)音樂節奏。
節奏,是李東陽在《懷麓堂詩話》論述音樂是詩歌本質性的又一個表現特征。
李東陽認為,長篇的詩歌必須突出其節奏,沒有節奏的變化,長篇的詩歌見落入模板,索然無味,需要節奏來變現詩歌的波瀾,而富有韻味。他認為詩人當中杜甫做的最好,杜甫的詩歌以“沉郁頓挫”著稱,李東陽提出“宗唐”,其實就是要學習杜甫。李東陽同時也認識到古詩歌的節奏與現在不同,究其原因,古詩歌節奏已經失傳很久了。如《懷麓堂詩話》云:“古詩歌之聲調節奏,不傳久矣。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諸詩,不過以四字平引為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節”。[4]
在李東陽看來,詩歌必須有節奏的,即須有“高下緩急之節”,因為有節奏,所以詩歌便可歌可詠,即有了歌頌的特點。李東陽想要達到使自然的“人聲和”升華為藝術的“樂聲和”,這是對詩歌音樂性認識深化的體現。
二、詩與格律
格律本來自音樂,在音樂散佚后,經研究者總結古詩歌的共同規律,便形成了今天看到的格律。李東陽認為音韻是詩之音樂性的具體體現,詩不出于自然的抑揚頓挫的和諧音聲也就失去了音樂性,這表明李東陽“與樂判而為二”的不滿以及對詩歌音樂美的追求。但是即便李東陽對“與樂判而為二”,只遵守格律的窠臼極力反對,但他也在他的詩學觀中強調了這兩者的相關性。詩詞格律一般有四大要素即用韻、平仄、對仗、字數,雖然用韻屬于格律的范疇之內,但在《懷麓堂詩話》中,用韻確是與詩的音樂性分不開的。
在李東陽看來,“韻”是詩歌音樂性的一個重要的表現,如果詩歌中用“韻”不穩,則會危及到詩句的成功生成,所以能不能善用“韻”直接關系到詩歌整體的成功與否。因此,李東陽十分注重“詩韻貴穩”,要求詩歌要有可歌頌性,以“具耳”聽之,要能給人以美得享受。此外如《懷麓堂詩話》第七八則“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華宮》《哀江頭》諸作,概亦可見。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為趫健,似別出一格。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弱無生氣。自后則韓退之蘇子瞻有之,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偶一啟鑰,為知音者道之。若用此太多,過於生硬,則又矯枉之失,不可不戒也”。[5]也是強調了用字用韻及音調的變化對于詩歌的影響。
而對于屬于格律范疇的諸如對偶、平仄、字數等等,李東陽則認為不必拘泥于此。對于詩是否應拘于格律,前人也有論述,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十《詩一·綱領》提到:“《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個與天通”,又在《禮四·總論》中說:“陳(宜中)問:‘古詩有平仄否?’李(漢老)云:‘無平仄,只是有音韻’龔(實之)大然之。謂之無有皆不是,謂之音韻乃是”。李東陽對此也有詳細的表述:
“律詩起承轉合,不為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為之,則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閑習之馀,或溢而為波,或變而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強致也”。[6]
李東陽認為律詩的寫作可以依照已定的格律,但切不可拘泥于格律的套路之中,詩歌需有自然之妙,而非強制而為,他反對“泥古詩之成聲,平側短長,句句字字,摹仿而不敢失”。[7]強調“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尤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易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乎是,亦未可與言詩也”。[8]
總而言之,“詩歌音律”是貫穿《懷麓堂詩話》的主線,李東陽強調詩歌的本質在于音樂性,在他的詩論中,詩歌回歸于本來的面目,他肯定詩的音樂性,提高了詩的藝術性,使詩歌不但有語言文字上的意義,更推動詩歌恢復到具有音樂本質的藝術作品當中。
參考文獻:
[1]李東陽著,李慶立校釋.懷麓堂詩話校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64.
[2]鄭玄,賈公彥.周禮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690.
[4][5][6][7][8]李東陽著,李慶立校釋.懷麓堂詩話校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108,203,102,20,20.
中圖分類號:I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7-0052-01
作者簡介:劉明哥(1991-),男,河北唐山人,云南民族大學2014級中國古代文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