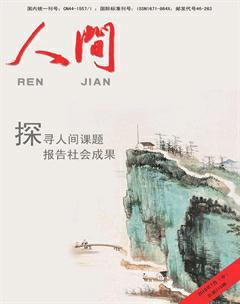從“他者”到“主體”:“小妞電影”的女性意識突破
劉亞群
(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24)
?
從“他者”到“主體”:“小妞電影”的女性意識突破
劉亞群
(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24)
摘要:相較于這種“絕對女權”的電影,“小妞電影”的挑戰似乎柔和了許多,也更容易為大眾所接受并理解。本文從分析“小妞電影”的特色出發,探討女性主義電影中從“他者”到“主體”的女性身份的轉變與女性意識的突破。小妞電影”的挑戰似乎柔和了許多,在將女性從“他者”轉移到敘述空間的“主體”地位時,不采用過激的言論和行為指責或挑戰男性,常常采用幽默輕松的故事情節與男性共存于敘述空間之中,變被動的塑造為主動的構建,探討的是一種二元共生而非二元對立的對話模式。
關鍵詞:他者;主體;小妞電影;女性主義;女性意識;女性電影
引言
如何擺脫女性在電影中的“他者”處境,恢復女性真正自主的自我身份,成為女性主義電影所關注的重點,即如何建構電影影像中的女性。可以說,西方女性主義電影對“男性他者”文化的解構是不留情面的對立,“是以一方使另一方屈服甚至毀滅另一方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進行的。”相較于這種“絕對女權”的電影,“小妞電影”的挑戰似乎柔和了許多,在將女性從“他者”轉移到敘述空間的“主體”地位時,不采用過激的言論和行為指責或挑戰男性,常常采用幽默輕松的故事情節與男性共存于敘述空間之中,變被動的塑造為主動的構建,探討的是一種二元共生而非二元對立的對話模式。
一、女性為主體的敘述視角
“小妞電影”是近年來在好萊塢流行的一種新興電影類型,但是它的源頭可追溯到1961年由奧黛麗·赫本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這類電影類型在美國已經有50多年的發展歷史了。早在婦女解放運動時期,“chick”一詞被認為是對女性的一種侮辱與貶低,被看成是男性的附屬。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于1929年就寫出了一篇抨擊無處不在的性別歧視現象的論文——《自己的屋子》,指出如果女性想要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社會前提條件。隨著小妞電影中突出女性主題文化形態的出現,人們漸漸開始關注女性文化。以往的主流電影多數以男性作為敘述中心,女性在電影中一直處于被動地塑造的地位,真實而完整的女性往往在電影中的塑造是空白的。作為以父權制為主的傳統敘事結構中,女性長期處于被動階段。然而,小妞電影將女性設置為敘述空間的中心,女性作為第一敘述視角,以輕松、俏皮、時尚的言語來表達女性在生活中獨特的生命體驗,以此體現出女性的欲望和主觀能動性,使女性不再是熒幕上被壓抑的“他者”。例如,安妮·海瑟薇主演的《公主日記》,主人公米亞本是高中里一個默默無聞、存在感為零的女生,長期沒有人關注使她非常自卑,甚至都不敢對喜歡的男生表白。然而突然有一天,當她知道自己是一個國家的公主,并努力改變了自己以后,她慢慢變得自信起來,最后收獲了榮譽與愛情。同樣由安妮·海瑟薇主演的時尚電影《穿普拉達的女王》中,主人公安德莉亞本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職員,她土里土氣,沒什么本事,與同齡的年輕時尚女孩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然而當她到了時尚雜志并成為主編米蘭達的助理以后,她開始漸漸蛻變,不僅人變得美麗時尚,以往被人忽略的聰明才智也漸漸得到了用武之地,最后她同樣是收貨了愛情與事業。
二、“看與被看”的重新書寫
女性的審美意識是流動和變化的,它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經濟、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一種特定時期的文化現象。20世紀80年代至今,隨著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一時期的審美變得多元化,女性的審美價值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一時期,媒體、社會輿論導向于注重渲染外在審美,基本忽視了當代女性的內在美,摒棄了當代女性具有的知識、才華和頑強、獨立的特性,一級女性依靠自身學識最終事業有成的情況。可以說,21世紀以來的新女性“已經從被動、服從變成了主動、征服”,女性的審美逐漸開始帶有強烈的主體意識,挑戰傳統審美取向。因此,在多元的文化形態下,小妞電影中獨具時代特色的女性形象應運而生。例如《布魯克林》中用于追求夢想、只身前往布魯克林的愛爾蘭女孩艾莉絲;《結婚大作戰》中的事業型女人麗芙以及艾瑪;國產電影《杜拉拉升職記》中專業干練的HR經理杜拉拉;《失戀33天》中婚慶公司高端婚慶策劃的大齡女青年黃小仙等等,都是極具時代特色的女性形象。從這些角色的定位上來看,可以發現小妞電影選取的女性主角均是占當今社會主體的年輕大齡女白領,她們大大咧咧且又脆弱敏感、獨立自由且又渴望愛情;她們時尚又自信、個性張揚又固執,且都或多或少有著復雜的感情困惑。正式這種當下時代多數都市知識女性的普遍真實寫照,為小妞電影吸引力大批忠實的女性觀影群體。
“男性觀看/女性被看”最早是約翰·伯格1972年在解讀歐洲裸體畫時提出的,伯格指出“女性自身的觀察者是男性,而被觀察者為女性”。1975年美國電影理論家勞拉·穆爾維的《視覺快感與敘事性電影》,將“女性被看”的觀點引入電影學界,“在一個由性的不平等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為主動的/男性和被動的/女性。起決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風格化的女人形體上”然而,小妞電影卻一反以往男性主權的電影,采用的是“女性觀看/女性被看”的模式,女性不僅僅成為電影的第一敘述視角,也成為了電影的主要觀影受眾。女性觀影受眾在小妞電影中更容易產生共鳴,她們沒有《末路狂花》中塞爾瑪的亡命天涯的生活;也少有或沒有《卡羅爾》中卡羅爾對于同性愛情的大膽追求與放棄;更沒有《消失的愛人》中艾米為了逃避婚姻與報復丈夫所設計的陰謀。她們有的只是身處當下社會所產生的由社會壓力帶來的學習、工作、愛情以及婚姻的苦惱而已。她們需要別人的感同身受與精神共鳴,需要對于壓力的消解與緩解壓力的放松,更需要解決問題的決心與勇氣,恰恰小妞電影為她們建構了這樣一種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她們從電影中產生了共鳴,將電影中女主人公的“麻煩”帶入到自己的身上,并伴隨著女主人公最后的成功,給予自己莫大的勇氣,給予自己解決問題的希望。
三、“對話男權”的二元敘述空間
無論是男性統治女性還是女性統治男性,都是片面的過激行為。而解決女性自由的重要途徑就是擺脫以往消極無為的思想,積極得投入到生活中去,肩負起個體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既不依附于男性,也不統治男性,而是與男性共同面對生活的困境。這種二元敘述空間并非單純過激的二元對立,而是二元相生相融的和諧空間。只有香型相互支持、和諧共處,才應該是女性甚至男性實現自由、幸福生活的有益出路。由此可見,小妞電影的受歡迎程度正是反映了“當代的文化特征和年輕一代的審美需求,遵循讓女性快樂的原則,滿足女性的欲望,關注女性價值、消費,貼合主流消費群體的生活觀念和價值標準。”這種看似平民化的價值標準,才是最能牢牢抓住大眾,特別是女性受眾的樸實的普世價值觀念。
許多女性主義電影產生了一種過激的悖論,認為男人與女人是絕對對立的,通過人為地設計,讓女性對男人世界進行宣戰。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女性形象和題材的書寫,振奮且鼓舞著存在于不平等的壓迫環境下的被動女性,然而,不少此類影片中男性的“無能”,“仿佛又在有意無意地規避性別意識的自覺與性別無奈的矛盾,以致始終未能真正塑造出在男權中心的世界里,應如何爭取自己應有的政治、經濟和身份的合法地位極其話語權的女性映像。”
結語
總而言之,目前很多描寫女性題材的電影仍然是從女性主義或女權意識的概念出發,而非真正來自生活,很多希望在女性話題上有所突破的導演,也僅僅只是從女性主義批評理論中照本宣科,或直接創作IP電影作品,缺乏對現實生活中各種不同類型、不同身份、不同社會角色的女性的深切體驗,結果導致無法擺脫男性看/女性被看的敘述模式,或者生硬地去表現性別權利的表層化的女性主義模式。此外,小妞電影還跳脫出了傳統的“看與被看”的二元對立的俗套,在男女平等的參照系中建立女性獨特的話語權,展現女性的獨立品格,從平淡中體味女性話語權與女性主義意識。
參考文獻:
[1]章旭清:《“他者”與“解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關鍵詞解讀》[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羅婧婷,李帥:《基于中西文化視野的中國小妞電影》[J],《中華文化論壇》2014年第2期。
[3](英)約翰·伯格:《觀察之道》,戴行鉞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美)勞拉·穆爾維:《視覺快感與敘事性電影》,周傳基譯,載張紅軍編《電影與新方法》,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
[5]邵雯艷:《從獨語到對話——當下女性電影創作的美學專向》[J],《當代電影》2014年第2期。
[6]金丹元,曹瓊:《女性主義、女性電影亦或是女性意識——重識當下中國電影中涉及的幾個女性話題》[J],《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
中圖分類號:J9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7-0191-02
作者簡介:劉亞群(1990.4—),女,漢,山東濟南人,碩士研究生,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現當代戲劇影視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