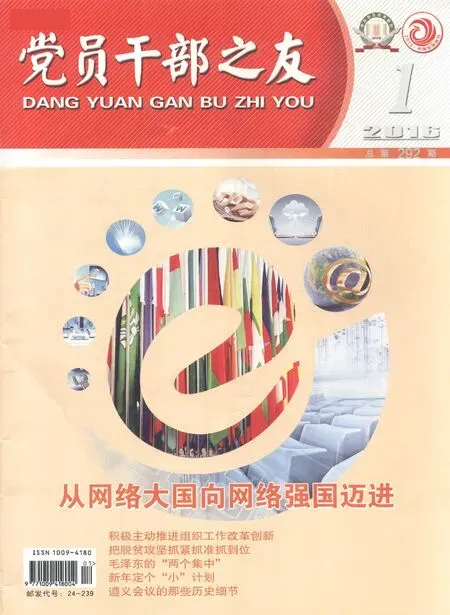新年定個“小”計劃
□ 逄春階
?
新年定個“小”計劃
□ 逄春階

黎 青/圖
新年新起點,總有新打算。有的寫在本子上,有的存在電腦上,有的印在腦海里。可年終一盤點,大而無當的計劃,大都落空。這樣的計劃有什么用呢?沒用處的計劃,不做也罷。從2014年開始,決計痛改前非。大計劃不定了,定“小”計劃,一年計劃一件事,必須完成的一件事。簡言之,就是學會用“減法”定計劃。
先說一年的讀書計劃。“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一年讀一本書。比如我2013年定計劃,2014年要讀完法國作家普魯斯特100萬字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這本書買了都20年了,書都發黃了,可拿起來就放下,難道一輩子都讀不完了嗎?不行,一年就一本書,沒時間就插空讀,結果還真讀完了,而且寫了詳細的讀書筆記。
我把這個計劃叫作“一本書主義”讀書計劃。“一本書主義”的說法,來自大作家丁玲。《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白夜1979年在《新聞戰線》雜志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當過記者的丁玲》的文章。白夜援引丁玲的回憶:“我在中央研究所任所長,一些學生來找我,看到我家中一本又一本的裝幀精美的外文書,都是什么普希金、托爾斯泰、雨果、狄更斯的名著。我就對他們說,一個人要是一輩子寫出這樣一本書,也就不錯了。后來這話傳出去,就成了‘一本書主義’。”丁玲還在不同場合說過類似的話,比如她在給一個文學青年的信中說:“寫文章不是要多,而是要好。過去有一個外國作家對我說過,鞋子要一百雙差不多的,不要只有一雙好的。而作品相反,不要一百篇差不多的,只有一篇好的也行,我認為這是對的。”
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是指一個作家必須寫一部立得住、傳得下去的書,要有一本足以支撐自己的書。而我作為讀者,要求自己一年下功夫讀一本書,讀一本立得住、傳得下去的書,也就是經典書。這個計劃是不是太“小”呢?一點不“小”。
以我為例。整天忙忙活活,一本本新書從網上購過來,翻翻前言,再看看后記,然后就束之高閣。有時自嘲,我就跟皇帝一樣,把天下美女選進宮中,據為己有,就再不眷顧了。書房里的書,大都簇新。但天天忙,忙著刷手機微信,還有博客、微博,已經沒有了耐心來看一本完整的書,整天泡在淺表化的段子里。所謂的“讀書”,是“虛胖”,水分太多,有量無質。讀一本書已經很難,讀一本經典書,那就更難。所以,必須給自己定個最低標準,一年看一本完整的經典。
知識的海洋真是無邊無沿,如果抓不到一根木板或者一個救生圈,真有可能被學海淹死。那根木板和救生圈是什么呢?我覺得就是那些經典書,經過了歲月的淘洗,至今仍然閃著光澤的書。1954年,著名哲學家熊十力先生寫給他的弟子張中行的條幅是:“每日于百忙中,須取古今大著讀之,至少數頁,毋間斷。尋玩義理須向多方體究,更須鉆入深處,勿以浮泛知解為實悟也。”我特別喜歡這幾句話。熊十力先生強調的是讀古今大著“毋間斷”,這真是防止被學海淹沒的鑰匙。一本書啃透了,那本書慢慢成了你在學海里的“島嶼”,一本書一本書地啃,“島嶼”就慢慢變大,隨著“島嶼”面積的擴大,一個人的自由度也就一天天慢慢變大。
學人讀“一本書”的例子很多。古人有得一本書而達到“終身弗離,王侯可讓,寢饋可廢”的地步。當代文學評論家劉再復回憶自己的恩師鄭朝宗先生,說“他是一個真正影響過我,真正在我的心坎中投下過寶石的人”。鄭先生指點劉再復讀錢鐘書先生的《管錐編》,他在信中說:“你對《管錐編》一定要‘天天讀’。”后來劉再復回憶說:“我聽了鄭老師的話,從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九年幾乎天天讀!到了海外之后,我寫作《人論二十五種》,其中的‘肉人’‘忍人’概念和許多例子都得益于《管錐編》。在鄭老師啟迪之下,我兩次讀破《管錐編》,這確實使我的學術素養有所長進。”
再說一年的“瘦身”家庭計劃。原來我也是定得滿滿當當,探親,訪友,旅游,健身,“一二三四”一大堆。每年都有個要到黑龍江尚志市葦河林場看小姑的計劃。小姑是逃荒到東北的,一去五十多年。但我去看望的計劃總實現不了。
2014年底,我就定了一個“瘦身”計劃,計劃2015年到東北去。從一月開始,二月、三月悄悄過,四月、五月溜達著過,眨眼間到了十月。手頭工作忙啊,一件又一件,離不開啊;從濟南到葦河林場1700多公里啊。理由一大堆,都在干擾著你,不能去。怎么辦?看看2015年時間不多了,有天夜里睡不著了,一年就定了一個計劃,竟然還完不成。計劃服從變化,還算個誠實之人嗎?
猶豫啥?來個痛快的!爬起來,網上訂票。于是在11月1日就飛到了小姑身邊。小姑78歲了,第一句話就惹出了我的眼淚:“天天說來,天天說來,還真來了。”我見到了至少四十年沒見的小姑。拉著小姑的手,我才發現,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理由,所有的理由都是脆弱的,不堪一擊的。我的計劃完成了。2015年,很圓滿。我找回了親情。
為什么以前去不了呢?因為看望小姑的計劃被淹沒在我定的宏大計劃中了。說我內心里沒有小姑,也不對。我經常在心里想著,但就是邁不動腿,下不了決心,沒把看望當成一件大事情。而當我一年就定了這個唯一的計劃時,就完成了。
生年不滿百,除去童蒙和耄耋之齡,除去病魔的入侵之外,真正能做事的時間,不過短短幾十年,如果什么都想去干,則什么也干不成。必須收縮陣線,選最重要的,舍棄那些不重要的,選自己最合適的,放棄那些能力不及的。有所為,有所不為。計劃就是想法。想法想法,想著想著,就想多了。就跟一棵樹一樣,得修剪掉多余的枝條。懂得舍棄,敢于放棄,勇于拋棄。
怎么修剪?我想到了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這個建議起草把握了幾個原則,其中第一個原則是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統一。我覺得這個原則也可以適應個人計劃的制定。國家規劃和個人規劃,道理是一樣的,以大比小。一個美好的規劃,必定有一個美好的目標。但目標再美好,也必須接地氣,必須符合自身。如果你不是宇航員,卻定個上天的目標,肯定就是癡心妄想。把妄想的所謂“目標”剔除了,剩下的就是實實在在的目標。目標有了,還必須找出阻礙實現目標的問題,問題就是矛盾,找出了問題,找出了矛盾,然后解決了,目標就實現了,計劃就落地了。
當代山水詩人孔孚有個原則,寫詩用減法,我看過他的手稿,勾勾畫畫,涂涂抹抹。刪去的多,涂去的多,詩人在大砍大削。原來,好詩是刪出來、減出來的。他的短詩《春日遠眺佛慧山》原稿是:“佛頭,青了。一顱的智慧,生出牙兒了吧?”定稿是:“佛頭,青了。”在手稿的邊上詩人說:“尾象:靈象。雖則靈象,但仍點破。泥于‘智慧’極其生發。仍在‘有限’境界。剜肉刪去,入‘無’。”把詩的后兩句刪去,那滋味是剜肉一般,看來減法不易。詩人一開始雖然意識到應該刪去,但還是下不了手,刪去又恢復,是“從眾”,是“拘成法”。但孔孚畢竟是孔孚,他那“獨步流俗”的膽識占了上風,“剜肉”刪去后兩句。詩不能湊合,湊合就把詩湊合掉了。
個人計劃也不能湊合,湊合就把什么都耽誤了。不湊合,就得用減法,減而又減,減到一,唯一。唯一的計劃,倒逼你完成。完成了,自己給自己點個贊。
祝大家新年都有個“瘦身”計劃。
(作者為《大眾日報》高級記者、山東省首批簽約文藝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