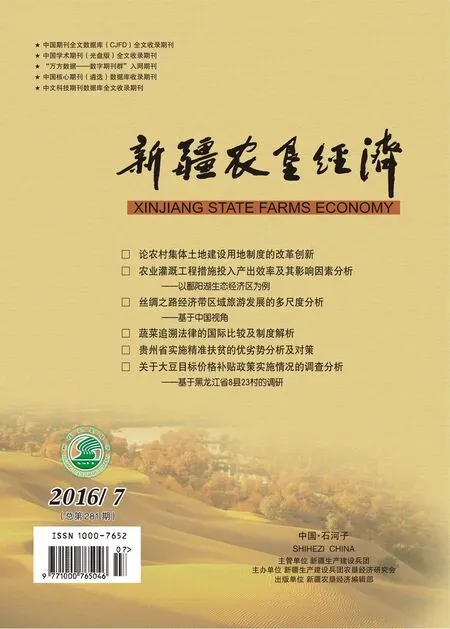農民工匯款與主觀幸福感:基于CHIPS2008的微觀數據
詹利娟 鄭 璐
(四川農業大學,四川 成都 611130)
農民工匯款與主觀幸福感:基于CHIPS2008的微觀數據
詹利娟鄭 璐
(四川農業大學,四川 成都 611130)
文章運用2009年中國家庭收入項目調查數據(CHIPS2008),對我國農民工匯款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同時使用一年中農民工在外出務工經商地生活月數作為工具變量處理可能的內生性偏誤,結論通過了較為嚴格的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農民工絕對匯款額與其主觀幸福感負相關,小幅降低了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絕對匯款額對幸福感的邊際效應高于收入帶來的邊際效用,即使控制了人均匯款額和相對匯款額,匯款依然降低了主觀幸福感水平。
農民工;主觀幸福感;匯款
一、引言
改革開放后,我國勞動力流動性限制逐步放松,廉價勞動力和優惠政策吸引著國外勞動密集型加工業不斷向東部沿海地區轉移,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城鎮成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聚集地,由此帶來了“民工潮”現象。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等一系列國家戰略計劃的實施,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規模將進一步擴大,并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力量。據預測,外出農民工2020年將達1.77億人,2030年1.9億人[1]。國內城鄉移民帶來了匯款的內部流動。基于我國農民的特殊家庭關系,農民工會將其收入寄回家鄉,農民工與家鄉的資金流通長期保持著高流量。大量的農民工匯款主要用于消費,部分用于投資性生產活動,其無論對于輸出地經濟發展還是農村家庭生活質量的提高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2]。
新型城鎮化建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其核心在于實現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最終落腳點在于農民工生活質量的提升。伴隨著經濟發展,農民工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后,必然會重視生活質量的提高,即時代的發展應該與人民主觀幸福感提升的要求相適應。近年來,卻呈現出“幸福停滯”的經濟增長現象,一系列“幸福工程”、“民生工程”等收效甚微[3]。許多地方政府將國民幸福感水平作為衡量發展成果的主要標準。那么,如何使得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的幸福感有效提升呢?規模日益增大的匯款是否對農民工的幸福感產生影響?會是怎樣的影響呢?
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利用CHIPS2008的橫截面數據,使用是否匯款以及匯款額度作為農民工匯款的指標,考察其對于農民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匯款不是狹義的僅指代銀行轉賬,而是廣義的包含銀行轉賬、寄回老家的實物折現和現金,這也與國內外研究相一致。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一)文獻綜述
關于幸福感的研究分為主觀幸福感和客觀幸福感,主觀幸福感從快樂論出發,是對現有生活滿意程度的整體性評價。21世紀以來,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主觀幸福感進行探討。微觀變量,諸如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收入及婚姻狀況均對主觀幸福感產生影響[4],但是不同學者在分析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子女數量等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程度時仍存在一些差異;此外,個人特征變量,諸如基因[5]、就業狀況[6]、健康狀況[7-10],同樣影響農民工的幸福感水平。在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中,收入特征作為影響人們生活和精神質量的重要變量,是現代經濟社會中福利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按照經濟理性假設理論,主觀幸福感和收入成正向關系;但實際上,“臨界點理論”認為,一國的平均幸福水平并不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而提高[9],這是因為當收入達到臨界點時,人們往往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或者對生活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除了絕對收入水平之外,相對收入水平[6]、收入預期[11]在主觀幸福感中同樣較為顯著。當然,家庭負債也影響著人們的幸福感水平[10]。Borraz[12]通過分析留守家庭成員(收款人)的匯款和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發現匯款和收款人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Alpaslan etal[13]在前人的理論基礎上,首次針對移民者匯款和其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展開研究,他通過實證發現,匯款對移民者的主觀幸福感有著正相關關系。綜上所述,在不斷更深層次的研究中,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研究的理論依據越來越充分,其中主觀幸福感與收入關系是研究熱點;而在移民匯款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這方面,國外少數學者開始逐步涉入,但國內尚未開始對其探討。
(二)理論分析
根據文獻綜述繼續進行理論分析:主觀幸福感的測量主要包含幸福程度(Happiness)、生活滿意程度(Life-Satisfaction)和心理健康程度(Mental Health)三種方法,一般健康問卷(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是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常常用來測量心理健康程度的方法,能有效評價主觀幸福感[14]。在處理一般健康問卷處理時,最常見的經驗做法是通過運用四分法(即0-1-2-3記分法,該量表總分范圍為0-36),來計算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指數。
在解釋變量方面,作為重要資本流動的匯款,是農民工收入的一部分,由于收入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13],農民工的匯款行為擠出其可支配收入,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會降低,由此,可提出研究假設H1:農民工匯款與主觀幸福感顯著正相關;但是,根據利他性理論[14-15]和家庭隱性借貸理論[7],農民工的匯款使得其匯款目的得以達成,匯款者也許會因此感到自身主觀幸福感的增加,由此,可提出研究假設H2:農民工匯款與主觀幸福感顯著負相關。
在控制變量方面,以往文獻顯示,影響農民工幸福感的控制變量可分為兩類:個人特征層面的控制變量集與家庭經濟層面的控制變量集。個人特征層面的控制變量主要有:(1)年齡。近年來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力,年齡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往往呈現出“U”形特征。(2)婚姻狀況。農民工婚姻狀況在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中是極為重要的控制變量之一,通常已婚人群對生活更滿意。(3)子女數量。由于孩子的養育需要付出一定的時間成本和貨幣成本,子女數量與主觀幸福感存在緊密的聯系。(4)性別。性別變量是影響人際體驗的重要因素,在我國,男性通常承擔較大的家庭責任,女性往往具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5)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的提升能帶動個人的經濟地位的提高,從而獲得社會支持,提高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6)就業狀況。就業狀況是造成農民工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也是影響農民工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家庭經濟層面的控制變量主要有:(1)勞動力收入。一般來說,勞動力收入和農民工的是密切相關的,由于農民工自身的經濟收入處在較低水平,勞動力收入和其主觀幸福感呈現出正向關系。(2)家庭負債。較高負債的家庭可能對未來有較好預期,往往具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17]。
三、變量選擇、模型構建及數據來源
(一)變量選擇
在變量選擇方面,本文選取使用四分法計算得出的主觀幸福感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農民工家庭月匯款絕對值作為解釋變量,農民工的個人特征變量(性別,年齡及其平方值,子女數量,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和家庭經濟特征變量(勞動力收入,家庭負債)作為控制變量。此外,本文在處理內生性問題時采用了一年中農民工外出務工經商月數作為工具變量;穩健性檢驗時增加了人均匯款額和相對匯款額兩個變量:人均匯款額的大小一方面能反映匯款總額,另一方面也能反映農民工的家庭負擔,即家中需要照顧的老人和子女數量;相對匯款額分析匯款總額與勞動力收入之間的相對關系。
(二)模型構建
為了研究農民工匯款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按照前人的研究,設定如下基本計量回歸模型:

在模型(1)中,被解釋變量SWBi表示第i個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指數。主要解釋變量Ri表示第i個農民工的家庭月匯款水平;解釋變量Xi表示第i個農民工的個人層面的控制變量集,包括:性別(以男性為參照組),年齡及其平方值,子女數量,婚姻狀況(以已婚為參照組),受教育程度,就業狀況(以已就業為參照組);解釋變量Yi表示第i個農民工的家庭經濟狀況,包括每個月農民工的勞動力收入和家庭負債;α0,α1,α2,α3為待估參數的系數或系數向量,εi為回歸模型的誤差項。
(三)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于“中國家庭收入項目調查”(CHIPS)在2009年開展的微觀調研,該調查涉及9個省份15個城市,涵蓋了5000個城鎮家庭樣本、8000個農村家庭樣本和5000個城鄉移民樣本。調查項目由北京師范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昆士蘭大學的學者發起,得到了德國勞動研究所(IZA)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NBS)的支持。基于研究目的,本文選擇了CHIPS (2008)數據庫中的城鄉移民人口樣本,該樣本數據全面反映了城鄉移民的人口統計特征、收入與消費、保險與保障、家庭經營與生活等方面的基本狀況,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在本研究中,剔除了一些指標具有缺失值的樣本。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表1 主觀幸福感的分布狀況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樣本數據的主觀幸福感指數分布狀況匯報在表1中,總共包含有效樣本數目為3368個。其中,0.06%的農民工幸福感為0,35.04%的農民工主觀幸福感指數在30以上,近半數的農民工主觀幸福感指數在25-30之間。總體而言,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分布相對集中,農民工主觀幸福感指數越高,分布的人越多。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第(3)列沒有考慮家庭匯款,研究農民工個人特征和其他家庭經濟特征變量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就農民工個人特征而言:年齡和年齡的平方的回歸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下分別顯著為
(二)基準回歸結果
由于主觀幸福感為非負的連續變量,因此,首先采用Tobit方法對計量模型進行估計。基準回歸結果見表3。
第(1)列只考慮了匯款對農民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數據顯示,在沒有引入控制變量的情況下,匯款的回歸系數在統計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匯款顯著降低了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但降低的幅度較低。回歸式(2)考慮了包括匯款在內的所有變量,此時匯款額的系數依然為較小的負數,匯款對于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帶來顯著的較微弱的負面影響。因此,無論是否引入控制變量,負和為正,說明我國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隨著年齡的增長先下降而后上升,兩者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呈現“U”形特征,這與Blanchflower and Oswald的研究一致[15];男性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男性要比女性幸福;婚姻狀況的結果表明,已婚者的幸福感要顯著高于未婚者;失業的農民工主觀幸福感非常顯著地低于就業的農民工,這是由于失業群體絕對收入水平和相對收入水平減少,失業群體對未來的收入有更悲觀的預期,生活狀態也更加趨向于惡化;而子女數量變量的系數不顯著,表明家庭中有無子女對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沒有顯著的影響;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對其主觀幸福感產生影響,在5%的統計水平下,受教育年限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受教育年限越長,農民工的幸福感反而越低,這與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CHFS)的數據表明在被調查者中學歷越高幸福感反而降低的結論相似。就家庭層面而言,家庭負債在5%的統計水平下顯著為正,結果表明家庭負債對主觀幸福感也具有較微弱但顯著的正向作用。勞動力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是正向的,且非常顯著,勞動力收入是影響成長發展體驗、目標價值體驗、心態平衡體驗和家庭氛圍體驗的主要因素[17],但是匯款對農民工幸福感的邊際效應大于收入的邊際效應。

表3 農民工匯款與主觀幸福感關系的實證結果
另外,第(4)(5)(6)列均采用Ologit模型,回歸結果和使用Tobit類似,匯款額變量依然十分顯著。
(三)內生性處理
使用Tobit模型估計計量方程(1)時會導致關鍵參數的有偏估計。在估計方程(1)時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Ri可能與誤差項εi相關,即主觀幸福感可能對匯款水平產生影響,農民工匯款行為可能較難增加其主觀幸福感,因此農民工匯款數額與其主觀幸福感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為了修正內生性偏誤,本文使用工具變量LM,其表示過去一年里農民工在外出務工經商地一共生活的月數(不足一個月按一個月計算)。LM工具變量會對農民工的匯款頻率有直接影響,進而影響匯款額,但并不會直接影響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水平。之所以選擇LM作為工具變量,是因為農民工在外出務工經商地的生活時間與其向家中的匯款額具有相關性,一般來說,一年中農民工離家月數越大,向家中的月匯款額度會上升,而且農民工在外出務工經商的月數也滿足排除限制,但是該工具變量對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卻不會產生直接影響。
“清欠行動”的難點與對策建議:一是部分地區政府財政困難導致難以做到 “限時清零”。不可否認的是,部分地區政府部門拖欠民營企業的賬款,就是因為財政有收支缺口。對于此類難題,在建立臺賬的基礎上,允許一定的“清零”緩沖期,同時政府部門領導也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氣度,樹立“看菜吃飯”意識,杜絕不顧經濟實力搞“大建設”“大操辦”等不良心理,防范新欠現象。二是三角債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清欠行動”的順利推進。一些國有大企業拖欠民營企業的賬款,或許是因其陷入三角債問題,為此建議清欠行動組要厘清欠款原因,適當拉長戰線,做到在解決民營企業問題的同時解決國有大企業的發展問題,營造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資金運行環境。
運用該工具變量,使用IVTobit模型,結果報告在表3中第(7)列;同時使用了2SLS估計模型,回歸結果報告在表3中第(8)(9)列。表3第(7)(9)列顯示,Wald外生性排除檢驗都拒絕了匯款額是外生變量的原假設,即匯款額是內生性變量。表3第(8)列顯示,在2SLS模型第二階段使用工具變量LM時,弱工具變量的穩健性檢驗拒絕了原假設,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因此,所用的工具變量既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也不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選用工具變量LM來估計農民工匯款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十分必要且合適。結果顯示,加入工具變量后,匯款對主觀幸福感依然顯著。
(四)穩健性問題
通過前面的計量分析,發現農民工的匯款增加會顯著微弱降低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為了考察該研究結果的可靠性,進行了如下的穩健性檢驗。首先使用農民工匯款額的替代性工具變量再對基本模型進行回歸;然后考慮納入新的控制變量是否對結果產生影響。穩健性檢驗結果經整理見表4。

表4穩健性檢驗結果
1.尋找農民工匯款額的替代性工具變量。在前文,采用農民工匯款絕對數作為主要解釋變量,反映了農民工匯款絕對水平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在穩健性檢驗中,分別采用農民工人均匯款額、相對匯款額、是否有匯款的虛擬變量作為農民工匯款額的替代性變量,表4中,分別使用匯款額、人均匯款額、相對匯款額回歸時,其系數絕對值是逐漸變大的,其中相對匯款額系數絕對值相對于匯款額達到了近300倍,這可能與相對匯款額是基于勞動力收入計算的有關[16],同時也說明了相對匯款額的增大對農民工幸福感的影響遠大于絕對匯款額和人均匯款額。總體來看,匯款水平確實對農民工主觀幸福感有顯著影響,主要結論依然成立。
2.納入醫療支出控制變量。醫療支出的有效控制被視為影響農民工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是因為:一方面,較少的醫療支出意味著農民工具有良好的身體健康狀況;另一方面,較少的農民工醫療費用反映出社會具備較好的醫療保障體系,有助于減輕農民工醫療費用負擔,為其在城市融入過程中營造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因此,納入醫療支出作為控制變量再次回歸基準模型,結果匯報在表4第(2)列,可以看出,加入醫療支出變量后,匯款額、人均匯款額和相對匯款額的系數均保持顯著為負的狀態,醫療支出系數保持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農民工的匯款行為對其主觀幸福感有著微弱且穩定的負面影響,醫療支出變量基本不影響農民工的匯款行為。因此,可以認為模型是穩健的。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運用中國家庭收入項目調查(CHIPS2008)的數據,實證分析匯款對農民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發現,農民工的匯款行為對其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匯款小幅度降低了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但農民工匯款絕對額對幸福感的邊際效應遠大于收入效應,相對匯款額對農民工幸福感的邊際效應大于絕對匯款額和人均匯款額的邊際效應。因此,本文認為匯款尤其是相對匯款是改善農民工福利的重要途徑。相關結果在考慮內生性的問題時依然成立。本研究結論與Alpaslan Akay等[16]的發現相反,這可能出于以下兩個原因:首先,匯款行為使得農民工自身可支配收入減少,改變了農民工的知足充裕感,從而影響其主觀幸福感;其次,實證數據主要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農民工基本情況,該時期勞動力市場萎縮,再加上經濟不確定性增大,匯款改變了農民工的社會信心,農民工出于預防性動機減少匯款數額,匯款行為抑制了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
提升農民工幸福感本身是一項復雜、立體、長期的社會系統性工程,本研究從匯款的角度考察幸福感,進一步加深了對農民工主觀幸福感影響的理解。在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全球經濟進入了“長期停滯”時期,對我國經濟持續產生負面影響[20];此外,國內經濟結構失衡的調整和城鎮化的轉型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此帶來的我國經濟下行壓力的持續加大,使得社會就業吸納能力減弱,農民工的就業壓力增大。
(二)政策建議
為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利益,應該從匯款額的減少和收入的增加入手,促進幸福感的上升,這將為農民工帶來更多的正向情緒,有助于增加其人力資本,緩解農民工“就業難”現象,為農民工帶來更多的客觀利益[21-23],從而有助于實現以幸福感提升為目的的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對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我國目前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也出現不平衡現狀,許多地區農村社保水平與農民日益提高的物質生活水平不相適應,部分偏遠地區甚至尚未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由于匯款的利他性動機,農民工會將更多收入寄回家,以保障留守家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因此,政府在完成社會保障體系全覆蓋的同時,要根據各地實際情況設計,確保能夠真正實現“保基本”“多層次”,以切實減輕農民工的經濟負擔,提升農民工幸福感。
2.提供農民工返鄉創業服務資源。一方面,政府應該致力于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形成有利于城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機制,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良好的環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應積極創建農民工返鄉創業園,通過創業扶持政策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以創業進一步帶動輸出地的就業。通過提供完善農民工返鄉創業服務資源,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不僅減小了我國嚴峻的就業壓力,帶動了輸出地經濟增長,而且通過回鄉創業,農民工的匯款降低,主觀幸福感也得以提升。
[1]巴曙松,等.城鎮化大轉型的金融視角:移民者崛起能否消費擴張動力[M].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2]胡楓,王其文.中國農民工匯款的影響因素分析——一個區間回歸模型的應用[J].統計研究,2007,(10):21-25.
[3]陳剛,李樹.政府如何能夠讓人幸福?——政府質量影響居民幸福感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2,(8):55-67.
[4]張艷華,于晶,常波.城區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分析——以沈陽市城區居民為例[J].吉首大學學報,2008,(30):120-123.
[5]Lykken D and Tellegen A.Happiness is a stochasticphenomenon[J].PsychologicalScience,1996,(7):186-189.
[6]魯元平,王韜.收入不平等、社會犯罪與國民幸福感——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J].經濟學,2011,(10):1437-1458.
[7]陳釗,等.戶籍身份、示范效應與居民幸福感——來自上海和深圳社區的證據[J].世界經濟,2012,(4):80-101.
[8]Shields M A,Price S W.Explo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England[J].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Series A(Statistics in Society),2005,168,(3):513-537.
[9]Easterlin R A.Income and happiness:Towards a unified theory[J].The economic journal,2001,111,(473):465-484.
[10]Frey B.and A.Stutzer.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40):402-435.
[11]羅楚亮.絕對收入、相對收入與主觀幸福感——來自中國城鄉住戶調查數據的經驗分析[J].財經研究,2008,(11):81-91.
[12]胡楓,史宇鵬.農民工匯款與輸出地經濟發展——基于農民工匯款用途的影響因素分析[J].世界經濟文匯,2013,(2):80—94.
[13]Alpaslan Akay,Corrado Giulietti,Juan D.Robalino,and Klaus F.Zimmermann.Remittances and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M].IZA Discussion Paper,2012,(6631).
[14]Clark,A.and A.Oswald.A simple statistical method for measuring how life events act happines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02,(6):1139-1144.
[15]羅芳.外來移民者家鄉匯款的影響因素及動機分析——以湖北省武漢市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07(專刊):49-57.
[16]Poirine,B.A.Theory of Remittances as an Implicit FamilyLoanArrangement[M].WorldDevelopment,1997,25(4).
[17]Blanchower D and A Oswald.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7):1359-1386.
[18]羅楚亮.城鄉分割、就業狀況與主觀幸福感差異[J].經濟學季刊,2006,(5):817-839.
[19]李強,毛學峰,張濤.農民工匯款的決策、數量與用途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08,(3):2-12.
[20]李揚,張曉晶.“新常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前景[J].經濟研究,2015,(5):4-19.
[21]De Neve J.and A.J.Oswald.Estimating the Influence of Life Satisfication:A Test of the Baseline Hypothesis[J].Economical Journal,2012,(118):222-243.
[22]Gielen A.C.and J.C.van Ours.Unhappiness and Job Finding[J].Economica,2014,(81):544-565.
[23]李樹,陳剛.幸福的就業效應——對幸福感、就業和隱性再就業的經驗研究[J].經濟研究,2015,(3):62-99.
(責任編輯:車碧云)
詹利娟(1993-),女,四川成都人,本科生,研究方向:農村金融、福利經濟學;鄭璐(1994-),女,四川德陽人,本科生,研究方向:財務管理學、福利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