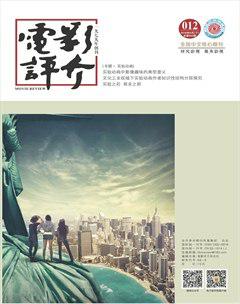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視頻內容跨屏傳播研究
王兆紅 劉慶振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視頻內容跨屏傳播研究
王兆紅 劉慶振
媒介融合的趨勢打破了過去邊界清晰的產業競爭格局,跨界融合成為當前這一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的熱門話題,不單是傳媒產業和電信產業內部外部的邊界逐漸模糊,就連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之間、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界限也在逐漸消融。但是,當前的媒介融合的確存在諸多“融而不合”的因素,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跨屏傳播實踐及其效果測量的實現。當然我們也堅信,隨著媒介融合的進一步發展和屏幕作為基礎設施乃至公共設施的作用進一步發揮,跨屏傳播必將成為一個無法阻擋的趨勢和毋庸爭議的事實。
一、視頻跨屏傳播興起的主要動因
截至2014年底,我國電視用戶達到12.9億,而網絡視頻用戶為4.8億,移動視頻用戶為2.8億,戶外視頻媒體(包括戶外大屏、公交、地鐵、樓宇電梯、賣場等媒體形式)用戶為1.1億人;電影觀影人次8.3億。[1]這其中,約有2億左右的用戶是在電視屏、電腦屏和移動終端屏之間重疊出現的,這也就意味著這些用戶會在不同場景、不同時段甚至不同身心狀態之間進行收視模式的切換和屏幕使用的轉換。在費用方面,除了影院電影、少量付費視頻和基本的有線電視費、網絡通信費之外,受眾所接觸到的大部分視頻內容幾乎都是免費的。受眾用自己的注意力資源交換了免費的視頻內容,而平臺運營商(電視臺、視頻網站等)則通過整合受眾注意力并將此打包出售給廣告主而獲得相應的廣告收益。2013年廣播電視廣告收入為1302億元(廣電總局數據),而2014年網絡視頻廣告收入為152億元(艾瑞數據),網絡視頻廣告收入約為電視廣告收入的1/10。然而,無論從用戶規模還是從收視效果而言,網絡視頻廣告的價值相對電視廣告而言都被低估了。產業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必然意味著競爭格局的進一步演進直至相對均衡。
這樣,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進者與守成者之間的產業競爭加劇成為跨屏傳播興起的重要原因,跨屏傳播成為產業競爭、合作、沖突、博弈的重要陣地。后起的互聯網視頻、移動視頻想要在廣告收入的規模和比重方面都能夠出現較大的增長,不惜重金在影視劇、綜藝節目、用戶原創等優質內容方面進行投資,并通過多頻次、多渠道、多屏幕的分發實現受眾規模的最大化。典型的例子如樂視,一直致力于打造垂直整合的“平臺+內容+終端+應用”的完整生態模式,并提出了“全屏實力”的概念,旨在實現電腦、電視、手機、PAD、電影五屏跨界聯動。而事實上,樂視進軍電視屏幕也是命途多舛,樂視盒子曾一度被廣電總局叫停。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媒介融合的規制政策并沒有真正調整,各種市場力量和行政力量的沖突和博弈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2015年4月樂視又重拳推出超級手機,這也是其在跨屏傳播實踐中的重要布局。相對新進者而言,電視臺在跨屏傳播方面的探索是由市場倒逼效應而推進的被動防御,主要是為了遏制視頻網站對自身收視率的沖擊和對廣告市場的進一步蠶食。然而除了湖南衛視的跨屏嘗試表現搶眼之外,無論是央視、東方衛視還是其他衛視諸侯,在跨屏方面都少有可圈可點之處。2014年12月31日,湖南衛視跨年演唱會直播當晚,芒果TV首次推出360度全方位網絡互動創意直播服務,用戶可以通過手機、電腦、平板、芒果互聯網電視、湖南IPTV等平臺進入相關專題頁面,對直播機位進行自主選擇、自主切換、自主導播,每個機位將拍攝包括后臺、全景、側景、特寫等演唱會視角,用戶還可以為自己喜歡的機位投票。實際上,運用產業競爭的五力模型來分析,視頻跨屏傳播就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電視臺之間、視頻網站之間、電信運營商之間、電視臺與視頻網站之間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視頻平臺運營商之間為了最大化自身的受眾規模和廣告收入而興起的。這種競合關系背后,既有產業鏈各環節的不同利益,又有更宏觀層面的規制部門間的不同利益。
跨屏傳播興起的另外一個動因就是視頻內容產業外部的廣告主的精準營銷需求,這與產業內部的競爭實際上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廣告主及其代理人廣告公司一方面希望自己的產品信息能夠實現最大范圍的覆蓋,另一方面希望信息能夠精準到達目標消費者進而提高自身在營銷和廣告方面的投資回報率(ROI)。由于傳統的專門化傳播“屏幕”的單向化、非智能化,廣告主“知道自己的費用有一半是浪費了的,但卻不知道是哪一半”,因此,其廣告投放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廣泛覆蓋。但是,隨著雙向傳播的智能化、互動化、融合化屏幕的大規模運用,視頻的多屏幕傳播和受眾的多屏幕收看已經是非常清晰的現實,加之媒介融合技術和大數據技術的突破,受眾在看屏幕的同時,屏幕以及屏幕背后的平臺運營商、內容運營商、廣告公司和廣告主也能夠實現對受眾的洞察。市場的需求和技術的支撐使得精準營銷成為可能,既然大量消費者或受眾擁有多個屏幕,那么廣告主當然希望在洞察消費者收視行為和產品需求的前提下能夠精準的、多頻次的、多屏幕的到達目標消費者,從而最小化自身的營銷成本。受眾的跨屏收視行為和廣告主的跨屏傳播需求就成為視頻跨屏傳播興起的重要動因。與此同時,內容運營商、平臺運營商、廣告公司、廣告主對跨屏傳播的效果測量需求也應運而生。“目前視頻媒體的每個細分領域各有一套相對獨立的測量體系,從評估指標到測量技術,都有所不同。如何融合這些不同的測量方法、或者推出新的跨屏測量體系,并且形成行業標準,是測量技術和實施方法都面臨的挑戰。”[2]
二、規制融合是實現跨屏傳播的關鍵突破口
跨屏傳播在實踐層面上遇到的各種困境,歸根結底是產業政策的頂層設計問題,而不是市場需求、技術難度等問題。只有實現了產業規制政策的融合,跨屏傳播當前遇到的問題才能迎刃而解。“媒介融合促進了規制融合,而規制融合是真正實現媒介融合的前提。”[3]需要強調的是,媒介融合的確會對規制變遷產生促進影響,但是,“媒介自身的經營調整所引發的對于文化、制度上的影響,甚至形成一種制度改革的期許,與其說媒介產業化推動者的主觀意識,不如說是產業化事實邏輯的倒逼效應”[4]。傳統縱向模式的分業規制出現了規制重疊和阻礙競爭現象的現象,而產業融合、媒介融合、跨界融合都意味著傳統縱向規制政策不能適應新的產業競爭和經濟發展,這在客觀上倒逼產業規制在橫向層面成立融合規制部門、樹立融合規制理念、消除媒介融合的政策梗阻。
當然這種規制融合必須是在明確區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堅持公平與效率并重的前提下展開的,畢竟文化產品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同時涉及到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宣傳和整個國家的文化安全問題。因此,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更不能將對事業的管理和對產業的規制混為一談,必須清晰的界定哪些領域屬于事業范疇,哪些領域屬于產業范疇,真正做到“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而本文指的規制融合,主要是針對產業屬性的媒介融合而言的,在強調逐漸放松進入許可等經濟性規制的同時,也需要進一步強化內容監管、防止壟斷等社會性規制,進而形成新的橫向融合型、競爭型的產業規制體系。
融合型的規制體系建立以后,對于不同屏幕允許呈現的視頻內容的監管標準是統一的,在電視屏幕呈現出來的內容具有負外部性,也意味著在電腦屏幕、手機屏幕或者其他屏幕呈現出來同樣具有負外部性,為什么要對各個屏幕所呈現的內容進行區別對待呢?規制政策不能因為電視觀眾的基數大、手機視頻用戶的基數相對較小,就對兩個屏幕進行區隔對待,更不能以此為借口而抵制規制融合的進程。在規制融合的基礎上,競爭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垂直統合下的電視臺之間的競爭、視頻網站之間的競爭、電信運營商之間的競爭,而是同一水平層面的各個主體之間的融合競爭,進而直觀的表現在各個屏幕終端上對受眾注意力的競爭。只有真正實現了規制層面的融合,跨屏傳播才具有了合法性地位。雖然規制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畢竟,這個進程伴隨著媒介融合的步伐已經開啟。
三、從IP到ID的產業競爭新策略
事實上,受眾或用戶“只關注具體的媒介形態是否更加簡便易用,媒介內容是否能夠滿足自身的需求,而不會去關注媒介體制和媒介融合的問題”[5],他們的根本需求不是報紙、電視機、電腦和手機,而是信息、娛樂、社交和意見結晶。如果有一種方式讓他們無須擁有或攜帶任何一種設備或屏幕就能獲得這些,那么他們就會什么也不擁有、什么也不攜帶。產業競爭的本質同樣如此,企業要的不是寬帶、光纖、無線終端等傳輸設備,也不是電視機、電腦、手機等終端屏幕,更不是成千上萬的員工或數以億計的觀眾,而是利潤。如果一個用戶能夠為企業貢獻全部的利潤,那么企業就會拋棄其他所有用戶。因此,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跨屏傳播的本質是使傳播內容在任何時空范圍內最大化的到達精準受眾,而跨屏傳播時代的產業競爭的本質則是利用這些精準受眾實現收益最大化。在當前的產業競爭環境下(圖1),內容的生產制作環節、集成分發環節和終端屏幕制造環節都充斥著幾家到十幾家實力較強的企業以及成百上千家的中小企業,并呈現出同質化激烈競爭的態勢。當前的媒介融合格局,稀缺的不是上述的中間環節,而是兩端:一端是跨屏傳播的內容源點即IP,一端是跨屏傳播的內容終點即ID(受眾或用戶)。而當在媒介融合和大數據技術基礎之上形成跨屏傳播的數據調查機構或監測工具之后,終點用戶的數據便能夠真正成為創意源點的決策依據,進而形成了媒介內容生產與傳播的閉環。因此,隨著屏幕越來越普及并成為媒介融合時代的基礎公共設施,同時伴隨著中間幾大環節的大企業通過兼并重組增強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并向產業鏈上下游滲透的步伐,未來產業競爭的藍海也將逐漸轉向跨屏傳播的內容源點和收視終點。

圖1 內容生產從鏈狀模式到閉環模式
四、從平臺為王向內容為王回歸
媒介融合的進程在另外一個角度而言也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的進程,當新媒體的無限傳輸對傳統媒體的渠道資源稀缺產生沖擊之時,渠道為王的呼吁甚囂塵上。于是,為了改造自身的渠道弱勢忙得不亦樂乎,傳統媒體紛紛觸網,傳統電視的有無線網、有線網向下一代廣播電視網(NGB)升級換代,以期重塑自身的渠道。當蘋果APP store、阿里巴巴、小米手機、騰訊社交生態圈受到熱捧之時,平臺為王的口號再次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于是,傳統媒體又虛心學習著互聯網企業開始搭建一個多屏傳播的生態系統,力圖適應這個全新的媒介融合時代下的跨屏傳播需求。然而,在迫不及待擁抱媒介融合時代的同時,傳統媒體實際上反而陷入了新媒體的邏輯圈套之中,新媒體不斷拋出各種概念更多情況下是為了在贏得法律寬容、時間紅利的同時,獲得資本市場的廣泛認可。視頻跨屏傳播成功的關鍵點不是誰擁有如何海量傳輸的渠道,也不是誰打造了怎樣超級的生態圈,當然這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誰的渠道或平臺上能夠呈現什么樣的內容。注意力是流動的,受眾是流動的,粉絲照樣也是流動的,他們尋找自身最感興趣的內容,而不會被所謂的渠道、平臺乃至屏幕束縛。在屏幕已經成為基礎設施、用戶能夠切換自如的可預見的未來,產業的競爭將重新回歸到內容為王的時代,受眾在根本上喜歡的是TFboys、中國好聲音、甄嬛傳、爸爸去哪兒、生活大爆炸等內容品牌,其次才是喜歡電視劇、綜藝節目、電影、新聞等形式品類,再次喜歡的才是湖南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優酷土豆、愛奇藝等渠道品牌。內容在哪里,注意力就會在哪里,受眾和消費者就會在哪里。內容是多屏分發的,那么受眾就會在多個屏幕上出現,內容能夠滿足受眾即時即地的跨屏收視需求,那么在需要的時候受眾就會跨屏而不致由于各種原因中斷收視造成注意力流失。如果沒有足夠優質的內容,即便是能夠實現跨屏的功能,也沒有多少用戶來跨這個屏。
五、從內容的創意起點鎖定跨屏傳播的終點
在回歸內容為王之后,視頻跨屏傳播的起點就是內容的創意,而在媒介融合時代,內容創意的競爭已經從傳統的作品模式的競爭升級到了更高層次的IP模式的競爭。既然媒介是融合的、屏幕是可跨的、注意力是流動的,那么如何創造出黏著注意力的超級IP就成為內容競爭的關鍵。IP模式將內容與受眾之間的關系從收視關系、消費關系升級到了更高層次的情感關系,進而產生“愛屋及烏”的衍生產品同樣受到熱烈歡迎的現象,典型的案例是就是電影《爸爸去哪兒1》斬獲7億票房,而驚悚片《京城81號》也借助《爸爸去哪兒》第二季嘉賓吳鎮宇的人氣收獲了近4億票房。IP模式的成功在于它能夠將之前對這一作品的大量粉絲的注意力遷移到不同形態的內容上去,有些IP作品的衍生內容敘事邏輯甚至都不太嚴謹,但由于受眾或粉絲已經進入它打造的話語體系或意識形態之中,他們仍能理解并沉湎其中。因此,基于IP模式的內容生產在創意階段就應該是面向受眾或粉絲的,當然也是面向多屏的,它能夠根據他們的喜好、需求和習慣衍生出諸如電影、電視劇、紀錄片、綜藝節目、動漫、短視頻、微電影、代言廣告、植入廣告等多元化的內容產品,甚至它能夠根據用戶對不同屏幕的使用頻率、接觸行為、切換習慣而對同一內容進行適當的調整,以最優化用戶的跨屏體驗。比如,由于電影的時間容量有限,內容生產商可以同時制作基于同一IP的加長版電影、紀錄片或電視劇呈現在其他屏幕上,這也將直接導致受眾從電影屏幕向電視機屏幕或電腦屏幕遷移;而適宜在手機屏幕、戶外屏幕、地鐵電視屏幕呈現的有關某一部作品的拍攝花絮、短視頻、微電影或預告片也能夠激發用戶在電影或電視機等屏幕的收視欲望。
結語
因此,跨屏傳播在本質上是一種用戶導向的傳播方式,可以稱之為用戶思維,而不是互聯網思維,互聯網思維本身是個偽命題。內容生產與傳播應該從用戶的需求出發,如果互聯網思維成立的話,電視臺做得好就應該叫電視臺思維,報紙做得好就應該叫報紙思維。因此,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產業競爭中,任何形式的媒體都不應該陷入別人的邏輯陷阱,一定要清楚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以及用戶最根本的需求,不要邯鄲學步東施效顰,最后卻在媒介融合的大潮之中迷失了自己。未來,產業環境和媒介技術仍然將繼續發生重大的變化,但是內容和用戶永遠是傳播活動兩個不變的端點,未來的產業在跨屏傳播方面的競爭將是對原創內容(IP)和用戶注意力(ID)的競爭,而這兩方面競爭的連接點則是基于跨屏用戶的大數據采集和分析,產業參與者應該沉靜下來,忘掉屏幕、忘掉互聯網思維、忘掉所謂的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之爭,真正樹立起用戶思維。誰能夠精準的把握住用戶,誰就能夠有針對性的創造出最符合用戶需求的原創內容。
[1]張海潮,鄭維東等.全面進入大視頻時代[J].媒介,2015(4):31.
[2]劉珊.全媒體視頻化,如何改變視頻傳播調查行業?[J].媒介,2015(4):54-55.
[3]肖葉飛,劉祥平.媒介融合與規制融合[J].現代傳播,2015(3):13.
[4]黃升民.旗幟鮮明做產業[J].媒介,2013(11):1.
[5]吳世文,謝湖偉.媒介融合的多重邏輯及發展取向[J].青年記者,2015,1(上):55.
王兆紅,男,江蘇蘇州人,蘇州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視覺傳播設計方向研究;
劉慶振,男,河北衡水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公管與傳媒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新媒體傳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