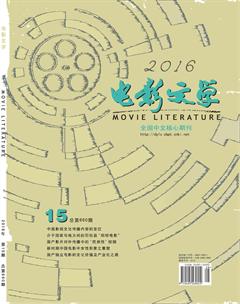介于國家與地方間的石柱縣“壩壩電影”
李歡 楊亭
[摘要]露天電影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農村,作為主要的文化傳輸以及民眾娛樂的手段,因其放映形式的靈活性、放映題材的針對性、受眾的大眾化等特質,被民眾稱為“壩壩電影”。過去對“壩壩電影”的關注,較多從電影學學科介入,闡述當代露天電影承載的傳輸功能。筆者于此處,欲從社會學的視角探究被塵封在歷史中的“壩壩電影”,其中隱現的過去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國家意志與民眾意愿的雙向機制。
[關鍵詞]石柱縣;“壩壩電影”;電影放映隊;國家意志;地方情感
一、問題提出
露天電影在國家文化啟蒙與教育政策的推動下逐步進入農村百姓的視野,它所傳遞的意識、觀念、情感等潛移默化地植入大眾生活中,作為特殊的文化傳播媒介,受到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學界研究露天電影多從電影學的視角對其解讀,剖析新世紀以來建設新農村的時代語境中,露天電影所發揮的功能,闡發露天電影的傳媒功效、營銷策略等問題。雖說此研究路徑著實令人折服,但是在筆者看來,對露天電影的研究還存在較大的空間,不僅應該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露天電影納入其考量之中,此時段露天電影所隱現的政治化、國家化傾向也應受到足夠的重視,還需要深究國家的政治行為在推行中借助什么來完成,同時農村又是如何來接受的。鑒于此,以筆者家鄉石柱縣為例,通過地方志等文獻資料的查閱收集和對石柱縣部分場鎮年滿60歲以上的老人進行口頭訪談等形式,來探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石柱縣“壩壩電影”究竟在農村傳播過程中如何實現國家到地方和地方到國家的雙向流通,進而考量在此過程中“壩壩電影”所呈現的獨特價值意義。
二、“壩壩電影”的個案調查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石柱縣由于經濟并不發達,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對精神娛樂的追求也表現得并不明顯。早期,由于文化匱乏,百姓農閑時常有的娛樂方式只有看土戲、唱地方民歌以及跳土家擺手舞等。這些土家族本土藝術相較于電影而言內容陳舊單一,受眾僅為部分老人,其形式也被集視覺、聽覺于一體的動態畫面所超越,因而電影更受百姓的青睞。每逢放映當日,以石柱縣為代表的西南農村地區,猶如農村趕場,呈現出“節慶”的場面。90年代以前石柱縣就組建過許多“壩壩電影”放映隊,分布于縣城、西沱鎮、下路鎮、王場鎮(原王場鄉)等各個鄉鎮,成為文化傳播的流動站。
筆者閱讀《石柱縣志》后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石柱并無固定的電影放映院。1984年,電影公司在縣城五一路(今街心花園左側)建立1028座電影放映院。1988年后,西沱鎮、王場鄉建有電影院,其余區鄉和茶園煤礦、趕家橋煤礦、黃連總公司、龍池壩水泥廠以及各區學校建有公用的放映室,農村仍為露天放映。[1]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西南農村,電影放映的方式仍然延續80年代以前的露天“壩壩電影”形式。此外,筆者抽選石柱縣南賓鎮、下路鎮、西沱鎮黎場鄉、黃鶴鎮(原馬武鎮黃鶴鄉)、王場鎮(原為王場鄉)五處作為調查點,以60歲以上的老人為口頭采訪對象,分別就以下內容進行訪談,包括“壩壩電影”的放映形式、放映地點、放映操作、觀影場面、放映片目等。
采訪中筆者收集到許多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期間播放的電影片名,由于被采訪者年齡較大,老人所談及的是回憶中印象較為深刻的影片。其中播放的影片包括:抗戰片(如《地道戰》《地下游擊隊》《小兵張嘎》《閃閃的紅星》《白毛女》《董存瑞》《東方紅》《地雷戰》等)、少數民族生活片(如《劉三姐》《五朵金花》《冰山上的來客》《草原上的人們》《阿凡提》等)、愛情片(如《白蛇傳》《廬山戀》等)、武俠片(如《少林寺》《霍元甲》等)、農村生活片(如《老井》《黃土地》《農田喜事》)以及有關種植、養殖和安全用電防火等的宣傳片(如種柑橘、養豬等方面)。此外,在片歇時還會播放一些革命歌曲、村內通知等。這些影片的放映時間幾乎與農村趕場時間①一致,在趕場當天下午五六點左右在各鄉、場政府辦公點面前的空地、場鎮學校的操場等地放映。另外于節日期間(如國慶節等)也會安排放映。
經訪談得知,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上級地方文化組織委派組建電影流動放映隊,放映隊又分放映小隊,多為2~3人。采訪的對象中,筆者有幸找到一位老電影流動放映員,②老人1983年在西沱鎮及附近場鄉做過為期一年的電影放映人,當時稱為西沱鎮電影放映小隊。據老人回憶,放映人要經過培訓,并到西沱鎮電影院統一領取電影放映機、白布以及電影膠片等,學習如何操作和使用放映工具。放送“壩壩電影”的范圍是西沱鎮及附近的一些鄉、場,包括黎場鄉、王場鄉、趕家橋煤礦等。放映人負責于放映前與基層地方組織接洽,提前通過喇叭、黑板及大字報等工具告之農村百姓電影的放映地點和時間。放映地點一般選在學校開闊的操場或村委會前的空地,以適應農村眾多的觀影群眾。放映時間則相對固定,與農村趕場時間大致相同,從而擴大“壩壩電影”的受眾面,也可以錯開各場鎮播放的時間以協調放映員的工作。據以上不完全統計,可大致了解20世紀八九十年代石柱縣“壩壩電影”主要放送的片目,筆者將其分為抗戰片、少數民族生活片、愛情片、武俠片、農村生活片以及關于種植、養殖等方法教授和安全用電防火等教育宣傳的科教片,此外,還會播送系列革命歌曲和村內通知等。0
三、“壩壩電影”:國家與地方的耦合
“壩壩電影”隨著群眾文化生活的多樣化而漸漸式微,不再具有因文化匱乏帶來的獨特視聽享樂,卻因時代的變遷而烙下深刻的印跡,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到不可小覷的媒介作用。一方面,“壩壩電影”隱現著過去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國家意志,從而巧妙規約著農村百姓的思想行為;另一方面,民眾在接受的同時通過放映人有效的表達意愿,并利用影片解決實際問題。
(一)國家意志對地方社會的傳輸與影響
播放“壩壩電影”在當時是非營利性質的行為,是國家有計劃地豐富農村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或者說實質上是一種國家權力意志的表達行為,起到啟迪基層群眾的作用。“電影的政治教化和思想教益功能,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被置于電影的藝術形式和娛樂作用之上,體現出電影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存在特征”[2],成為一種思想教育體制。作為時代的產物,這種特殊的文化產業,在觀看時表面上沒有現金的交換,讓百姓與藝術品達到“無中介接觸的印象,而文化產業則從一系列在消費者背后進行的交易中獲得利潤”[3],這種“利潤”即文化產業達到將國家的意識形態等通過電影畫面形式傳遞給基層群眾的目的,所傳遞的文化、思想、觀念等信息則因國家交予地方推送的各類電影片目而相異。
首先,在上述之電影片目中,如《地道戰》《地下游擊隊》《小兵張嘎》《閃閃的紅星》《白毛女》《董存瑞》等抗戰影片,除了回味經典之外,影片的放送更為重要的是向農民傳遞主流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向農民群眾傳達出我黨對于人民的領導教育和感召力,飽含著一種懷舊情懷、一種憶苦思甜的思想內涵在其中。福柯的《規訓與懲罰》中談到“肉體是馴順的,可以被駕馭、使用、改造和改善”[4]154,國家權力意志在此借助電影規訓百姓的行為方式,“強加給它各種壓力、限制和義務”[4]155,它們如毛細血管一般,遍布于地方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并通過“壩壩電影”這一形式發揮作用,規范并且馴服人的身體和靈魂,使其符合國家所倡導的社會規范和行為秩序,并教導群眾相信黨、跟隨黨,從而走向一條康莊大道。據筆者的爺爺回憶,他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電影《白毛女》:“那時候還沒有電視,看露天電影是很難得的事。爺爺記得最清楚的電影就是《白毛女》,喜兒非常可憐,后來頭發都變白了,黃世仁這個地主真是可恨!現在生活越來越好了,那種事也不可能有了。”③百姓在“壩壩電影”放映中看到和聽到的,在與鄰里鄉親聊天的過程中對之重復并熟知,譬如其中的口號、標語等(如《閃閃的紅星》當中的“紅星是咱工農的心,黨的關懷照萬代”“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在此循環往復的過程中,“壩壩電影”將國家意志更為深刻地標記在百姓腦海中。電影當中充滿正氣的英雄人物,比如電影《劉三姐》當中的巾幗英雄劉三姐,《小兵張嘎》中的少兒英豪小兵張嘎,《董存瑞》中的革命英烈董存瑞等在當時一度成為備受百姓追捧的國家英雄,甚至如兒童在游戲中也會爭做英雄角色。筆者的父母也談到當時看電影猶如過年一樣高興,為了看電影,可以翻山越嶺徒步四五個小時走到鄰近的王場鄉去,毫無怨言。那時候許多孩子都會扯下樹枝,削成槍的形狀,別在腰間,模仿電影中的人物。“壩壩電影”此時便成為引領時尚的風向標。
其次,在調查中收集到反映中國少數民族生活的電影作品,包括《五朵金花》《劉三姐》《冰山上的來客》《草原上的人們》等。這些少數民族生活片向基層農民呈現了中國其他地區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態,影片大都表現中國少數民族的一種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他們對于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新中國持有的是一種支持和擁護的態度。這類影片事實上“起到了縫合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罅隙的作用”[5],通過此類影片來暗合少數民族地方的需要,對基層百姓,具體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石柱縣的少數民族群眾,也是在強調構建一種少數民族對于國家的認同感,強調民族團結和對民族精神的彰顯,凸顯各民族共存之意義,喚起華夏民族一體化的重要性。“壩壩電影”在這里成功地達到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的功能,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傳播的有效手段。與此同時,這些作品中經典的片曲給許多老人留下深刻印象,包括《劉三姐》當中悠揚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草原上的人們》中深情的《敖包相會》以及《冰山上的來客》中的民族歌曲《花兒為什么這樣紅》等。這些歌曲至今為很多藝術家傳唱,成為經典,也被眾多基層群眾所知曉,這則要歸功于“壩壩電影”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在做訪談時,老人馬培坤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影片《劉三姐》和《草原上的人們》,老人已年過八旬,她激動地說:“原來外面還有這么多不一樣的人……”訪談接近尾聲,老人還深情地向我們哼唱了影視歌曲《敖包相會》。
此外,筆者還收集到諸如《廬山戀》《白蛇傳》一類的愛情故事片,愛情在當時的農村本屬于敏感話題,之后伴隨電影的介入得以逐漸改變,婚姻法強調的自主之風借由電影傳遞給群眾;《少林寺》《霍元甲》等武俠故事片受到村民特別是兒童的喜愛,一招一式皆展現著中國功夫的精湛與魅力。據筆者的父母回憶,二人相識即由于母親認為父親穿著長衣恰似電影中的陳真,可見電影帶來的影響之深刻。一些反映農村生活的影片,如《老井》《黃土地》等,反映農村現實生活和農民思想的變化,體現國家對農民思想的教育,鼓勵農民追求思想進步和新生活。至于放映的科教片,除了種植、養殖方面的內容外,還包括國家政策的宣傳,例如“尊老愛幼”“民族團結”等口號與不同時期地方宣傳的重點不謀而合,農民在觀影的同時受到政策的洗禮。在片歇時,放映人還會播放一些革命歌曲,或者是鄉上村里的通知,電影銀幕被充分利用并融入百姓生活。
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電視在農村普及,“壩壩電影”逐漸退出基層農村的視野,卻在農民心里留下深刻的記憶,并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農民的思想和行為習慣。國家意志,通過“壩壩電影”這種文化形態得到了有效的表達,同時達到豐富群眾精神世界的雙重效果,實現了自上而下的溝通。
(二)地方社會對國家意志的接受和認同
“壩壩電影”對當時的群眾而言意義重大,他們借助電影間接學習文化知識,豐富認知并運用于實踐,隨之而來的是文化意識的普遍萌芽,農民利用電影為自己服務甚至通過放映人傳達需求以解決現實問題,國家意志自此為地方社會所接受,并改變百姓生活。
首先,通過“壩壩電影”,當地百姓得到文化的啟蒙,百姓學習文化知識并將其運用于自身的生產生活實際。多數農民未曾受過良好的教育,識文斷字的能力有限,更多的農民于觀影后熟知片中的語言用詞并加以運用,在一定程度上學習了文化知識,普通話也得以推廣。訪談中筆者得知,百姓在起名字時常會借用影片中所涉及的詞匯,譬如許多農民群眾給子女起名為“安全、洪衛、紅星”等與科普宣傳片中“安全防火”等標語暗合;更為可貴的是,農民意識到文化知識的重要性,更多人將子女送到學校受教育,響應國家當時開始實行的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為改變農村生活現狀打下基礎。百姓通過“壩壩電影”還養成了一些習慣,如早晚刷牙漱口,男士留長發等。此外,對待農村普遍問題的意識也得以萌芽。調查結果中包括《廬山戀》《白蛇傳》等愛情片,解凍了愛情這一敏感話題,曾在農村普遍存在的包辦婚姻現象得以改善。據筆者了解,婚戀自由方針在父輩一代人中漸漸得以貫徹;男女不平等問題得到重視,配合教育科普片中“生男生女都一樣”的生育政策號召,女性地位得以逐漸提升,許多農民愿意將女孩送進校園接受與男孩同等的教育;最為顯著是90年代的“打工潮”現象,農民種糧養殖收益甚微,銀幕上所展現的外部世界于物質和精神方面便顯現出更大的吸引力,許多農民放下鋤頭,南下到廣東一帶打工,農民努力創建新生活的意識通過電影得以樹立。
其次,電影潛移默化地改變著老百姓生活的同時,老百姓也借助電影為自己服務。例如,在黎場鄉播放“壩壩電影”的時間是約定俗成的“一、四、七” ⑤當中的日子,那時,電影放映日甚至成為“節日”,百姓手拿煙斗和零食提前去占領有利位置。在觀影以及更換膠片的間歇,聊家常,聽趣聞,打聽莊稼長勢,詢問牲畜喂養經驗等,甚至在這期間完成相親的見面儀式或各戶舉行婚喪嫁娶儀式的請柬作用,提升了百姓間的交流機會。此外,重要的通知,譬如征兵、婚慶、會議通知等,借助電影媒介實施傳達,這是當地社會與民眾能動地改造電影這一外來藝術形式的結果。部分村民還通過與放映人溝通,告訴放映人自身所需要的影片類型,通過影片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例如,百姓期待電影給予自己生活和日常勞作方面的幫助,在西南地區農耕時,希望放映人能帶來一些農作物種植方面或是有關喂養牲畜方法的影片。放映人將百姓需求反映到地方,地方通過協調最終將影片交給放映人播放。在此過程中,電影流動放映人成為媒介,基層的農民群眾通過“壩壩電影”這種文化形態達到一種自下而上的溝通和反饋。與此同時,農民在電影中看到的新興行業擴展了其致富視野,甚至將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從事效益更佳的產業,例如辦制磚廠、修理廠、運輸行業等,農民的致富途徑得到本質性的轉變。
“壩壩電影”作為時代的產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價值意義。它曾經發揮的歷史功效,在國家與地方之間的雙向機制中得以充分展現,國家和地方社會的雙向溝通借助影片得以實現,并通過“壩壩電影”和電影流動放映人來實現地方社會與國家意識的搭橋。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一媒介逐步退出歷史舞臺,雖然部分地方還在實施電影文化下鄉的舉措,但其追求的價值目標、營銷策略等同本文的研究點不屬于同一范疇。此處筆者正是通過透視“壩壩電影”的文化功能及其價值意蘊,希冀對這一塵封歷史的文化形式所蘊含的特定時代的精神文化符碼憶現,因此具有一定的價值。
注釋:
① 調查點趕場時間:西沱鎮黎場鄉常為“一、四、七”,即每月含一、四、七的陽歷日期,如十一號、二十四號、七號等(下同);石柱縣城常為“一、四、七”;黃鶴鎮(原馬武鎮黃鶴鄉)常為“二、五、八”;王場鎮(原王場鄉)常為“三、六、九”;下路鎮常為“二、五、八”。
② 訪談對象:陶遠昌,男,69歲,石柱縣西沱鎮黎場鄉人。訪談時間:2016年1月29日。訪談人:李歡。
③ 訪談對象:李洪發,男,78歲,石柱縣西沱鎮黎場鄉人。訪談時間:2016年2月4日。訪談人:李歡。
④ 訪談對象:馬培坤,女,81歲,石柱縣黃鶴鎮(原馬武鎮黃鶴鄉)人。訪談時間:2016年2月3日。訪談人:黃玲。
⑤ “一、四、七”即每月含一、四、七的陽歷日期,如一號、十四號、二十七號等。
[參考文獻]
[1] 石柱土家族自治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石柱縣志評議稿1986-2002年(下)[Z].2007:715-716.
[2] 章柏青,賈磊磊.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上冊)[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9.
[3] [英]約翰·湯普森.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M].高铦,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110.
[4] [法]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5] 饒曙光,等.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史[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1:334.